編按:
本文節錄自《華文散文百年選.中國大陸卷2》的〈冬至如年〉一文,作者徐則臣,他的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獲第五屆老舍文學獎、2014年亞洲周刊中文十大好書,短篇小說〈如果大雪封門〉獲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北上》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等。
以下為摘文——
人老了對生命和死亡的看法會變。70歲後,祖母突然熱衷於談論死亡。之前有20年她對此毫不關心,每過一天都當成是賺來的,一年到頭活得興興沖沖,裡裡外外地忙,不願意閑下來。這20年的曠達源於一場差點送命的病患。50歲時,醫生在我祖母肺部發現了可疑的陰影,反覆查驗,儘管好幾家醫院都說不清楚這陰影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但結論驚人地相似。當時正值寒冬,馬上到春節,醫生們說:回家準備後事吧,過不了這個年。那時候中國還處在喑啞灰暗的20世紀70年代,醫生的話跟老人家的語錄一樣權威。一家人抱頭痛哭之後,把家裡所有的錢都拿出來,又借上一部分,決定再跑一家醫院。去的是大城市裡的一家軍隊醫院,在遙遠的海邊上。其實也不遠,一百里路,但對一個一輩子生活在方圓十里內的鄉村女人來說,那基本上等於天的盡頭。祖母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了大城市,有樓有車,馬路上的人都有黑色的牛皮鞋穿,她覺得來到了天堂裡,死也值了。她做好了準備。可是在經過繁複的檢查之後,醫生告訴我們家人:沒查出明確的毛病,但應該不至於死,回家好好活,活到哪算哪。
等於從鬼門關走一遭又回來,祖母滿心再生的放鬆和欣喜,決定遵照最後一個醫生的囑咐:活到哪算哪。就活到了70歲。70歲的時候身體依然很好,好得彷彿死亡的威脅從沒降臨過。這個時候,祖母突然開始談論死亡。那時候我念中學和大學,每年只在節假日才回家,一回來祖母就跟我說,在我不在家的這些天,誰誰誰死了,誰誰誰又死了。白紙黑字,好像她心裡有本「錄鬼簿」。祖母不識字,也不會抽象和邏輯地談論死亡,她只說一些神神道道的感覺。有一陣風過去,她就說,有人死了。一塊黑雲擋住太陽,她就說,誰要生病了。滿天的星星裡有一顆突然劃過夜空,她就說,某某得準備後事了。有一年暑假我在家,祖母坐在藤椅上覺得渾身發冷,她跟我說,這一回得多走幾個人了。
 圖/僅為情境配圖。取自pixabay
圖/僅為情境配圖。取自pixabay
的確,年紀大一點的老人經常會約好了一起死,75歲的這個剛埋下地,74歲的那個就跟上去了。一死就一串子。過去我不曾在意過。到祖母七十多歲開始不厭其煩地談論死亡時,我才發現,在鄉村,死亡真的像一場瘟疫,開了一個頭,總會一個接上一個。所以祖母說,你看巷子裡的風都大了。她的意思是,人少了,沒個擋頭,風就可以愈來愈肆無忌憚地滿村亂跑了。在70多歲的某一年,祖母開始抽菸、喝酒。過去活得勁頭十足,每天都像過年,現在要把每天都當年來過。70多歲了,祖母還是很忙,但動作和節奏明顯慢了下來,從堂屋到廚房都要比過去多走好幾步,往藤椅上一坐,經常一時半會兒起不來。她肯定很清楚那把老藤椅對於她的意義,所以經常擦拭和修補;她坐在藤椅裡慢悠悠地抽菸,目光悠遠地對我講村裡已經發生的、正在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死亡。
現在想起祖母,頭一個出現在我頭腦裡的形象就是祖母坐在藤椅裡抽菸。祖母瘦小,老了以後又瘦回成了個孩子,藤椅對她已經顯得相當空曠了。她把一隻胳膊搭在椅子上,一隻手夾著菸,如果假牙從嘴裡拿出來,吸菸時整個臉都縮在了皺紋裡。除了冬天,另外三個季節藤椅上都會掛著一把蒼蠅拍,抽兩口菸她就揮一下蒼蠅拍。有時候能打死很多蒼蠅和蚊子,有時候什麼都打不到。這個造型又保持了20年;也就是說,從祖母熱衷於談論死亡開始,時光飛逝中無數人死掉了,祖母在連綿的死亡敘述中又活了20年。
臨近90歲的這幾年,祖母每天都會有一陣子犯糊塗。除了我,所有半個月內沒見到的人她都可能認不出來。即使是我,她最疼愛的唯一的孫子,有一次在電話裡也沒能辨出我的聲音。我在北京,隔著千山萬水跟她說了很多噓寒問暖的話。然後她放下電話,跟我姑媽說,剛才有個男的打來電話,讓我多喝水,多吃東西,誰啊?
還有一個重大變化,祖母不再談論死亡。菸還繼續抽,酒也照樣喝,一天裡有愈來愈多的時間坐在藤椅裡,偶爾揮動蒼蠅拍,話也愈來愈少。死亡重新變成一件無足輕重的事。
因為間歇性的糊塗,我們經常把她的沉默也當成病症之一,看她安詳地坐在藤椅裡,不忍去打擾。只有等祖母想要說話了,我們才陪她聊一聊。祖母開始談論各種節日和節氣,往歡欣鼓舞上談。這個我能跟她老人家談得來。土節、洋節,各種稀奇古怪的節日,我基本上都知道一點,傳統的二十四節氣也能扯上幾句。我還不識字的時候,二十四節氣歌和一些農諺就會背了,這大概是大多數鄉村知識分子家庭裡的孩子都要經歷的最早的知識啟蒙。不過啟蒙完了也就完了,跟土地漸行漸遠,與鄉村為數不多的聯繫之一,也僅是靠著那點童子功,能把二十四節氣有口無心地順溜地背下來了。祖母在談論這些節氣時像回到了20年前,而一旦回憶起在這些節氣中的個人史,祖母思路之清晰,簡直就是回到了40年前。某年某節,某件事發生了;某年某節,某個人如何了。她用她為數不多的清醒時光回憶了90年裡的各種節日和節氣。
「那個時候,」祖母說,「我就想活到過年。」
我明白。醫生當時斷言,她過不了年。「都過去的事了,奶奶。」
「現在不想了。過了年也就那樣。」
祖母的口氣裡有一個勝利者在。但她對春節還是相當看重。實際上是最看重,在她的時間節點裡,一生中最大的事情不少都發生在這個天寒地凍的日子裡。因為過年的時候一家人總要團聚在一起,一夜連雙歲,是終點也是起點。
但祖母去世在冬至那天:她完全是掐著點兒要在那天離開人世。這當然是我們事後的推斷和發現。
是我們迷信嗎?祖母能決定自己的死亡?我們一直在懷疑,但不得不承認,從祖母決定不再進食開始,她的確就一直在扳著指頭數。冬至前的半個月,祖母從藤椅上下來,經過走廊前的臺階時摔倒了,摔裂了右腳踝骨。就算對一位90歲的老人來說,這也不算多大的傷。對祖母來說更算不了什麼。在之前的五年裡,因為股骨頭壞死,祖母相繼動過兩場大手術,第一次植入了人造的左股骨,第二次植入了人造的右股骨。換了兩根骨頭,祖母依然能夠拄著拐杖到處走。
踝骨骨裂無須大驚小怪。不過傷筋動骨100天,需要耐心。照例治療,上藥,石膏,夾板,休養。祖母枯瘦,醫生建議打點滴給祖母消炎和補充能量,以利於恢復。這個建議很好,祖母在醫院裡靜脈注射了幾天藥水,出院後回到家,某個早上突然決定不再進食。祖母自己的決定。祖母多年來一直是過於有主張的人,說一不二。開始還願意喝點粥,兩天后,一粒米粒都不進,只喝稀湯,然後稀湯和牛奶也不喝,只喝白開水,很快連白開水也不願大口喝,只能過一會兒喂一湯匙,潤潤喉舌。12月天已經很冷,祖母躺在床上,你把她兩隻胳膊放進被子裡,她就拿出來,兩手交叉,閉著眼,緩慢地扳動手指頭。不說話,只是一遍遍數手指頭。給她掛鹽水打點滴更不答應,連著針頭一起拔了扔掉。不吃,不治,閉著眼數手指頭,數得愈來愈慢。直到某一天,手指頭不再數了,很長時間才能艱難地睜一次眼。祖母不再說話,除了嗓子裡偶爾經過的痰音,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
一大早我還躺在北京的床上,母親打來電話,說祖母可能不行了,抬頭紋都放平了。鄉村裡的死亡有一套自己的倫理和秩序,抬頭紋攤平了意味著是眼瞅著的事。我趕緊往機場跑,回到家,祖母躺在床上,睜了半隻眼看了看我,接著又把眼睛閉上。我不知道這一次她老人家是否認出她的孫子來。祖母沒吭聲,再也沒吭過一聲。
接下來是殘忍卻無可奈何的漫長的守候過程。漫長是指那個煎熬的過程,殘忍也指的是那個煎熬的過程,你知道她在奔赴死亡,你知道無法救助,你還得眼睜睜地看著她的生命一寸寸地從她的身體上消失。這種守候完全是一種謀殺。一天過去,一夜過去;又一天過去,到晚上,祖母早已經神志不清。你知道緩慢的死亡對她也是煎熬,但你也得順其自然。先是胳膊不再動,然後是腿不再動;祖母偶爾轉動一下脖子的時候,93歲的祖父經過祖母身邊(這也是在他們共同的生活中,最後一次經過祖母身邊,其餘時間祖父把自己關在房間,一個人悲傷和回憶),祖父說:
「她要等到12點。」
12點就是半夜,零點,是新一天的開始。被祖父說中了,12點附近,祖母突然挺了一下身體,不動了。再沒有比那夜更漫長的夜晚。
的確沒有比那夜更長的夜晚。那天是冬至。那一天太陽光直射南回歸線,北半球全年白天最短,黑夜最長。那一天在北方,是數九寒天的第一天,明天會比今天更冷。
我們的哭聲響起。祖父在房間裡說:「這日子她選得好。」
是不是祖父都知道?他們在一起生活了70年。祖父說,這一天要吃餃子,要給祖先燒紙上墳,這一天要當成年來過。我知道往年冬至也要吃餃子、上墳,但從不知道這節氣有祖父這一次語氣裡的隆重。
安葬了祖母,我查閱相關資料:這一天,「陰極之至,陽氣始生」,古時它是計算二十四節氣的起點,也是歲之計算的起訖點;這一天如此重要,僅次於新年,所以又稱「亞年」;民間常說,「冬至如大年」、「冬至大如年」。
祖母過了年,也到了冬,圓滿了。願她在天之靈安息。
2014年3月13日,知春里
作者簡介 徐則臣(1978-),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現居北京,任《人民文學》雜誌編輯。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獲第五屆老舍文學獎、2014年亞洲周刊中文十大好書,短篇小說〈如果大雪封門〉獲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北上》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等。著有長篇小說《午夜之門》、《夜火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北上》;中短篇小說集《跑步穿過中關村》、《居延》、《石碼頭》;散文集《我看見的臉》、《別用假嗓子說話》、《從一個蛋開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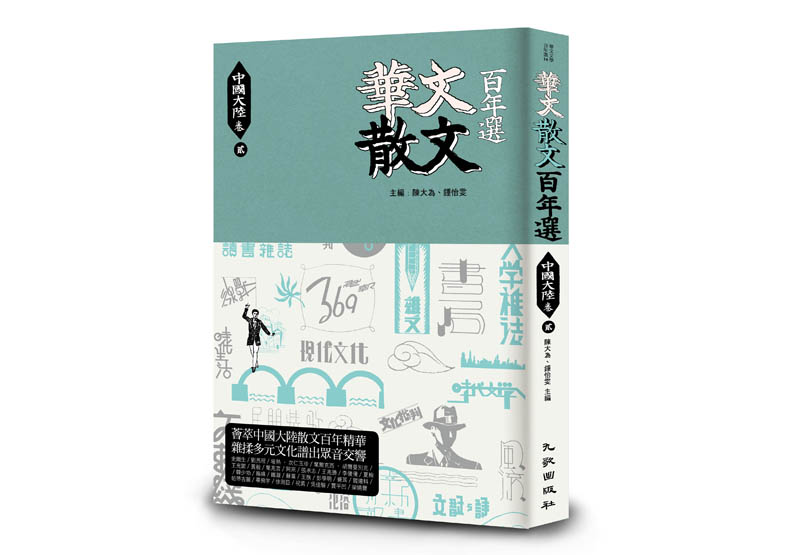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華文散文百年選.中國大陸卷2》一書,陳大為、鍾怡雯編,九歌出版。
本文節錄自:《華文散文百年選.中國大陸卷2》一書,陳大為、鍾怡雯編,九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