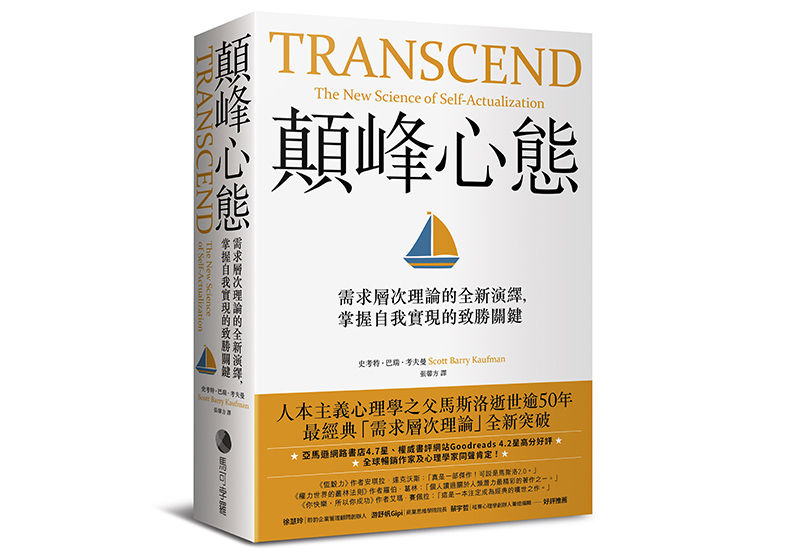編按:臨床心理學家喬治.博南諾將韌性定義為:人在面臨極度危險或創傷性的事件時,維持相對穩定、健康的心理與生理功能運作的能力。某種程度上,痛苦在找到意義的那一刻起,便不再是痛苦。(本文摘自《顛峰心態》一書,作者為史考特.巴瑞.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以下為摘文。)
韌性可以被訓練
能夠妥善解決暴力或危害生命的事件的那些人,往往被視為英雄。無論出於多麼正當的理由,這種做法通常會加深一種錯誤的觀念,就是只有少數「情緒強度出眾」的人才具有韌性。
——喬治.博南諾(George Bonanno),〈失去、創傷與人類的韌性〉(Loss, Trauma, and Human Resilience,2004年發表)
某種程度上,痛苦在找到意義的那一刻起,便不再是痛苦。
——維克多.弗蘭克,《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1946年出版)
在2004年的開創性論文中,臨床心理學家喬治.博南諾從廣泛角度闡述壓力回應的概念,在學界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他將韌性定義為人在面臨極度危險或創傷性的事件時,維持相對穩定、健康的心理與生理功能運作的能力。博南諾回顧大量研究發現,韌性其實是許多人都具備的特質,它與精神病理的缺乏並不相同,而且還可經由許多出乎意料的方式訓練而成。美國約有61%的男性與51%的女性表示自己在人生中至少經歷過一次創傷,有鑑於此,人類其實具有極大的韌性。
事實上,許多經歷創傷(例如罹患慢性病或不治之症、失去摯愛或遭受性侵)的人不只展現強大的韌性,還在走出傷痛後過得更好。研究顯示,大多數的創傷倖存者並未發展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病癥,其中甚至有許多人從經驗中得到成長。理查.泰代斯基(Richard Tedeschi)與勞倫斯.卡洪(Lawrence Calhoun)發明了「創傷後成長」一詞來解釋這種現象,將其定義為人在克服極度艱難的生活環境後所產生的正向心理變化。根據研究,源自逆境的成長領域可分為以下七種:
源自逆境的成長領域
可以肯定的是,多數在創傷後成長的人都寧願自己不曾經歷過創傷,而相較於正面的生活經驗,創傷很少能促成這些成長領域的進步。儘管如此,其中的多數人往往在試圖理解深不可測的事件之後,對自己突如其來的進步感到訝異。成長與痛苦時常並存。
猶太拉比哈洛德.庫什納(Harold Kushner)回想痛失愛子的經歷時,貼切地描述了這種感受:
因為亞倫的出生與死亡,我成為一個更加敏感的人、更盡職的牧師、更有同情心的諮詢顧問,如果不是這個原因,我不會如此。假使可以讓我的兒子起死回生,我願意放棄一切。假如我可以選擇,我會放棄自己因為過去的經驗而在精神上獲得的成長與洞察……但我別無選擇。
創傷讓我們必須重建自我與內在
無庸置疑,創傷會撼動我們的世界,迫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待所珍視的目標與夢想。泰代斯基與卡洪以地震作比喻:我們傾向仰賴一套特定的信仰與假設,來看待世界的良善與可控制性,而創傷事件往往會粉碎我們的世界觀,破除我們習以為常的感知,讓我們必須重建自我與內在。
但我們擁有的選擇是什麼?澳洲精神病學家維克多.弗蘭克說:
當我們無法再改變情況時,我們就會面臨改變自我的挑戰。

近年來,心理學家開始研究將危機視為轉機的心理過程,並逐漸瞭解到,這種「心理受到震撼」後的重建,其實是成長的必要條件。正是因為自我的基礎結構受到了撼動,我們才能占據最有利的位置,去追尋生命中的全新機會。
同樣地,波蘭精神病學家卡齊米日.東布羅夫斯基(Kazimierz Dabrowski)主張,「正向人格裂解」(positive disintegration)有助於成長。東布羅夫斯基研究了一些心理高度發展的實驗對象後得出結論,健康的人格發展往往需要人格結構的分裂,進而引起暫時的心理壓力、自我懷疑、焦慮與沮喪。然而他認為,這個過程可以引導個體深入檢視自己的潛力,最終促進人格發展。
將危機視為轉機的因素一:認知探索
使我們得以將危機視為轉機的一個關鍵因素是,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探索自己對於當下事件的想法與感受。認知探索(Cognitive exploration)——可定義為好奇各種資訊與傾向進行複雜與彈性的資訊處理——讓我們對令人困惑的情況感到好奇,使我們更有可能在看似難以理解的事物中找到意義。不可否認地,其中有許多可促成創傷後成長的過程,會牴觸我們逃避極度難受的情緒與想法的天性。儘管如此,唯有卸下天生的防衛機制並勇敢面對眼前的難題、將一切視為成長的養分,我們才能開始接受生命中無可避免的矛盾,從更細微的角度看待現實。
將危機視為轉機的因素二:反芻思考
經歷創傷後,不論是生重病或失去摯愛,我們自然會難過、反覆想著所發生的事情,一再出現負面的想法與感受。反芻思考(rumination)通常表示,你開始努力理解眼前的事件並積極推倒舊有的信念與找到新的意義與認同。雖然反芻思考起初往往是自動產生、造成侵擾與不斷重複的,但隨著時間過去,這種思維會變得越來越井然有序、受到控制與沉穩謹慎。這種轉化過程無疑會帶來巨大的痛苦,但在你反芻思考的同時,也會建立起強大的社會支持系統並找到其他的表達管道,這麼做對成長助益良多,讓我們得以挖掘內心深處從未意識到的力量與同理心。
將危機視為轉機的因素三:增進「心理彈性」
難過、悲傷、憤怒與焦慮等情緒,也是人在面對創傷時的常見反應。經驗性迴避——逃避害怕的想法、感受與知覺——非但無助於抑制或「自我調節」這些情緒,反而讓事情變得更糟,使我們認為這個世界並不安全,變得更難以追求有價值的長期目標。透過經驗性迴避,我們封閉了探索能力,因而錯失許多能帶來正向經驗與意義的機會。接受與承諾治療將此作為核心主題,旨在增進人們的「心理彈性」。如此一來,我們便能抱持探索與開放的態度,在面對創傷時依循自己的價值觀採取更好的應對方式。
陶德.卡珊登與珍妮佛.凱恩(Jennifer Kane)以大學生為對象進行了一項研究,評估經驗性迴避在創傷後成長中發揮的作用。在這群學生之中,最常見的創傷事件包括親人或摯友驟逝、車禍、目睹家暴與經歷天災。卡珊登與凱恩發現,這些研究對象在創傷中承受的壓力越大,之後的成長幅度就越大,但這個結果只限於呈現低度經驗性迴避的那些人。經歷過比其他人更大的壓力、而且幾乎不依賴經驗性迴避的人,在人生中得到成長與意義的程度傲視其他的研究對象。至於那些採取經驗性迴避的大學生則呈現相反的結果,他們承受更大的壓力,但經歷創傷後所得到的成長與人生意義的程度卻不如其他人。這項研究印證了日益增加的文獻結果,顯示焦慮程度低伴隨經驗性迴避程度低(即具有高度心理彈性),讓生活品質有所增長,也指出人在創傷事件後會領悟更多的人生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