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天下難,治天下更難。對蒙古人來說尤其如此,畢竟他們建國才二十年,創製文字才二十二年。他們倚賴商人管理商業體系,卻無法在治國上如法炮製,只倚賴哪一個特定族群。穆斯林的治理規則大不同於漢人,而基督徒又與穆斯林以及漢人都不一樣。在市場上,來自不同文化的商品可以隨意搭在一塊:來自中國的絲衣、來自波斯的花緞腰帶、來自西伯利亞的貂皮衣領、來自印度的孔雀翎毛、來自威尼斯的珠子、來自阿富汗的綠松石飾物。但無法從不同文化各挑選出政府制度、行政方法和法律,然後如商品般混搭在一塊。穆斯林律法來自古蘭經,而古蘭經只能用阿拉伯語讀,此外古蘭經所倚賴的伊斯蘭曆,又以穆罕默德前往麥地那的路線為依據;因此,蒙古人若要採行穆斯林的行政系統,就得接受全然不同的另一種語言和宗教。同樣的,採用中國的行政系統,也離不開中國文字和曆法。政府的構成遠比市場更為複雜。
蒙古人無法單純借用既有的體制,必須另創一個新制,由於男人忙於馬不停蹄的征戰,因此這份重責大任便落到成吉思汗統治絲路沿線一連串王國的女兒們肩上。阿剌海身為蒙古人裡較資深的皇后,又轄有帝國最大一部分的領土,帶頭創立了政府。學習閱讀和書寫是她得預先做好的準備之一。她在哪裡、又是如何學會讀寫,我們不得而知。有位南宋派來的漢人使節,針對其蒙古之行寫了一份詳盡的報告,他寫道,阿剌海不只學會了基本的讀寫,每天還撥出大量時間讀書。他甚至提到阿剌海對宗教典籍的喜愛,但未說明是哪種典籍。根據這位宋朝使節的描述,她特別精於醫術,還在她治理的國內設立了醫學機構。
根據在今日內蒙古敖倫蘇木(Olon Sume)遺址的考古調查結果,我們知道她的都城裡有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的宗教建築,很可能也有儒家、道教的機構和神職人員。這麼多種宗教、語言齊聚於一座小城市,點明了蒙古帝國的一個招牌特色:跨越民族畛域且往往在文化方面兼容並蓄。蒙古人未曾加諸於其子民身上普世宗教,反而是鼓勵各種宗教百花齊放。像阿剌海這樣的蒙古人,從五花八門的宗教教義、器物、儀式中挑選自己中意的,就像他們挑選當地食物時,以個人好惡為標準。不只這位皇后有權依個人好惡來行事,每個蒙古人都擁有這個機會。
阿剌海別乞塑造出一種強有力的蒙古式國際觀。身為家族與蒙古族裡第一個治理定居文明的成員,她發明了蒙古帝國後來依循的文化與組織模式。她的都城將陸續成為其他城市取法的原型,首先有窩闊台在蒙古打造的都城哈剌和林(Karakorum);再來是忽必烈在內蒙古打造的上都;最後則是忽必烈所打造的元朝都城汗八里(Khan Baliq,當時的中國人稱之為大都,即後來的北京),而且每一次取法,規模都更勝從前。
成吉思汗橫掃華北,女真人所創的金朝投降於他,接著逃到更南邊,把北方全留給蒙古人,金朝殘餘勢力因而成了蒙古與南宋之間的緩衝。成吉思汗原本期望女真人歸附蒙古帝國,替他繼續治理華北,因此金朝皇室的南逃使他雖掌控華北,卻無政府可治理該地。他不能留在中國,也無意親自治理這個地區,於是他找上女兒阿剌海。阿剌海已是戈壁以南地位最高的蒙古人,僅在她的父親之下。成吉思汗於一二一五年退回蒙古時,把蒙古人在中國攻下的土地交由她掌理。他將留守部隊交由札剌亦兒氏(Jalayir)的木華黎(Muqali)將軍指揮,但卻下令要他聽命於阿剌海。木華黎麾下的戰士大都是札剌亦兒氏的族人,該氏族長期以來追隨孛兒只斤家族,忠貞不二。
伐金之役後,成吉思汗把更多心力放在下一場征伐大業上,這次的對象是中亞的穆斯林國度。這段期間,他較不注意華北而愈來愈倚重阿剌海,阿剌海也以實際表現證明自己愈來愈懂得治國。她雖獨力行事,可是不管距離父親的活動宮廷多遠,阿剌海總是以整個蒙古世界的最佳利益為行事準則。成吉思汗知道自己會在外多年,於是指派兩個人負責管理已攻下的土地。他讓么弟鐵木格斡赤斤(Temuge Otchigen)掌理漠北蒙古高原,而把漠南新征服的土地交給女兒阿剌海別乞,並封她為「監國公主」。她轄下的人民從集中於今日內蒙古境內、約只一萬人的汪古族,擴大為散居華北各地的數百萬人。
阿剌海當政時,頻頻派兵協助父親在中國與中亞的軍事行動。這些來自中國的部隊包括醫療人員,對於將中醫的名聲和醫療實作散播至穆斯林世界與西方,貢獻甚大。
成吉思汗將三個女兒安插到絲路沿線當皇后,藉此控制了沿線地區和連接中國與穆斯林諸國的脆弱商業路線。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用兵中亞,開啟了一個新階段,不只奪取貿易路線,還將貿易路線深入到中東製造業中心。一如他在中國攻城略地開啟了接收中國製造業的過程,他的部隊鎖定穆斯林世界的手工製造中心,從而將絲路兩端的主要終點一併納入掌控。
在成吉思汗一生事業中,他兒子們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有限,而且沒什麼進展;但他女兒們的角色則隨著她們心智的成熟、經驗的累積而不斷提升。攻下形形色色的新國家和生態區,不斷為蒙古人帶來新的軍事和治理需求。
成吉思汗的女兒們所扮演的角色令中國人不解,可是中國人又對她們所掌握的權力肅然起敬;至於波斯人與成吉思汗另一位女兒的相遇,則是引發了困惑(這還是好的情況),以及在其他情況下被認為是厭惡與驚愕的反應。中國人嘲笑蒙古女人舉止粗俗,穆斯林則叱責她們褻瀆宗教,而且對文明造成威脅。
成吉思汗有許多女婿命喪戰場,但女婿若死在叛亂者之手,通常會引發慘絕人寰的報復。汪古叛亂者的遭遇相當幸運,與你沙不兒(Nishapur)造反城民的悲慘遭遇,猶如天壤之別。汪古人造反十年後,當成吉思汗攻打中亞的慘烈戰役正處於最高峰、而最終目標仍在未定之天時,你沙不兒城的叛民殺了他另一個女婿。
你沙不兒位在今日伊朗東部境內,是蒙古人西征時呼羅珊(Khorasan)地區的主要城市之一。呼羅珊以波斯文化為主流,但其實是突厥帝國花剌子模(Khwarizm)的一部分。該帝國的版圖涵蓋今日烏茲別克、阿富汗、土庫曼、塔吉克。你沙不兒地處盛產綠松石的礦場附近,是象徵波斯文化的神聖青綠色的源頭。體現該時期藝術與科技的美麗釉陶也產自此地。受人喜愛的波斯詩人歐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am),一○四八年生於該城,死後亦長眠於該城;透過詩作,他用文字替你沙不兒城和波斯文學罩上魔幻的美麗氛圍。這個盛產綠松石、詩、瓷器的城市,是波斯文明的結晶。因此,當這座城市遭異教公主所率領的軍隊毀壞,代表對所有伊斯蘭文明無以復加的侮辱。在穆斯林世界看來,這一事件就是整個蒙古時期的象徵。
波斯作家志費尼(Ata-Malik Juvaini)的編年史,首度詳述了此事的經過。儘管志費尼活躍於蒙古政壇,對此事的記錄稱不上客觀超然,不過他卻是穆斯林世界裡最忠於史實、最見多識廣的史學家。志費尼親身參與了自己筆下所述的許多事件,而且與多位目擊者談過話,其中許多人與他私交甚篤。
蒙古人攻下不花剌(Bukhara,即今日的布哈拉)、撒馬爾罕(Samarkand)、都城玉龍傑赤(Urgench)這三座花剌子模大城時,花剌子模的蘇丹逃往你沙不兒;可是他未整軍備戰,反倒沉迷於酒色。誠如志費尼所寫,「他眼中只有尋歡作樂一事。」「忙著安頓他心愛的女人,無暇訓練部隊,脫去他后妃的衣服時,忘了釐清重要事務的混亂。」這位蘇丹及其僕人縱情於宴飲,當蒙古人抵達時,他醉得不省人事,直到僕人往他頭上潑冷水,才把他叫醒。一二二○年五月十二日他放棄了你沙不兒,往西逃向今日的伊拉克。
你沙不兒城民很識時務,完全未抵抗即開門投降,同意協助蒙古人追拿他們的前統治者:花剌子模蘇丹。蒙古大將速不台(Subodei)的軍隊抵達,波斯人獻上食物給士兵與戰馬享用。在蒙古人眼中,接受降民食物乃是極具象徵意義的舉動,不只表明得到被征服人民的歸順,更重要的,還表示蒙古人將接受他們,讓他們以屬民的身分繼續過活。此後,你沙不兒人還供應物資給為追捕花剌子模蘇丹而經過該城的其他蒙古軍隊。
有一短暫時間不再有蒙古人來。隨著城中蒙古部隊變少、隨著蘇丹已擊敗蒙古人的謠言傳來,城民開始蠢蠢欲動,等著想造反、報復。他們以為這波蒙古浪潮已過,迫不及待想擺脫蒙古人與先前蘇丹的統治。誠如志費尼對當時情形的描述,「誘惑的魔鬼在人腦裡下了顆蛋。」
這些穆斯林似乎不知道蒙古軍隊的主力還未到。因此,一二二○年十一月,成吉思汗的女婿脫忽察兒(Tokuchar)跟著一支萬戶部隊抵達時,他其實屬於成吉思汗么子拖雷所統率的主力部隊的前鋒。第三天,脫忽察兒遭防禦土牆射出的箭擊中,不久後身亡。根據志費尼所述,這些波斯人完全不知這名倒下戰士的身分,因此當他的軍隊撤退時,他們以為自己打敗了蒙古人。此後直至來年春天降臨之前,你沙不兒的城民似乎都認為他們已成功且一勞永逸地趕跑了蒙古人。你沙不兒守軍有三千把弩、三百具攻城機,還有可以點燃、用來從防禦土牆拋向蒙古人的石腦油。
蒙古軍於一二二一年四月七日星期三早上進攻。星期五午禱時,蒙古軍已將護城河填平,首次在城牆打出缺口,在他們所控制的一段城牆上,得意地升起他們的旗子。雙方繼續激戰,當天晚上和隔天一整天,蒙古人不停進逼,終於拿下整個城牆和所有防禦工事。根據許久以後所寫的一份可信記述,七萬守軍死於你沙不兒之役。
你沙不兒的城民突然間被困在自己的城牆裡。對蒙古人來說,這正是他們獵捕野獸的一貫做法—拉起圍欄圍住野獸,然後恣意宰殺。首先,脫忽察兒的遺孀、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女兒,堵住流入城中的水,下令要城民出城。你沙不兒城民被趕到平原上後,她帶著侍衛進城,搜捕拒不出城者。
蒙古人打獵時總會放掉部分獵物,讓牠們得以繁衍。同樣的,即使全城的人都該死,蒙古人仍會留一些活口。脫忽察兒的遺孀從中挑出日後可能有用的工匠。蒙古人極看重有專門技能的人(從冶金或寫作到木工與織布),但戰敗的軍人或沒有技能的人(富人也在此列),對他們沒有利用價值。
在汪古部背叛她、殺死她丈夫後,阿剌海別乞仍替汪古人說話,保住他們的性命。相反的,成吉思汗這位女兒覺得自己與殺死她丈夫的叛亂者沒有關係,於是下令燒掉這座無人城市,然後將所有人處死,只留下挑出的工匠。套句編年史家華恩達米(Khwandamir)的話,「她讓城裡再也沒有會動的東西。」據說遭處死的人數達一百七十四萬七千人,實際人數應該只有這數據的百分之一左右。儘管如此,仍說明了蒙古人恐怖的程度。熱愛祖國城市的波斯編年史家志費尼描述道,「大肆報復時,連貓、狗都不得活命。」蒙古人處理完你沙不兒城時,「房舍全被剷平」而「玫瑰花園成了火爐」。
穆斯林學者認為,這個女兒可能是禿滿倫,但波斯原始史料未提及她的名字。蒙古人攻占的城市太多,無法用文字一一記錄,因此上述說法也未出現在蒙古人自己的文獻裡。除非有不為人知的新文獻問世,否則這公主究竟是誰,永遠都會是個謎。
在蒙古人攻占的一長串城市裡,你沙不兒的戰略意義不大,但該城的文化地位,以及該城落入異教女人手中之後的駭人下場,讓你沙不兒的失陷在穆斯林世界引發深深的恐懼。當時任何受過教育的穆斯林,大概都深切感受到蒙古人所預示的、隱隱逼近的毀滅命運。著名波斯詩人歐瑪爾.海亞姆似乎早在詩中預見:「不管是你沙不兒或巴比倫,生命之酒一滴滴不斷流逝;生命之葉一片片不斷落下。」
伊斯蘭與基督教的編年史家,以這個姓名不詳蒙古公主的故事,作為蒙古人作戰時野蠻的代表性證據,同時提及按性別、年齡堆成的一座座頭骨丘,提及征服者攻城後連貓狗都不留活口的冷血無情。這些史家描述蒙古人的征戰經過時,一再提到這些情景,在記載喪命人數上似乎力求精準的他們,卻未費心寫出讓敵方軍隊與平民都嚇破膽的那名女人是誰。這些編年史家只說她是成吉思汗的女兒、拖雷將軍的姊妹、戰士脫忽察兒的遺孀。
對於這些有關蒙古人的駭人故事,成吉思汗不思消弭,反倒予以助長。鑑於兵力上敵眾我寡,鑑於他所欲征服、控制的人民為數眾多,他知道打勝仗除了要靠軍隊,還要靠宣傳和公關。自小在備受欺凌的環境中長大,讓他在洞悉人最想要、最害怕的事物上,有著過人的本事。在打造其帝國時,成吉思汗總是設法利用人性的這兩個弱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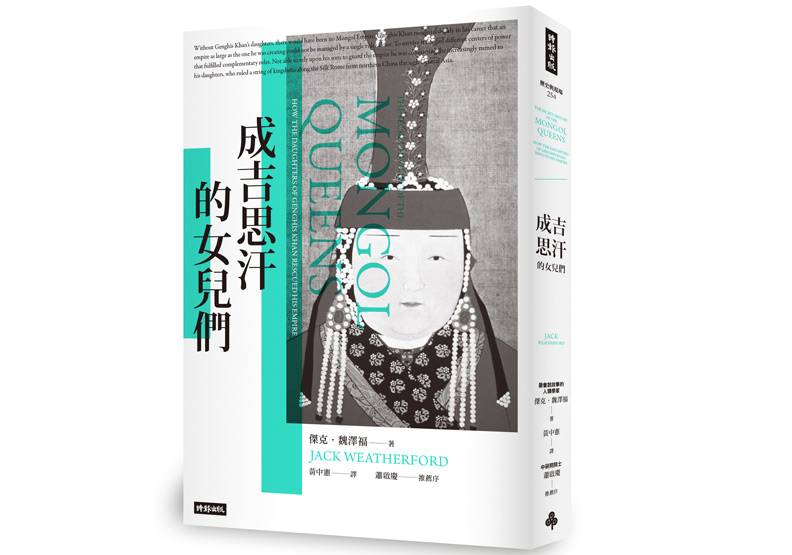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成吉思汗的女兒們》一書,傑克‧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著,黃中憲譯,時報文化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