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到處都有賣肉羹、魷魚羹的店家,夜市中要是沒有這兩味,就不能稱之為夜市。把魚肉與麵粉攪拌成魚漿,用瘦肉塊為餡,沾著魚漿,盈握為度,捏成塊狀,滾水煮熟,再放入大鼎中,與大白菜同燉煮,調味勾芡,即成肉羹。嗜海味者將肉塊代以發泡好的魷魚,稱魷魚羹。食用之際,佐以烏醋、胡椒,更令人垂涎。這兩種羹可以單獨享用,也經常與滷肉飯搭配,頗有公不離婆,秤不離砣的休戚與共。好事者多所傅會,說肉羹也是臺灣的獨一份。其實,羹的歷史,跟人類知道用火的時間,相去不遠。中國人從知道祭天祀地開始,就有羹,至今不衰。
夏、商、周三代,只有天子可以祭天,諸侯僅可以祭祀一些地方神祇,祭品往大鍋裡煮,熟了以後上供。這口鍋不一般,稱為鼎,因為有祭天祀地的功能,也就象徵權力,「鐘鳴鼎食」者,幾家能夠?楚國要挑釁周天子,特意派人去問鼎的大小,準備複製一套,中國成語故事就多了個「問鼎中原」。臺灣人至今稱鍋為鼎,仍是保存漢語古風。
鼎裡煮完祭祀用的牛、羊、豬,湯汁當然不能丟,放點穀類作物、蔬菜,煮成一鍋,稱為羹,《說文解字》說:「凡羹,齊宜五味之和」,自然可以當做祭品,或是薦於祖先,稱為「大羹」。羹字从羔从美,味道美甚,故祭祀時不調味,有「大羹不和」的說法,《左傳》多處提到大羹祭祀。《禮記》則介紹一般家庭食用「鶉羹、雞羹、雉羹、脯羹、犬羹、芼羹」,算是家庭食譜。一家人圍著一口大鍋,燉煮小型動物做羹,分而食之;如果加上野菜,則稱芼羹,更適合家庭食用。兩千年以下,仍可以想像當時的滿足。
周代另有一道菜,湯鍋放肉與稻米,煮成一鍋,稱為糝,也是八珍之一。《說文解字》解釋:以米入羹為糝。徐州一帶,糝至今仍是特色佳餚。閩南語稱稀飯為「糜」,臺灣有個類似「糝」的小吃曰「肉糜」:米飯與瘦肉片同煮,加新鮮筍子。味道極佳,應該就是晉惠帝嗜食之物。宋代以後,北方人稱糜為「水飯」,孟元老提到開封夜市有專賣「水飯」的店家。
除了水飯之外,開封美味還有羹,尤其瓠羹、縷肉羹、肚羹之類,相當普遍,許多店家都會做。這時候,羹的意思有點變化,麵條與肉類同煮,也稱羹,「合羹」應當是大碗的打滷麵;半份則稱為「單羹」。原本吃羹只用匙即可,一旦加上麵條,可就得使筷子,所以孟元老說原本吃羹用匙,「今皆用箸矣」。臺灣也有「羹麵」,應該就是宋代的合羹,打滷麵也相當類似。
現代,北方方言基本不稱羹,凡是以汁液為主的食物,多稱為「湯」。湯字本義為熱水,〈九歌〉有「浴蘭湯兮沐芳」的說法,可以為證。至今閩南語形容湯水滾沸為「湯湯滾」。所謂「香湯」,用以沐浴,並非飲料。作為飲料的湯,大概只有中醫的湯劑。魏晉時期,有湯餅一味。三國時期的學者何晏,臉甚白,皇帝懷疑他擦了粉,特別在炎夏宣他進宮,給熱湯餅吃。何晏不免出汗,臉上卻沒有糊妝之窘態,說明他並非擦了粉。《正字通》說湯餅是水麵,應當是今日的湯麵,與羹自有分別。唐詩說「三日入廚下,洗手做羹湯」,羹與湯雖並稱,概念並不模糊,宋代人進飯館後,先有人端湯倒茶,再進餐。
元代以後,羹、湯之間的區別漸泯,甚至羹、湯不分。例如《飲膳正要》提到葵菜羹,有順氣功能,作法是用羊肉、良薑等物,熬成湯,放入羊肚、羊肺、蘑菇、胡椒、白麵,再以蔥、鹽、醋調和。團魚湯也是羊肉熬湯,加上甲魚塊、白麵條、胡椒,蔥、鹽、醋調和。作法與內容都類似,卻有的叫湯,有的稱羹。
羹、湯主要的差別在於湯汁是否濃稠。將富含澱粉的穀類作物放到肉汁燉煮,自然濃稠,稱之為羹,閩南語中至今仍是如此定義。如果湯汁並非濃稠,則稱做湯,蘿蔔湯、排骨湯都是,並不混淆。所以店家製作肉羹時,也都勾芡。這樣的作法,也見於洛陽水席之中。
吃羹,湯湯水水,必須有較大的容器,古人多用盆,莊子鼓盆而歌,又留下「鼓盆之痛」的成語。包公傳奇中,所審的烏盆非洗臉裝水之用,也是用來吃羹湯的食器。有一年到南韓開會,朋友介紹典型的韓國食物,早餐為牛雜湯飯,放在盆中。上桌一瞧,立刻領悟莊子所鼓之盆為何,挺有意思。
(照片╱攝影:張智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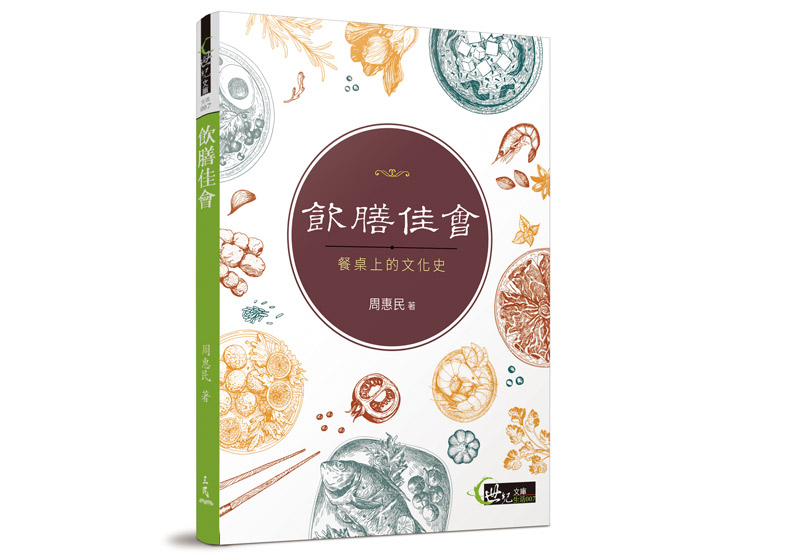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飲膳佳會:餐桌上的文化史》一書,周惠民著,三民書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