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淨土
對猶太人來說,拜占庭帝國很快就出現了一抹曙光。猶太詩人曾將這個帝國比喻為但以理在精神迷亂的夢中獲得的啟示―長著十隻角和鐵齒、銅爪的第四隻野獸。即使如此,這一切總會過去的,因為這十隻角最終會轉過來攻擊這隻孕育他的野獸。對於一個好戰、始終懷有統一基督教帝國的偉大夢想的羅馬皇帝來說,查士丁尼所能做的大概只有這麼多了,關於改建猶太會堂為基督教堂的法令從來也沒有嚴格執行。據我們所知,只有一個相對重要的例證,就是約旦東部的哲拉什(Jerash)。那裡有一座建於西元四世紀、非常漂亮的猶太會堂,於六世紀三○年代初被改造成了基督教堂。對於那些鳩占鵲巢的基督徒而言,猶太人的建築顯然過於華而不實。因此,猶太會堂裡描繪挪亞洪水的鮮豔華麗的鑲嵌畫(幸運的是,其殘片得以單獨保留了下來)被鏟掉,並換成了更莊重的幾何造型設計,只剩下一些動物—綿羊、鹿和公牛―依舊平靜地在碎石間吃草。
查士丁尼自己當然也明白,集體皈依畢竟不是一夜之間就能成就。他的計畫基本上是按照奧古斯丁的思路設計,只是希望順勢讓猶太人皈依,而不是用棍棒脅迫他們改信基督。雖然已經禁止他們研讀《米示拿》,這在當時算得上是一項極其卑劣的措施,但他卻愚蠢地忽視了如下事實:既然這本書記述的是口傳律法,那麼其中大量的內容,早就已經內化於猶太人的社會習俗與律法行為之中。在另一項法令中,查士丁尼竟然規定猶太人在會堂裡必須用希臘語誦讀《妥拉》(每三年通讀一遍),其實在許多地方他們早就這麼做了。當時使用的版本是亞歷山大的《七十士譯本》,即由耶路撒冷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人翻譯的經文本。
基督教的羅馬帝國以為這樣就可以加速希伯來語的消亡,但顯然為時已晚。這種《聖經》的語言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正在進入一個充滿活力和不斷創新的新階段。《塔木德》的兩個新版本―「耶路撒冷版本」(在加利利人完成)和「巴比倫版本」,後者就是在巴比倫的蓬貝迪塔、尼哈迪亞(Nehardea)和蘇拉猶太研究院中寫成的。其中為《米示拿》增補了大量的評注,形成了所謂的《革馬拉》。他們正是用這種方式創立了一個龐大的、驚人的、具有漫談式風格的希伯來文文學體系。其內容不拘一格,從流傳已久的神秘傳說到時常發生的律法辯論,可以說應有盡有。這部《塔木德》篇幅宏大,幾乎無所不包,不僅可用作律法指南以及平日的自省、啟蒙和討論,同時也是一種啟發甚至娛樂的方式。
《塔木德》是那些學術聖哲(當時稱「阿莫拉」)的宗教王國。希伯來文學的另一種形式也起源於這一時期。其不僅為學者和法官階層所採用,而且也體現在猶太會堂普通會眾的誦讀聲中。在當時的巴比倫,猶太會堂大多為拉比的私有財產,通常就設在他們自己的家裡。有些拉比(當時稱「拉布」﹝Rab﹞)現在依然如此。實際上,這是原來「經文講習學校」(Beit Hamidrash)的一種延伸形式,前來學習的主要是他們的門徒。而在巴勒斯坦,由於咄咄逼人的基督教會和充滿敵意的皇家法令,猶太教日益陷入了重重困難之中,但那裡的猶太會堂仍然是公共活動場所。那些被蔑稱為「當地人」(am ha’eretz),即無論在世俗社會還是宗教界都算不上貴族階層的人,平時可以與名字往往非常顯眼地鐫刻在鑲嵌畫上的當地顯貴,和祭司、利未人一起討論問題。對他們來說,用激情洋溢的希伯來語創作的「新詩歌」(piyyutim)無疑是一種在逆境中安慰會眾的精神力量。
在正式祈禱—按慣例要誦讀「示瑪」和經匣中的內容並用立禱(amidah)的方式背誦「十八祝福詞」—的間隙以及誦讀《妥拉》之前和之後,唱一首聖歌或吟一首新詩也算是情感的調劑和抒發。一些最早創作的詩歌節奏很快,顯然是為了在舉行莊重的儀式之前吟唱,比如像新年節期間反覆吹響羊角號。並且在後來許多不同的版本中,這一階段所寫的新詩仍然延續了這種風格。一些流傳最廣、最受歡迎的詩作,例如<幸福>(Ashrei)、<永恆的主>(Adon Olam)、<讚美上帝>(Yigdal)、<除我們的主外沒有別神>(Ein Keiloheinu)(註一),則是後來中世紀的作品,以至於連平時不常參加正式祈禱儀式的猶太人也耳熟能詳。當然,要確定創作的具體日期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些詩歌大部分來自中世紀的「福斯塔特(Fustat,開羅的舊稱)秘庫」中保留下來的猶太文書殘片。但根據其鮮明的風格,可以確定最早的「新詩」應該寫於西元六世紀至七世紀。
他們創作的這些感情強烈的詩行,是一種情緒的宣洩,是用詩歌的形式對迫使他們痛苦地分離出來的壓迫者發動一次反擊。事實上,他們並不掩飾自己內心的仇恨。「度瑪(Dumah,即以東,指羅馬人)的統治者將被擊敗,他們將匍匐在地,像蟲子一樣舔地上的泥土。」雅乃(Yannai)在一首詩中寫道:「讓以東的土地上發生大屠殺,願他們的田地裡燒起大火。」他的學生以利亞撒.本.吉利爾(Eleazar benQillir)甚至寫下了一些詛咒他們遭到報應的血腥詩行:「打倒以掃的兒子,張狂一時的惡棍,讓他們斷子絕孫,妻子守寡。」或許這些帶著火焰和硫黃的詩行會應驗在他們自己和同胞的身上,因為據說雅乃非常妒忌他的學生吉利爾,於是把一隻蠍子放在他的鞋子裡把他毒死了。
但其中最早的一位詩人,即西元六世紀在巴勒斯坦從事創作的約西.本.約西(Yose ben Yose),曾將《聖經》及其闡釋者作為在哀痛中希望彌賽亞降臨的一種載體。他的聲音是屬於猶太會堂的,《雅歌》中的新娘被完全人格化,她在不斷加深的絕望和悲痛中,等待著上帝化為新郎出現在她的面前。不義之人把上帝趕跑了,她只能在他曾經顯現過的老地方即海洋和曠野之間徒勞地尋找。但希望的種子畢竟留了下來:「他會在他的心裡為我播下永遠的印記,就像他在蘋果樹下用一個聲音把我喚醒一樣。」鳥鳴聲變成了悲慟,就彷彿鴿子也在痛苦地哀悼。「埃及飛來的麻雀在曠野中哀鳴/亞述的鴿子也想發出聲來/去看看那些麻雀,找到那些沉默的鴿子/為他們吹響號角吧。」於是,新郎回到了會堂,通過對罪行的懺悔和對救贖的期待,羊角號暗示的期望中的彌賽亞終於降臨,以東人垮臺了,耶路撒冷得到了重建。僅僅通過這些詩歌的片段,你完全能夠感受到那些時至今日仍然在舉行的猶太會堂儀式歷歷眼前(就像基督教堂中相應的各種儀式一樣):祈禱、誦讀和祝福聲和諧地融為一體,並不時夾雜著一些虔誠的詩句和讚美的聖歌。
無論猶太人是否流落到世界各地或被驅逐到巴比倫,早期的虔誠詩歌都應該是遙遠的猶太社區遭到壓榨和迫害的產物。因為他們依然沉浸在對耶路撒冷的強烈思念之中,如此之近但又如此遙遠。與創作「新詩」的詩人們強烈的奮發向上情緒不同的是,那被約西.本.約西巧妙譽為「像在吃著『細心』製作的無酵餅」的《巴比倫塔木德》,則表現出與「新詩」相反,極其冷靜的風度。《塔木德》的風格,另一種源於昆蘭神秘主義即所謂「天宮」(hekhalot)文學的詩歌卻屬於另一個世界。「天宮」這個名字意味著天上宮庭,在那裡,純潔的信徒升天後,可以看到坐在寶座裡的上帝的真實面容和形體。
但是,《塔木德》卻是另一個世界的作品,是薩珊王朝統治下波斯的巴比倫的產物。那裡的猶太人,完全擺脫了在基督教領上遭受的極大的恐懼和不斷被魔鬼化的折磨。猶太人不會因為先知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升天而受牽連。實際上,聖典《阿維斯陀經》(the Avesta)中甚至根本沒有提到他的死亡。在被波斯征服後的四個世紀裡,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位於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城市,如尼哈迪亞、蓬貝迪塔、蘇拉和瑪霍札(Mahoza),即薩珊王朝首府泰西封(Ctesiphon)的周邊地區,那裡的城市生活並未完全免於戰亂。西元四世紀中葉,在伊嗣埃二世(Yazdegir Ⅱ)和卑路斯(Peroz)統治下曾發生過兩次迫害猶太人的事件。但大多數情況下,那裡的猶太人幾乎沒有受到拜占庭基督教帝國的影響。
在波斯人的保護下,猶太人和猶太教一度非常繁榮。在拜占庭帝國的領土內,猶太人不能對非猶太人提出指控,甚至不能作為證人出庭。但在波斯的巴比倫,他們享有與其他人一樣的法定權利。因此,猶太人在波斯人的法庭上就像在自己的法庭上一樣。一位名叫撒母耳的資深拉比曾明確表示:「(民)法就是有效的法律。」猶太族長(resh galuta)的地位略低於波斯貴族,但其權威得到當局承認。他們的日常生活時尚而高貴,享有直接進入薩珊宮廷的權利。與拉比和聖哲在《塔木德》研究院裡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是,猶太族長往往擺出大衛王室的最後一位傳人約雅斤(在第一聖殿被焚毀之後流亡巴比倫)後裔的派頭。當時流傳著大量有關猶太族長與波斯國王之間過從甚密、關係融洽的故事。西元五世紀初,猶太族長胡那.本.拿單(Huna ben Nathan)曾與伊嗣埃一世一起參加祭祀儀式,當時他穿著和瑣羅亞斯德教祭司的法袍(kustig)幾乎一樣的長袍,當他的腰帶滑落下來時,國王甚至體貼地親手幫他繫上。
所有這些,只是因為猶太教並不是瑣羅亞斯德教故事傳說中的角色,至少沒有扮演弒神的角色,所以波斯人覺得沒有受其威脅,兩種宗教甚至還有許多教義有共同之處,都非常看重死者的潔淨,認為月經和遺精是不潔的。這樣看起來,猶太人把修剪下來的指甲屑掩埋掉的特殊要求,很可能直接來源於波斯瑣羅亞斯德教的習俗。當然,如果這裡的猶太人兜售護身符和咒符(與其他地方一樣,這種生意在巴比倫非常流行),肯定不會有人懷疑他們是在販賣邪惡的工藝品。
由於生活在一個世界上最擁擠和最複雜的城市化社會中,那些說亞蘭語的猶太人的居住條件,以及其他所有方面都居於富有階層和貧窮階層之間。他們是河運生意人也是碼頭上的搬運工,是放債人也是趕騾車的人,是醫生也是地主。因為《塔木德》是寫給各地和各種環境下的猶太人看的,所以這本書的作者記述了大量區別他們之間差異的人種學資訊。《米示拿》甚至把女人在逾越節期間使用的化妝品視為「酵物」,因而將其列為禁品。當然,那些編纂《塔木德》的聖哲不會寫下這句話就放下筆,因為他們緊接著又對小女孩使用脫毛劑這個問題作了種種規定。關於這個問題,作為專家的拉弗.猶大(Rav Yehudah)說:「沒錢的女孩用檸檬(唉唷唷……),有錢的女孩用精麵粉,而公主(「猶太公主」第一次在文獻中出場)六個月用一次沒藥的油。」他們這種漫無邊際的開放式聯想,自然而然引起了一場關於「沒藥的油是什麼」的大討論。當時,拉比們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但卻都沒有搞清楚。因為他們似乎認為這種精油來自未成熟的橄欖,實際上,這是一種從帶刺的沒藥植物的果實榨取的汁。除非在巴比倫橄欖油是作為脫毛劑出售的,否則拉比們就不得不進一步制定判斷化妝品真假的標準了。其實,他們不過是希望有錢的女孩(猶太公主畢竟是少數)在逾越節期間皮膚不要沾上麵粉。
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希望在逾越節家宴上沒有任何沾染麵粉的嫌疑,因為他們已經規定,絕對不能用以東人(羅馬人)的醋,也不能用大麥釀製的「米甸」(Median)酒。但這卻進而讓拉比們(不過沒有什麼像樣的理由)不僅對化妝品,而且對有可能使腸胃停止或放慢蠕動的食物也發表一番高論。不要大驚小怪,普通大眾吃的當然是「有利於排便,不利於長高,並剝奪他眼睛的五百分之一光明」的食物,這無非指的是黑麵包、半生不熟的蔬菜和釀製時間不足的啤酒。要改變這一切,你首先要有精粉麵包、特製的葡萄酒和大量的肥肉(最好是未產過子的母山羊肉)才行。聖哲們的營養專業知識像他們關於脫毛化妝品分類的建議一樣無聊。
儘管《塔木德》就生活中幾乎每一個可以想像到的細節提出了各種瑣碎的建議,並且有些的確有待商榷,但《塔木德》仍不失為一部有血有肉的經驗著作,而不是枯燥的律法指南。可以肯定的是,《塔木德》並非文化隔離的產物,而是產生於一個猶太生活對周圍的文化始終開放的世界,當然更談不上是《妥拉》猶太教妥協的結果。從這意義上講,《塔木德》詳細討論了所有的問題和困惑,回答了在長期散居生活中一直困擾著猶太人、有關「開放與封閉程度」的所有問題。有趣的是,正是因為波斯巴比倫的社會習俗與猶太習俗,尤其是在潔淨問題上竟然如此一致,所以對於應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改進巴比倫人的習俗這問題上,不僅普通大眾,甚至《塔木德》的編纂者們也產生了分歧。誰有資格在法庭的案件審理時作證?對這個問題,波斯律法採取了一種包容的態度。對此,有的拉比予以認可,有的則不予認可。例如,生活在瑪霍札城郊上流社會的拉比納曼.本.雅可夫(Nahman ben Yaakov)是猶太族長的親戚。他就認為讓一個曾和已婚婦女調情嫌疑的男人當證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與之類似,勤勞多產的《塔木德》編纂人拉瓦(Rava)也認為,一個以喜好﹁不可食﹂食物而名聲不佳的猶太人,不應該在作證時遇到任何障礙。而來自蓬貝迪塔研究院,相對狹隘的猶太社區的拉比阿巴耶(Abaye),則對以上兩種情況都持否定態度。這種分歧主要體現在巴比倫猶太人中富有、悠閒的精英階層,以及生活相對簡樸和封閉的學術圈子裡的猶太人之間。許多屬於前一類人的拉比,平日過的是一種波斯傳統的一夫多妻生活,允許丈夫在國外時擁有「臨時的妻子」,他們不認為有理由要求他們與元配離婚。
當然,《塔木德》編纂者觀念上發生分歧,並不僅僅是出於社會地理學方面的原因。那些用狹隘眼光和用更寬廣的胸懷闡釋《妥拉》和《米示拿》的人之間之所以發生分歧,或許只是因為他們的思路有所不同。關於《塔木德》這套書本身,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靈活性:不時用大量的篇幅記述各種聲音、相互插話甚至兩代人之間吵架般的對話。《塔木德》是這個世界上第一部「超文本」,它往往在同一頁上為各種評注甚至評注的評注、引文的引文留下大量的空白―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不同的論點、手跡甚至不同的文字(其中收入了一些亞蘭譯文)密密麻麻地寫在羊皮紙上,而猶太人直到西元九世紀才使用所謂手抄本(圖書複製的早期形式)。這種羊皮卷軸的形式使得本來已經很鬆散的《塔木德》更加鬆散,隨意轉動的卷軸意味著源源不斷的自由聯想,在那些律法、故事、幻覺和爭論之間流淌出各種奇思妙想。《塔木德》的權威性是與其口傳傳統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它完成了從直覺到對話的飛躍,就像一道無法阻遏的光芒閃過,不必在意這道光芒與所討論的問題表面上有什麼關聯。無論在哪裡,當你沉浸在《塔木德》字裡行間時,與其說你在讀,還不如說你在聽。
當然,你也是在用眼看。請看:兩位當時非常重要的拉比,希亞(Hiyya)和約拿單正走過一片墓地。約拿單長袍上的邊穗拖到了地上。「還是提起來吧,」希亞說,「不然這裡的死者就會說:『 他們明天就會來和我們作伴,今天竟然在嘲笑我們。』」約拿單(讓我猜猜,他是一邊走一邊提了提他的長袍,還是停下來指著對方呢?)答道:「你說什麼呢?死人會知道什麼?難道《傳道書》中不是說『死人一無所知』嗎?」(註二)希亞開始激動起來。「拜託啦,如果你真的讀懂了的話,你就該知道『生者』指的是義人,即使死了也還活著,而無知的『死者』無論生死,永遠是『無知的』惡人。」
《塔木德》中有關安息日的經文純粹是為了方便講故事來斷句的,希列和沙買的故事尤其如此。為了弘揚忍耐的美德,其中有個故事說的是一個人打賭他能激怒平日以冷靜著稱的希列。在一個安息日之夜,這個打賭的人猛敲希列家的門時,「希列正在洗頭髮」(《巴比倫塔木德》喜歡描述這樣的細節)。聽到敲門聲,希列急忙披上一件長袍,問他需要什麼。「我有一個問題。為什麼巴比倫人的頭是圓的呢?」希列甚至連肩都沒有聳一下:「因為他們的接生婆太不專業了。」哦,是這樣。過了一個小時,他又回來了。「那為什麼帕爾米拉人的眼睛會疼呢?」「我的孩子,問得好。因為他們住的地方沙太多。」就這樣,你問我答持續了好久。即使當這個討厭的陌生人挑釁地說「我有很多問題」時,這個偉大的人也沒有一點煩躁的跡象。「你想問什麼就問什麼。」「那好吧,他們說您是一個王子。在以色列,像您這樣的人可不多見。」「為什麼,我的孩子?」「因為您剛讓我輸掉了四百蘇茲(註三)。」希列知道他已經黔驢技窮,但仍然溫和地說:「你輸掉四百蘇茲,總比希列發脾氣好吧。」
像《米示拿》滿篇都是解釋、評注和民間的智慧故事一樣,篇幅更為宏大的《塔木德》儘管看上去似乎敘事無分巨細,但實際上論述的卻是最深刻的倫理準則。什麼時候可以合法地休掉妻子呢?(只有當她對婚姻不忠時才能達成離婚協定,因為「以色列人的主上帝說:『我討厭離婚。』」)什麼時候生死大事比守安息日還重要呢?(通常的做法是,如果需要,你必須先把水燒熱。(註四))最感人而直白的是(耶路撒冷《塔木德》反映出巴勒斯坦的悲傷,或許在西元五世紀薩珊人才突然變得對猶太人不怎麼友善)聖哲們竟然自言自語地問自己,面對非猶太人急於皈依猶太教應該如何表態?「我們對他說:你為什麼要皈依呢?難道你不知道現在的以色列人正憂心忡忡、精神緊張、受人輕慢、遭到騷擾和迫害嗎?如果他回答說:『我知道,我自己不配(分享他們的愁苦)。』我們就立即接受他。」
然後,他們會告訴他哪些誡命很難堅持,哪些誡命容易遵守。並告訴他違犯誡命會受到懲罰,而遵守誡命則會得到獎賞。
在巴比倫散居地,不論生活如何容易(但並非一直如此),若有人要獲得塔木德式猶太教的接納就不只意味著要分享那些失落的痛苦回憶,而且還要去感覺、去看、去聽,就好像那些痛苦仍然在發生一樣。其中有一篇問道:當巴比倫的軍隊最後在阿布月初九那一天摧毀了進入聖殿的通道時,利未人站在高臺上在唱什麼呢?當貝塔爾(Betar)村落入哈德良軍隊之手並且「聖殿山被犁平」時,是什麼樣子呢?當然,他們也可以分享那個期待中的彌賽亞世界,當某些事情終於發生的時候—「以東人」(羅馬人)垮臺,上帝像新郎一樣回到耶路撒冷聖殿,來到等待著他的新娘會堂面前,回到那些一邊看著他們,一邊祈禱、誦讀《妥拉》、高聲吟唱著「新詩」的猶太人面前—安著金色大門的聖殿及其內廳正中間掛著「幔子」的至聖所,必將得到重建。
有的時候,《塔木德》中的拉比、猶太族長及其猶太法庭以及廣大的普通大眾都認為,最黑暗的時刻意味著曙光即將來臨。西元七世紀初,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烏斯(Heraclius)似乎完全陷入了傳播基督教福音的狂熱之中。他在法令中宣稱,猶太人除了皈依基督之外沒有其他的路可走,必要時可以採取強迫手段。因為他們只有信奉基督才能獲得拯救,而只要他們還在盲信,他們就是危險的,因為他們是魔鬼的造物。與此同時,赫拉克利烏斯還禁止在工作日舉行祈禱儀式,試圖從根本上滅除猶太教,並規定在任何時候都不得背誦「示瑪」(據說,當時的領誦人在祈禱儀式上會通過隨意插入「示瑪」的方式規避這一規定)。就我們所知,在拜占庭—羅馬帝國的各猶太散居地中,只有一個社區被迫集體皈依了基督教,這個社區就是馬格里布地區的鮑里姆(Borium)。
但在赫拉克利烏斯的宏大計畫得以實施之前,卻突然發生了充滿彌賽亞色彩的重大事件。西元七世紀初,薩珊國王霍斯勞二世(Khosraw Ⅱ)決定鼓動他的領地內的猶太人,希望他們支持由其將軍沙巴赫拉茲(Shabahraz)指揮的一次針對拜占庭帝國的軍事行動。據說,當時的猶太族長的兒子尼希米,動員了一支兩萬人的猶太後備軍與波斯人聯合作戰。他們一路進軍,突破了拜占庭人的防線。安提阿這座代表著基督教帝國榮耀的中心城市被攻陷,從加利利的猶太核心地帶―賽佛瑞斯、拿撒勒以及提比利亞當地―招募的猶太後備軍,由提比利亞的班傑明率領,也加入了波斯的遠征軍。他們勢如破竹,直抵猶太地。經過三個星期的圍困之後,猶太人終於奪回了原本屬於他們的城市(從哈德良發布禁令以來還是第一次),隨即在波斯帝國的領地內建立了一個猶太自治城邦。
「殉教聖徒名錄」(Martyrology)記述了基督教會和基督徒在這次戰爭中所遭受的毀滅性創傷。幾乎沒有基督教堂的遺跡在歷代的考古中被發現,但至少在瑪米拉(Mamilla)池塘邊的一個耶路撒冷遺跡發掘現場發現一些遺骸。現在那裡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型購物中心和高檔住宅區。無論猶太人是不是曾經向迫害他們的占領者復仇,當時期望中的彌賽亞並沒有降臨。幾乎在清理和重建工作開始之前,波斯人就已經奔向前方新的戰場,看來他們是要讓耶路撒冷和猶太人自生自滅。西元六二八年,在赫拉克利烏斯的軍隊被擊敗僅僅十四年後,他們便捲土重來,更變本加厲地實施報復。基督徒們肯定在想,猶太人的再次失敗仍是他們盲目輕信造成的。因為除了耶穌基督再臨,根本就沒有其他的救世主。猶太人應該丟掉幻想,接受基督教的旗幟將永遠飄揚在耶路撒冷上空這一事實。
或許,基督徒們才更應該丟掉他們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吧!因為在西元六三八年,在他們重新占領這座城市僅僅十年後,穆斯林便在第二哈里發歐麥爾(Umar)的率領下,征服了耶路撒冷。根據後來猶太人和穆斯林文獻的記載,猶太人作為歐麥爾軍隊的嚮導,陪著哈里發來到了聖殿山的原址。據說穆罕默德就是在那裡升天的,並且在往來的路上還向猶太先知打聽過那裡的情況。當歐麥爾看到基督徒十年前為了污染聖殿而故意堆起來的那堆垃圾時,非常悲傷、震驚。據說他立即下令清理現場,猶太人當然巴不得做這項累人的工作。作為回報,他允許來自加利利的七十個猶太家庭住在耶路撒冷,他們後來在聖殿原址附近建起了一座猶太會堂。於是,一種猶太人和穆斯林和諧共存的文化,由此誕生。
不知閱讀至此的諸位,會怎麼看這段歷史?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們的故事。
註一:這些都是後來的猶太人在晨禱、晚禱或安息日祈禱儀式開始之前或結束之後吟誦的詩篇,各個時期和各散居點的猶太人或許選取的「曲目」會有所不同。
註二:參見《傳道書》9:5。
註三:古代猶太銀幣單位,《塔木德》中常與第納爾交替使用。一蘇茲為四分之一舍客勒,重十四至十七克不等。
註四:此處作者意為由於生死大事通常需要先燒水,因此違反了安息日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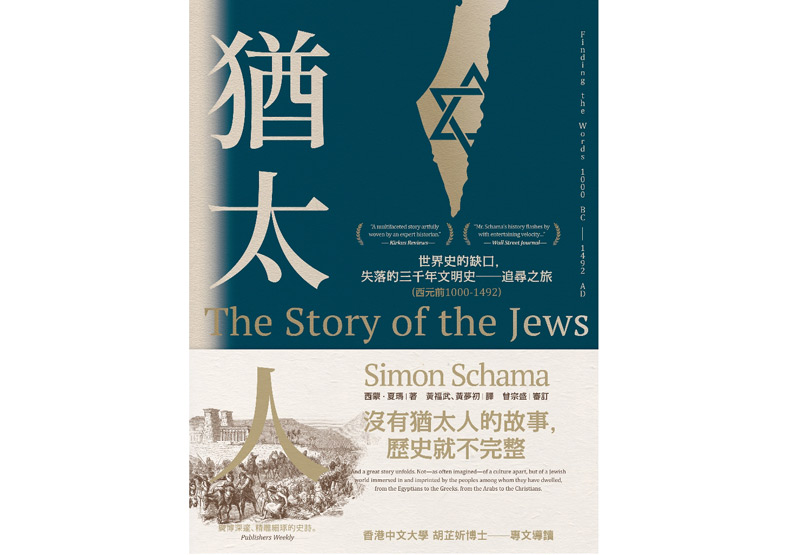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猶太人》一書,西蒙‧夏瑪(Simon Schama)著,黃福武、黃夢初譯,聯經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