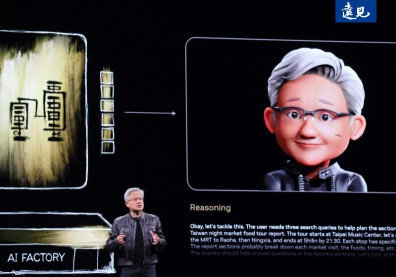楊德昌電影中的大都會特質和慣常使用的反諷手法,使他成為一個世界級的電影導演,不論後現代敘事或題材語言都能運用得如魚得水。很明顯地,《恐怖份子》的故事是圍繞著機會和命運而發展出的錯綜敘事,超前了整個時代。但電影中特殊的社會和文化隱喻,仍使楊德昌被辨識為一個台灣導演,他的創造力和這個島嶼的命運密不可分。在他的動畫網站Miluku.com中,這種台灣文化的特殊性最能清楚顯現出來。事實上,楊德昌最重視的就是動畫卡通網站,其他拍片計畫實為第二順位,這表示他非常相信未來動畫媒體會是一個趨勢,不論是在尋找資金或是創作前景上。至少現在網站能接觸到最廣泛的觀眾,他們大多透過科技產品接收資訊,而非透過特定組織。為了在電影產業中持續創作,楊德昌必須籌到足夠資金,也必須考慮所有契約、合約、協定,而為了既得利益,參與投資者會提出許多附帶條件。當時,製作、發行、映演等的電影產業體系裡,導演缺乏實際的權力,只是巨大資本網絡中的一個小小螺絲釘。反諷的是,隨著《一一》的成功,楊德昌正處於最顛峰的狀態,卻在此時決定不拍更多電影,要照自己的方式拍自己的電影。他朝網路動畫的方向前進,對於楊德昌而言,這是一種回歸,因為他擁有卡通繪圖、圖像設計的天份,也因為電腦工程專業的高學歷和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一一》為他早期電影中的一些問題提供了某種解答,或說綜合的呈現。在早期階段,即使大家非常讚賞楊德昌的故事大膽地在不同敘事和時空之間自由切換,但仍然有不夠自然的對話或演技,例如角色的說話方式過於正式、對白太不口語,給人一種做作的感覺。像是《海灘的一天》,譚蔚菁的前任男友佳森在將死之際,還先發表一串長篇大論。類似的對話也出現在《青梅竹馬》的阿隆和阿貞之間,兩人一本正經地談論著對未來的展望。這種笨拙的表現可能和劇本寫作有關,為此,侯孝賢和朱天文除了對當代都會的焦慮提出看法之外,也共同承擔編劇不夠好的責任。
類似的例子還包括《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Honey,以及《獨立時代》裡的作家,兩個角色均滔滔不絕地訴說著自己的內心想法。另外,《海灘的一天》在選角、表演和化妝造型上也有著明顯的瑕疵。張艾嘉當時已經將近三十歲,卻扮演一個十七歲的小女孩,她頭上的假髮看起來也不夠自然。譚蔚菁這個角色是一個廣受讚譽的鋼琴家,但鏡頭呈現上並沒有成功營造出她彈琴的樣子,很明顯地,飾演此角的胡茵夢並不會彈鋼琴。片中不時呈現傳統台灣人的家庭,父子、母女之間的互動卻讓人感覺過於生硬,彷彿身為外省人的楊德昌正闖入一個不熟悉的領域。他們雖然住在日式的房子內,在屋子裡竟然沒有脫鞋,而且這還是發生在楊德昌編寫及協拍於日本拍攝取景的《1905年的冬天》(1981,余為政導演)之後的事。
反觀《一一》,楊德昌的創作技巧可謂無懈可擊,不同於之前的黑色喜劇,此片鋪陳了溫暖的色調,發展出鳥巢狀的敘事結構,並結合之前通俗劇作品中的主題。這部片呈現嶄新的、自然的抒情文體,能夠優雅地平衡不同世代、不同戲劇謎面,以及各條平行的敘事線。片中的演技、對白也較為自然不做作,具有十足的說服力,可歸功於藝術大學學生的才華,以及台灣電影最天賦異秉的編劇吳念真。《獨立時代》、《麻將》中那份新興都市的過剩意識,逐漸轉變成對城市相互連結此一全球化現象成熟但哀傷的自覺。《一一》仍然保有一些過去的慣例,像是虛假的藝術、詐欺、騙局等情節,但這些部分處理得較為含蓄,彷彿是受到遙遠過去的影響。然而,在這個完全互相依賴的世界中,這些部分也已經無處可藏,反而瀰漫著一種對逝去的青春、理想主義、浪漫愛情的緬懷(nostalgia)。如同楊德昌電影裡的其他主角,已屆中年的N.J.(吳念真飾)和妻子(金燕玲飾)正處於低潮、失落的狀態。但他們的小孩正對世界好奇地探索,彌補了大人的缺陷,與婆婆的死亡練習形成平衡。大部分的時間裡,她都躺在床上陷入昏迷狀態,但婆婆的昏迷也是一個關鍵元素,造成一種失落、不平衡,也與整個社群的資本算計、權力平衡有關。
失蹤人口在楊德昌的電影裡是一個常見的戲劇元素,他們的缺席與資本和信心的失落有關,且同時是經濟上和心理上(情)的。基本上,楊德昌的所有敘事都是為了要解決一個謎團或難題,而每個故事都始於以「失蹤」為形式的錯位。例如,《海灘的一天》開頭始於尋找失蹤的丈夫;同樣地,《青梅竹馬》中消失的梅小姐則暴露出主角阿貞和阿隆的議題。而《恐怖份子》裡雖然沒有人真的失蹤,但整部電影的核心是延遲、錯置與等待。此外,Honey 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明確的失蹤角色,躲在台灣南部的某個角落。在Honey 消失的這段期間,牯嶺街的幫派上演著權力與女人的爭奪戰,但他回來時,卻無法重整秩序,而落得被謀殺的下場。《麻將》裡,策劃綁架的目的是為了要引出紅魚失蹤的父親,最後發現,他的父親與情婦在藏身處一起自殺。同樣地,《一一》的婆婆在長久的昏迷後醒來,然後逝去,將全家人再度凝聚在一起。
在楊德昌的電影結構中,這些失蹤的人事扮演著敘事和意識型態的關鍵。失蹤的事物反而會突顯出人際關係的整體系統和模式,而一旦此一失蹤的人事再度冒出,卻會出現另一個新模式,而非回復到過去的狀態。楊德昌的電影對改變快速的當代生活提出尖銳的觀察,也展現出消逝與回歸之間的抽象辯證。他的電影裡總會有一個不見的棋子,以此推動情節發展。整個風暴、角色的行為反應,都是在試圖重新建立平衡,而一旦失蹤的部分還原,原本的結構便會瓦解。回頭來看,仰賴失蹤以重新達到平衡其實是個假議題,因為故事的謎團並不會因為這個失蹤的部分就停滯下來,相反地,故事遮蔽了它。儘管人們試圖回復原本的秩序,它卻會自動發展出另一種新形態。失蹤者的遺跡只殘存在生者的心目中,總是掙扎著要重建過去的模式。電影常常描述顛覆、再重建的過程,這樣的行為可能含有些許救贖的意義。在楊德昌的世界裡,系統內發生的任何瑕疵都有獨特性,因此無法以部分替代的方式來修補受損的系統。當社會機器改變的速度比人類還要快,人會失去和社會協商的能力,因為失落的部分反而會讓人特別意識到它的存在,但人往往無計可施,只能不斷嘗試。過去,台北的都市空間是由一條條的鐵路形構,而今卻遭架高的公路、地下運輸系統取代。透過失蹤的人和重建的需要,表現出人們的社會關係也處於變幻莫測的狀態中。楊德昌過去用導覽(navigate)的方式帶領觀眾,而現在用巡覽(netvigate)的方式讓觀眾認識適應社會、人的毀滅與限制。
透過拍攝《一一》,楊德昌放下了過去對僵化的當代文化和商業體系的不信任。他讓自己與都市和解,雖然都市人經常猶疑不定,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只是一味地想念失去的東西。他靜靜地從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運作方式中退出,尤其是其中的種種資本競爭、商品需求,單純地接納了人類存在現況中的不完美和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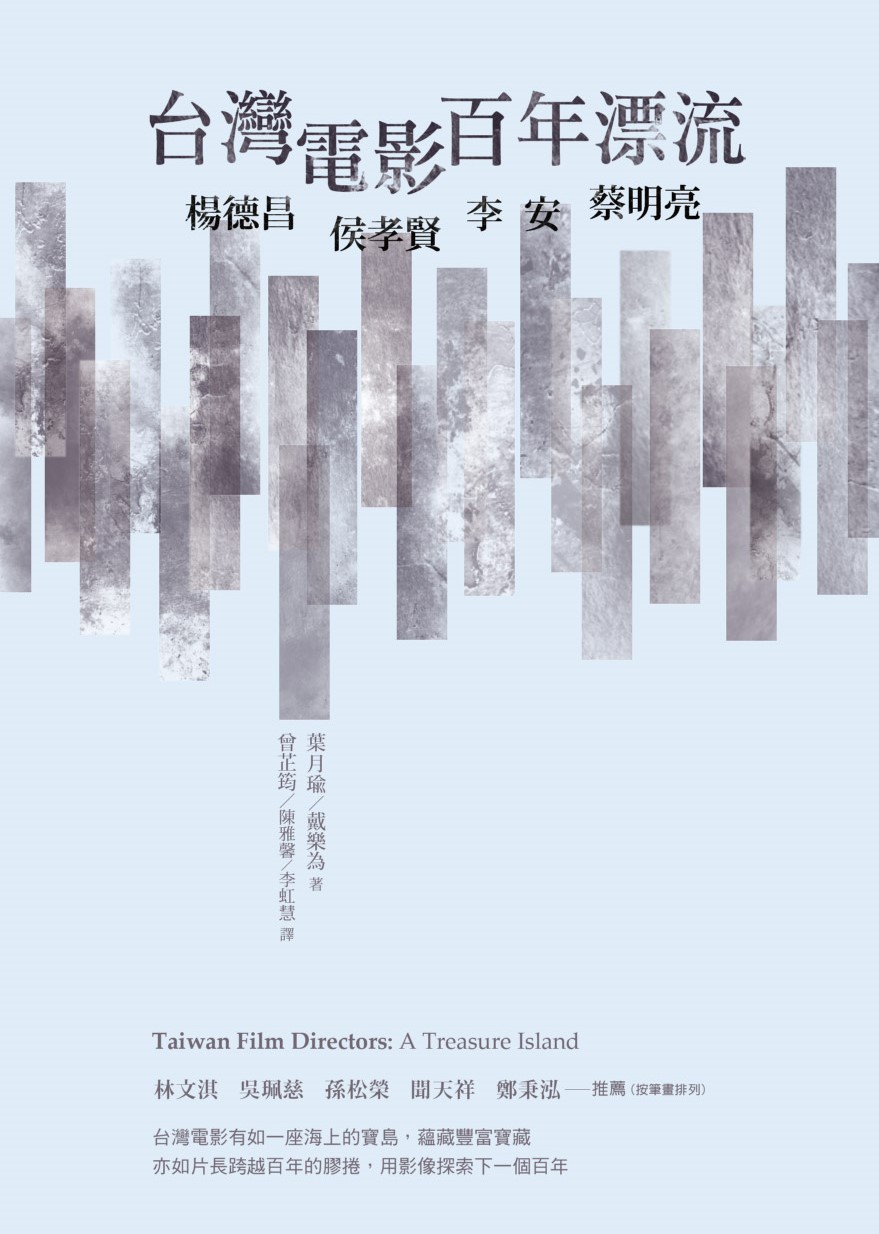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台灣電影百年漂流》一書,葉月瑜、戴樂為著,曾芷筠、陳雅馨、李虹慧譯,書林出版。
圖片來源: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