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會對日本的年輕人說這些話,其實就我本身也有一個理由,那就是我一直在思索著:是不是一提到台灣,日本社會就會陷入顯著的「思考停止」狀態?
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認知,其背景和我個人的體驗有著密切關連。
一九九八年,當時正在九州朝日新聞久留米分局擔任記者的我,在社內的留學選拔中脫穎而出,得以進行為期一年的中國話進修。那時候,朝日新聞的中國話進修,一年只有一個名額。當時,我在分局正好遇到一位個性不合的上司,不管是工作還是精神上都十分低盪,所以當我得知獲選的時候,那種欣喜莫名的心情,至今依然記憶猶新。
按照公司的制度,留學之前首先必須轉任到東京。到達東京後,要在當時稱為外報部(現在的國際報導部)的部門待上幾個月,然後一邊在俗稱「外電」的海外新聞處理課(又稱內勤課)工作,一邊進行留學的準備,等到秋天入學的時候,再動身前往中國和歐美等世界各地。原則上,要選擇哪一所大學留學,都是交由留學生自行判斷。我因為大學時代在中國、台灣、香港都有或長或短的留學經驗,所以做了多方面的檢討,最後決定前往當時剛進行總統直接民選的台灣。
因為我對中國話有相當的自信,所以我計畫跳過語言學習,直接前往研究所就讀,然後在一年之內把學分修完,第二年回到日本寫論文、取得碩士學位。我寫了一封信給某位在台灣研究方面相當著名的大學教授,拜託他幫我介紹適合留學的地方。現在想來,這樣的舉動也未免太莽撞了,一想到就忍不住冒冷汗。不過,這位教授卻相當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並將我介紹給台灣大學的教授、後來在陳水扁政權底下擔任陸委會主委的陳明通。於是我來到台灣,接受面試獲得了合格。
我將希望前往台灣留學的事情傳達給外報部的上司,當我要去面試的時候,上司也鼓勵我說「要加油喔」。可是,等到我報告自己收到台灣大學合格通知的時候,外報部長卻突然露出不高興的表情,開口說道:「你真的要去台灣嗎?重新考慮一下會比較好喔!」驚訝之餘的我,不禁據理力爭說:「一開始說沒有問題,結果現在才說不行,這樣會讓人很困擾的!」可是上司卻說:「狀況改變了。整體來說,朝日新聞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去台灣留學的。」「因為沒有人去所以就不能去,這也未免太奇怪了吧!如果台灣不能去,那乾脆事先把這條規定列出來不就好了嗎?」儘管我竭力反駁,但對方還是沒有說出明確的理由。
之後,這件事就懸在那裡過了好一陣子,然而決定留學地點的最終時間,終究毫不留情地逼迫而來。「社內的高層XX先生會火大喔」、「如果將來還想去中國的話,那就不該去台灣」,社內的前輩也給了我一堆諸如此類的「忠告」。在這當中,有一位我素不相識、曾經擔任過中國特派員的資深前輩,將我叫到社內的咖啡廳,如此質問我:
「你知道日中記者交換協定嗎?」
「知道是知道,不過這和留學應該沒有關係才對吧。」
「如果中國認為朝日新聞意圖分裂國家、違反日中友好精神的話,你能負得起這個責任嗎?」
事實上,在我感覺起來,一九六四年簽署的記者交換協定,到現在已經幾乎沒有實效性了。(譯註:舉例來說,中國曾經一度據此要求日本各報社關閉台灣分局,不過現在各社依然在台灣與北京都有分局。)只是,遵從日中「政治三原則」、不參與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這樣的潛規則至今依然束縛著日本媒體。然而,要說我去台灣留學是種「分裂國家的活動」,這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當然,我也絕不是為了搞分裂活動,所以才去台灣的;我所期望的是提高中國語文能力、加深學識,為將來的中國與台灣報導做出貢獻。
我愈發頑強抵抗,但鐵了心的上司向我下達最後通牒:「你要放棄留學,還是放棄台灣?這是業務命令,你要選哪一個?」雖然我很苦惱,但還是不想放過留學的機會。於是,基於現實優先考量,我只得放棄留學台灣,轉而前往福建省的廈門大學留學。之所以選在台灣對岸的廈門留學,多少也有一點意氣用事吧。
當時的我,當然充滿了挫折感。只是,我也隱約理解到,之所以變成這個樣子,原因乃是在於朝日新聞「貼近中國」的立場。不過,隨著時間流逝,當我在自己心中客觀回顧這段體驗的時候,我不禁在想:除了這點以外,是否還可以就更深一層的層面,來探討這個問題呢?
姑且不論一九七○年代,在中台交流已經有相當程度起步的一九九○年代,朝日新聞的一名年輕記者要前往台灣留學這種事,理應不會引起中國憤怒才是。然而,朝日新聞(裡面我的上司們)卻判斷說,只要和台灣有關,就會影響和中國 之間的順暢往來,於是不准我前去留學。說穿了,這完全沒有任何具體根據,只是按照「和台灣有關應該就不行」這種常識去做出的推斷。
日本所謂的「進步派」勢力(媒體、知識分子、政黨等),用有點難聽的話來說,他們對戰後中國的立場就是:「日中關係=以日中友好為基礎;歷史問題=承認日本的過錯;台灣問題=盡可能顧慮中國的主張」。
以友好方式經營日中關係,是一種外交政策,關於歷史問題,也是屬於個人信念的問題。可是,在台灣方面「顧慮中國的主張」這點,並非出於任何自己的主見;事實上,在我想來,這種做法根本無異於「對日本人而言,關於台灣,最好什麼都不要想」、「因為萬一被中國抱怨很麻煩,所以乾脆不要碰台灣比較好」這樣的態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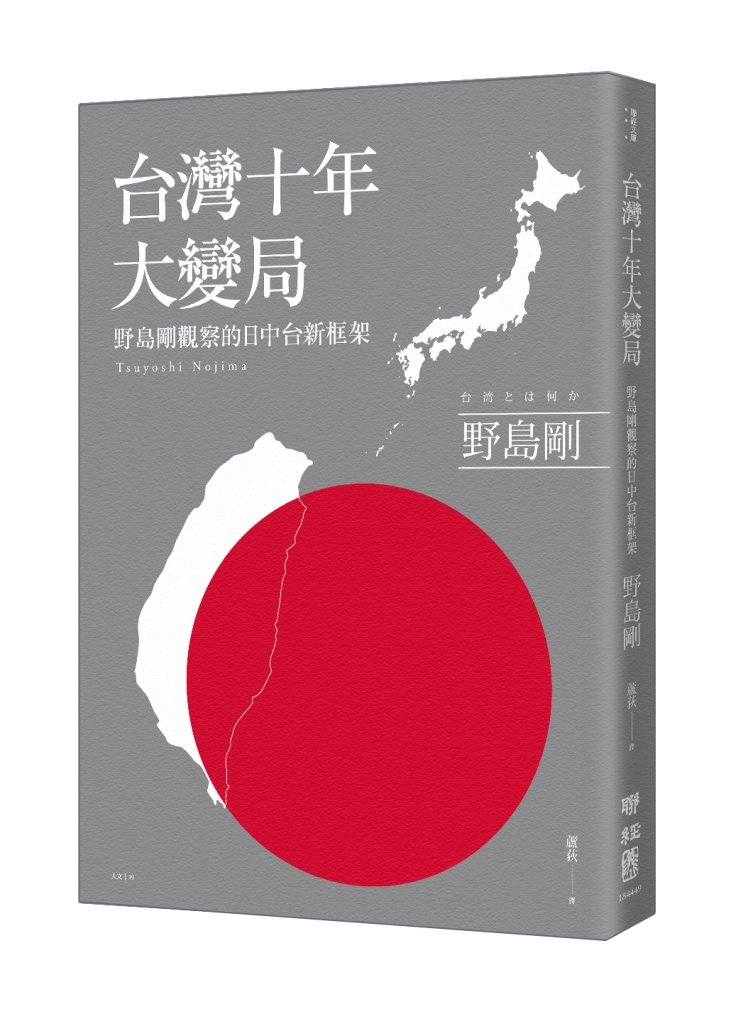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台灣十年大變局:野島剛觀察的日中台新框架》一書,野島剛著,蘆荻譯,聯經出版。
圖片來源:pakuta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