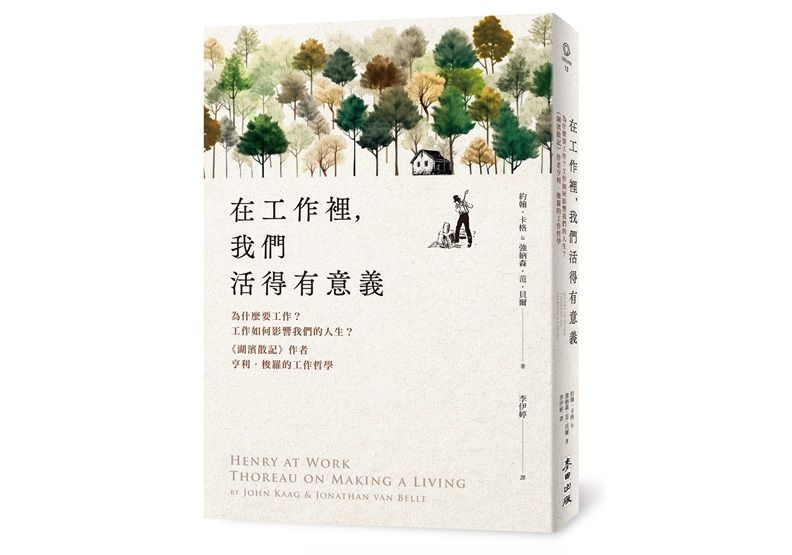後世素知梭羅以環保、廢奴主張、文學成就聞名,很少人知道他除了大量的寫作、散步、沉思之外,還是一位腳踏實地的勞動者。他一大重要思想來源就是一生經歷過的各色各樣工作:保姆、家庭教師、體制外學校辦學者……原來梭羅所有的思考核心,都是「在工作裡,我們如何活得有意義?」(本文節錄自《在工作裡,我們活得有意義》一書,作者:約翰‧卡格、強納森‧范‧貝爾,麥田出版,以下為摘文。)
梭羅通曉希臘語、熱愛雙關語和語源學,並且是一名嚴謹的作家,他選擇「經濟」一詞作為《湖濱散記》最長篇章的標題,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藉由住在一間簡樸的湖畔小屋裡(他的oikos),並將這個家打理得井然有序,可以說,梭羅也意圖幫助其他人,讓各自的家都井然有序——就這麼一間房子接著一間房子、一個家庭接著一個家庭,眾人將齊力為社會賦予新的生命。
第一章這個單調的標題,隱含一個別具深意的雙關語,它低語著:「這是一本關於一間房子的書;一間位在湖畔的簡單房子,但也是一間不那麼簡單的房子;一座混沌之屋,繞著太陽運行。」
經濟的目標,不是銀行帳戶和股票投資組合,而是支持一個家的培育和維持;這個家就最親密和最具啟發性的意義而言,有能力養護那些尚在成長中的人類。
現在,我們馬上就能想到反對的意見:「我的銀行帳戶確實支持了我的家,和我成長的能力。」但這種反對意見,忽略了梭羅的重點所在:一份工作,或許可以充盈你的銀行帳戶,讓你能夠支付房貸,每三個月去度一次三天假期,但它也可能浪費掉你生命的大部分時間,甚至扭曲你的生命——將生命花在從容打造一個美好的家庭,似乎會更值得。
無論是就字面或象徵意義、是從廣義或狹義層面來理解所謂的「家庭」,皆隨你高興,但不管怎麼說,這就是事實。梭羅相信,某種類型的工作,將使我們居住在這個世界上,而擁有(真確地擁有)「安適如歸」的感覺。而這正是梭羅所追求的經濟目標。
(延伸閱讀│人的「社會層級」共有7種:你在哪一層?跟擁有多少財富無關)
✻✻✻
在瓦爾登湖畔,梭羅如此記錄他的工作日:「大多數時候,我並不在意時間如何流逝。時光向前推移,彷彿只是為了照亮我的某些工作:這才清晨;哦,看啊,轉眼又是日暮時分了,卻沒有完成什麼值得紀念的事……我的日子,並非以帶有異教神祇印記的每週7天來循環;每天也不是被切分成特定的24小時,使我,在時鐘不停的滴答聲裡備受研磨。」
今日,時鐘的滴答聲使我們大多數人感到煩躁。滴答滴答:該起床了,該洗澡了,該走了,該打卡了(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該工作了,該休息一下了,該繼續工作了,該吃午餐了。滴答滴答。該假裝在工作了,因為你已經精疲力竭。該倒數計時了,滴答滴答。時間就是金錢。時鐘像一條鱷魚尾隨在你身後,吞噬你成年後的生活。
如果你看一眼梭羅寫字檯的翻板背面,你會發現數以千計的鉛筆痕跡,那是他隨性削鉛筆時所留下的痕跡。這是梭羅唯一認可的「打卡」方式,也僅只記錄了他著手工作的意圖。
梭羅在他的小書桌前所做的一切,完全取決於他自己,而那些邊框的刻痕似乎在說:「預備,就位,起跑。」他出發了,但從來不會是在別人的時鐘下奔跑。
我們的日子屈指可數,但我們的每時每分,也必須如此機械地計數嗎?我們常談到「上班時間」和「下班時間」,界線卻往往模糊不清。雇主和員工爭論通勤時間是否應該算作「上班時間」。
用梭羅的話來說,人生的任務是「充分善用時間」,於是,擁有一份工作時間表並不可恥。但「打卡」這件事,梭羅絕對無法忍受。
「上班打卡」,或者說,讓一個人對老闆、監督者或「上級」而言變得如此透明,這與廣泛形塑梭羅人生的超驗主義理想完全背道而馳。這種手段,將人的生命時間簡化為某種可替代的、無差別的東西——最終,你等於是用自己無法被償還的時間,來交換幾個銅板。
個體的生命價值是什麼?工業革命時期的工廠裡,時鐘是用來將薪水精確計算到幾角幾分的。最終,這就是問題所在。「對一個人來說,」梭羅喝斥道:「對一個人來說,沒有什麼比從容做成的決定更管用的了。」
(延伸閱讀│莊子的思想「相對論」:不做「人生勝利組」,也能做「人生幸福組」)
✻✻✻
當我們閱讀梭羅的作品時,請一定要記得,他對人類發展的觀點(例如,人應該有安排自己工作時間的自由),往往取決於他明顯意識到的階級現實。
他能夠決定自己的「工作時間表」,乃是因為他願意放棄某些現代奢侈品(梭羅是一位「節儉富翁」,在極少資源下過著富足的生活);同時也因為,作為一名穩固中產階級的哈佛畢業生,他擁有一定的生活地位。
是的,梭羅家族在有些時候可能較為貧困,但他們從未真的那麼貧窮過。於是乎,沒錯,關於「打卡」的事,梭羅能夠教我們什麼,確實令人有些懷疑。畢竟,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設法避免了這麼工作。
然而,對一個令人擔憂的事實,梭羅並沒有視而不見——在我們的社會中,經濟上最弱勢的群體,承擔了過多的匆促工作、被微觀管理的工作,和無意義的工作。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但絕對不是說,這樣的趨勢理應繼續下去。
如果梭羅今日還活著,他一定會和我們一同面對生活的基本事實。於是,關於「打卡」的事實是這樣的:大多數美國勞動者(大約75%),在早上6點至10點之間開始他們一天的工作。這對他們來說是好事:也許,他們能夠在合理的時間上床睡覺,不會喝太多酒,早餐還能吃碗麥片。而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的人,比起那些非貧窮人口,更有可能在非標準的時間開始工作。
「更有可能」究竟是多可能呢?他們在下午3點至晚上11點間,開始工作的比例,至少是後者的兩倍。這個時段,許多幸運且健康的人,正坐下來享用一頓有豆腐和蘆筍的營養晚餐的時候。而在美國,上夜班的黑人和拉丁美洲裔族群,比例則特別高。
無論這些人是否天生屬於雲雀型、貓頭鷹型、山鷸型或其他類型都不重要——他們必須在晚上7點至午夜之間上班,通常會一直工作到天明。這對他們來說,可不算是好事了:也許,他們只能在照顧孩子的空檔,擠出幾個小時的睡眠;在其他人都在工作時,看些電視節目來自娛;晚餐,則吃一些除了麥片之外的東西(這可能就是他們的早餐)。時間滴答、滴答作響。
在《湖濱散記》裡,梭羅有句名言:「大多數人在沉默的絕望中生活。」這或許是真的,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選擇的餘地。許多勞動者根本無從選擇。
在梭羅的時代,他們被稱為奴隸;在我們的時代,我們看見那些奧妙,但又並不真的那麼奧妙的經濟枷鎖,拘限住了貧窮的人——其中許多人,或者是新移民,或者根源直溯美國的動產奴隸制。當我們跟隨梭羅在工作時,這些都是需要處理的「基本事實」。
梭羅曾經、現在也仍然具有顛覆性,而我們不會美化他。他鼓勵我們所有人抵制壓迫的、以及傳統意義上的「打卡」;同時,他也鼓勵我們推翻一個制度,這個制度迫使數十億人參與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比賽——這是一場人們注定無法獲勝的比賽。
(延伸閱讀│「中產階級」的定義是什麼?人類學家:追求累積財富是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