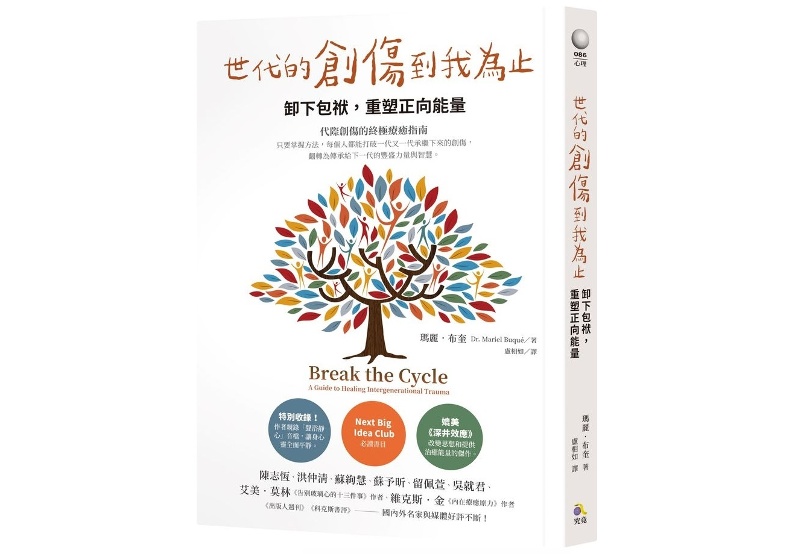當身體一處傷口未癒合時,會持續引發疼痛,且有可能感染其他器官;當情緒得不到治癒時,同樣也會對我們造成傷痛,並蔓延到我們身邊的家人及朋友, 最終,還可能會在數年和數代之間轉移。這就是「代際創傷」。這些傷口的成因很複雜,且深深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身體和精神。(本文節錄自《世代的創傷到我為止》一書,作者:瑪麗.布奎,究竟出版,以下為摘文。)
我的外婆、母親和我都在貧困中成長。外婆幾乎大半輩子都生活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巴拉奧納小鎮。
我記得10歲那年,因為家中和村子裡都沒有自來水,我和外婆一起走了1.6公里多的路。外婆身高約135公分,身材嬌小,在回家的路上,她一邊拉著我的手,一邊穩穩地把約3.7公升重的水桶頂在頭上,為家人保存辛苦汲取的每一滴水。
這幅畫面永遠無法從我的腦海中抹去。儘管物資如此匱乏,她仍珍惜所有,我因此感到既震驚又慚愧。
她不僅汲取每一滴水、每一份食物,還得添購負擔得起的盥洗用品,只因這些都是生存的必需品。
儘管她這一生都活在生存模式中,但她仍保有頑強的生命力。因為外婆的緣故,我除了保留任何民生所需品之外,也保留生活中的每一件小物品。任何東西都不能浪費。因為她使我明白一個人可以擁有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快樂。
母親在40歲時帶著兩名年幼的女兒移居美國,她一生也都堅持著這種節儉的精神,十分善於保存物品,一放就是幾十年—即使這些東西早已不堪使用。
我們住在紐澤西州紐華克市一處低收入社區裡。在母親眼中,不應該任意丟棄任何一件物品,因為在巴拉奧納的童年曾讓她歷過「一無所有」,所以,即使我們的衣服穿不下或電器壞了,又或者其他家用物品不堪使用,都不會被母親扔棄,相反的,它們會被整齊地裝箱保存。
多年以後,當我們有足夠的錢買新的東西時,舊有的物品就會被寄往多明尼加。因此,幾十年來存放的東西在家裡堆積如山。
但漸漸地,我了解到在這些箱子裡真正保存下來的並不是舊衣物或壞掉的烤麵包機,而是母親對一無所有的恐懼。
這種匱乏的心態,自她童年起便根深柢固存在她的心裡,這種思維模式植入了她對於生存的恐懼,以及無法幫助家人的愧疚。
我和母親如今生活無虞,但我經常發現自己也和她一樣,留戀那些我不需要的物品。如果我把東西扔掉而不是把它們捐出去或寄回多明尼加,我就會充滿罪惡感;如果我沒有把東西用到最後一滴,就會發現自己在內心低聲說著「我很浪費」,因為說不定哪天我會需要它、萬一屆時我一無所有。儘管家裡一直都有自來水,但我仍然生活在外婆的恐懼當中,擔心哪天沒有水可用。
我和家人擁有同樣的恐慌,她們的恐懼不經意地轉移到我身上。當我小心翼翼地保存物品時,我感受到了對它們深深的忠誠。這樣做讓我覺得是在紀念它們,但過了很久以後,才意識到這份忠誠是要付出心理代價的。
幸運的是,因為打破逐漸了解到的代際創傷所帶來的惡性循環,我幾乎擺脫了內疚和恐懼。我希望其他受此折磨的人也能擺脫對痛苦的「忠誠」,達到情感和情緒的平衡。
若要做到這一點,那些受此苦難的人必須透過了解他們與家族的痛苦傳承間的代際創傷,才能獲得治癒。這並不容易,卻是可能的。這種治癒所帶來的富足是美好的,且值得我們付出努力。
(延伸閱讀│為何不幸的人,要用一生治癒童年?創傷研究專家:大腦記憶連氣味、聲音都能儲存!)

代際創傷究竟是什麼?
但我們應該如何認定這種痛苦就是代際創傷?代際創傷究竟是什麼?
一切源於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歐文醫學中心的成人精神科門診工作的那幾年。我在那裡接受了博士生培訓。當時我正負責治療一位個案,治療過程十分艱難。
在這世上,很少有事情比在治療中陷入死胡同更令人沮喪的了,而那這正是我和個案到達的地方。在那一刻,我們只能枯坐在那裡,房間裡瀰漫著一種令人窒息的無助感。
我覺得自己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給個案,因為我所接受的培訓雖然很足夠,但並沒有讓我為此刻發生的事情做好準備。
不久,我思索出身處迷霧之中的原因。我的個案背負著代代相傳的罪惡感、悲傷、悲痛、憂鬱、焦慮等。因此,我們不只要解決個案的痛苦,還要處理個案的家人和祖先的情感負擔,他們有的甚至已經不在人世。
這是一項重大的治療挑戰。傳統西方心理學培訓並未教導心理諮商醫師做足準備,以治療病人的代際創傷。當個案帶著整個家族成員的情感創傷來診間時,我們沒有任何指導手冊。
在治療個案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了幾代人的重擔在其身上。在這趟治療之旅中,唯一的辦法就是穿越重重迷霧,處理過去幾代人的痛苦。儘管困難,但我知道必須進入深度探索才有辦法做到。
一個人為何要背負人生從未經歷過的創傷?
療程帶來的感悟永遠改變了我。從那時起,我每天都在思考代際治療的問題。我經常思考:一個人為何要背負人生從未經歷過的創傷?我想知道創傷如何從一個人傳遞到另一個人身上。
我對於代際創傷代代相傳的方式越發好奇。它是否如同這位個案的故事一樣,還是有其他會在我們生活中出現的變異方式?為了找尋答案,我的思緒總在這上頭打轉。
儘管幫助個案度過難關令我備感壓力,同時也感受到了做為一名臨床醫師的重重壓力,我仍堅持尋找出解決方案,以幫助無數受此折磨的人。
那次治療成為我如何看待臨床工作的轉捩點: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使我更能理解,當一個人帶著整個家庭的情感傷痛和治癒這種創傷的迫切心情前來就診,我要如何提供幫助。
做為一名科學家,我決定調查需要採取哪些措施來治癒像你我這樣的人,擺脫家庭和社區經歷的幾世代創傷,用健康、適應性強的因應策略來取代這些創傷反應。
(延伸閱讀│原生家庭的傷:父母在等孩子一句道謝,孩子卻在等父母一句道歉)
代際創傷在情感創傷中是唯一會橫跨世代的類型
許多家庭成員都可能經歷過這種創傷。但是,它是如何通過幾代人傳遞到你身上的?我們現在知道有兩種傳遞方式。
第一種是透過生物學,具體地說,是透過遺傳自父母雙方的基因。這意味著,如果父母中任何一方經歷過創傷,將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基因密碼,並將這些基因遺傳給你,使你因此受到壓力和創傷的影響。
第二種傳遞方式則是透過心理經歷,比如沒有受到照顧者妥善照顧、有害的人際關係、極端逆境、壓迫和一生中經歷的痛苦。這是創傷透過行為與習慣,從照顧者傳遞給孩子或從社會傳遞給個人的方式。
現在,代際創傷可以被打破,基因遺傳不需要再傳遞下去,因此希望藉由這本書來治癒創傷。試想,當一個人帶著生理上的情感創傷,且在沒有安全基礎的保護之下,會發生什麼狀況?代際創傷會藉由創傷循環在你的生活中顯現出來。
雖然這種類型的創傷源自家族中某個人經歷的創傷事件,但它對你的心理、行為和情感卻產生了影響,甚至還可能影響到橫跨世代的家庭成員,以及整個社區。
代際創傷是一種心靈創傷,它造成的情感傷害具有很多層面,對一個人的心理(思維和情感)、身體(身體承受痛苦的方式)和精神(內在認知和與他人連結的中斷)產生影響。這使我意識到,治療也具有多維度,必須面面俱到地治癒一個人的心理、身體和精神,也包括治癒人的靈魂。
(延伸閱讀│「好好先生」、「好好小姐」的原生家庭,可能都有一個「這樣」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