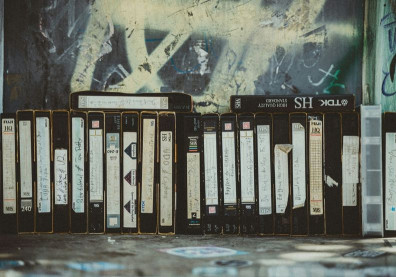阮義忠:不要用「賣點」決定一切
我感覺到這個時代蠻「消費走向」的,最普遍的現象就是我們的價值觀念和傳統的完全不一樣。我個人最憂慮的是,我們已經喪失了很多東西,在以往我們認為很嚴肅的東西現在都已經被輕鬆化了,例如以前覺得感情是很可貴的本質,現在似乎已不這樣看了。
在「消費走向」的時代,幾乎什麼東西都要看有沒有市場來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價值觀念已經失去了原則性,隨時在動搖、混淆。這個時候,我個人最擔憂的是:我們不曉得什麼是最值得追求或最重要的。
創造出來的慾望
不管以前多好的東西,到了現在,都變成以有沒有「賣點」、有沒有需要,及有沒有人接受來決定。所謂的需要、接受,也和以前不一樣,因為現在一切講求有沒有市場。現在連人的慾望都是被創造出來的,有一股力量在推動,讓你知道你需要什麼、有什麼是你所欠缺的。如此一來,我們可能被推銷了我們並不需要的東西,也被灌輸了錯誤的觀念。
這種現象並不只是在台灣,所有的商業社會都會發生這種問題,我想美國也是。現在經濟學者被認為是時代的代言人,在以前也許不是。我記得九月號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提到索爾貝婁的最新小說「更多人心碎」。在記者採訪他時,索爾貝婁曾經表示,像傅利曼似乎認為在商業時代裡,個人的自私是推動整個社會進步的原因之一。他說:「我的老天啊,我們需要這麼多文明的自私來決定我們的未來嗎?」
人的自私都會被當成促進成功的正常天性,其出發點和運作,都會形成很嚴重的問題。現在這種工商業社會裡,經濟操縱了我們的演出,塑造出一些「英雄人物」。
價值混淆的社會
事實上,這是全球性的問題,只要是資本主義走向的社會都會發生。日本大約在十年前就有「暴走族」,台灣現在有飆車問題,美國在五0年代也有類似的情形,而且更兇悍。他們是比較個人英雄主義,我們的飆車則是傾向於群體,這群年輕人似乎是在反對什麼,他們把所有的氣都出在跟他們有對立關係的人身上,例如警察。
這些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經過程。據我瞭解,資本主義一個基本的觀念是「找出需要給予滿足」。這很恐怖,如果真的有需要而被找出來那還好,如果這需要是空的、不落實的,是被創造的、誤導的,那我們不是在「不需要」中循環嗎?
在這種循環裡,一定會出現問題,因為人們會把「滿足需要」,和以前所謂的「人應該忠貞」等等視為同樣重要,倫理觀念也都搞混了。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有和動物下一樣的地方,動物是有需要給予滿足,牠就乖乖的,而人不同,人應該是自理想、有抱負、有關心的。
大家在這種價值混淆的社會,要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堅持原則的要求,已經很難了,因為我們很不容易去看清事實與假相。
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那裡,我們自已要分辨清楚,看這個東西是不是我所要的。這個分辨能力和以前分辨是非善惡的參考依據不大樣,我還不曉得是什麼。
現在有一個隱憂:究竟教育是在教育我們什麼?學校教育是在教你考上大學,當你考不上大學的時候,又會鼓勵你社會就是大學,叫是社會教我們什麼呢?可能教的是你如何在這社會中生存下去的辦法。我個人覺得很恐怖。
農村也在改變
十多年在全省各地攝影,讓我覺得以前鄉村的人沒有想到他們的生活情況不好,只是很認命的過活,那種人生觀有以承受很多苦難。
那種人整觀是好是壞我們姑且不論,但我很明顯的發現地們的轉變。現在他們慢慢知道比較;為什麼我那麼窮還要繳稅,那些有錢人好像沒有繳什麼稅?他們就會逐漸把自己的經濟情況歸諸於外力。以前他們種多少東西,拿到附近市場賣就好,現在不一樣,還要透過中間商、農產產銷制度,我知道嚴重時產地價格和我們消費者吃到嘴裡的價錢,差距是四十倍。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問題,也是由於市場運作方式的不一樣,農村社會的生活方式也跟著改變,他們開始不平、憤怒。而農村的這種「進步」,也使他們的價值觀念改變了,覺得自己那麼辛苦,卻賺不了多少錢。如果這個社會的制度健全的話,他們種菜得到應有的利潤,就會很甘心的種菜。現在是生產者、消費者吃虧,當中的商人佔便宜,所謂的「逼死你死」(business)。
現代人容易感到挫折
這就是都市把鄉村抽空了。都市人不會感激生產者,所以現代人特別容易有挫折感。
在現在這種工商業社會裡,最大的教育力量就是來自於傳播界。例如我看了雜誌上的一篇好文章,就可以感動我做很多的反省,這是很好的教育。因此,我們應該稍微平衡一下,沒有「賣點」的東西要稍微肯定一下,不要用「賣點」來決定一切。
(阮義忠為攝影家.楊孟瑜整理)
陳映真:我們喪失了中國焦點
我以為目前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四十年來,我們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中喪失了歷史,喪失了中國的焦點。
從一九五0年台灣編入世界反共圍堵戰略線之後,國土分裂,民族離散。這以後的三十七年中,台灣的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都在國家分裂的架構下完成。我們的學術、文學和政治,也都在國家分裂的框架下發展。久而久之,「我國」人口不知不覺間成了「一千八百萬人」而沒有人引為怪事。大陸中國成了異國,大陸同胞成了異族。
台灣的經濟長年來把大陸市場視同不存在;政治則不論朝野,莫不以國土分斷的永久化和固定化為宗旨;藝術文學的劇作,從來不考慮目前作品在百千年後中國統一之日,於中國文學藝術的傳承中的意義。科學研究、學術著作,也多以當前偏安之格局著手。越來越多都市年輕人和文化人,公開表白他們對中國大陸毫無情感。
國際冷戰心智、長期僵化了的反共宣傳,中共政治和權力的退行化,是造成台灣整個世代喪失民族自覺和民族主體性的原因。在國家分斷的歷史下喪失了歷史的台灣,在反共主義的延長線上,終於出現了反對和疾視中國、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和中國人的所謂「分離主義」。
至少在台灣海峽,國際冷戰架構,從七0年開始重編和鬆弛化。台灣近年的民主化改革、探親之開放、大陸書刊的逐步解禁,皆有助於海峽兩岸和平結構的展開。
我們期待海峽兩岸皆能痛定思痛,在民主主義基礎上大力推展民族統一運動,使分裂的國土和離散的民族再度統一,結束民族相敵和全民族的創意及英智因敵對而抵銷渙散的歷史。
(陳映真為人間雜誌發行人)
曾昭旭:中國人失去了教養
我覺得最可憂慮的是社會上普遍瀰漫著一種不良的心態,我稱之為「消費有心態」。
消費的心態,就是對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都心存利用而不珍重、愛惜、尊敬,「利用」還是個比較中性的字眼,說嚴重些,就是「剝削、耗損、消費」。消費就是「用完就扔掉」。
如果抱持著消費的心態,我們就不會顧慮外在的事物美不美,能不能長久存在;因為反正是要丟掉的。在這種心態之下,許多事物就從有尊嚴、有價值、有地位的身份,被轉換成廢物,轉換成垃圾。所以今天才會垃圾充斥,包括物質垃圾和文化垃圾。
人類的活動有一些的確是臨時的消費活動,但有一些則具有永恆的意義:如讀文學、藝術作品時應該咀嚼一下,得到一些啟發領悟,不該讀完就扔掉。但現在人們把藝術品也看成消費品,從事藝術活動只是為了找一時的刺激;因此只看表面可以哈哈一笑、供消遣的部份,不問內含的意義;連帶的把藝術家、作家也視為消費品,去看他只為滿足好奇、打發無聊,並無敬意。
最近甚至流行到連學者也要變成消費品,凡是「明星學者」、「熱門學者」,到處都要請他。很多雜誌社也因為有龐大的消費人口,而被逼參與剝削學者--儘管他沒有時間,精力過份透支,學問不再長進。我們的社會變成一個最會糟蹋學者、作家的社會。先把他炒熱,弄到後來真的油盡燈枯了就丟掉,再去挖掘新的偶像,龐大的社會需要,會把人的精力、才華迅速吸乾。
挺嚴重的是,連最親愛、最不該成為消費品的「情人」,都漸漸變成消費品了。要「消費情人」,所以不斷扔舊的、換新的,做感情遊戲。
心靈被糟蹋利用
人與人之間互相剝削、利用、併吞,就是所謂「人吃人」。當世界變成人吃人的世界,人們偶而表現出來的一點愛心、關懷、善意,都仍不免被人利用糟蹋,一旦心靈受到「糟踢利用」的傷害,就越不敢把真正的誠意拿出來,於是社會越來越冷漠。結果都市從表象來看雖是文明、遠離蠻荒的,但本質上還是人吃人,還是個蠻荒,還是個叢林。我們可稱之為「都市叢林」。
當社會比較貧窮,人們的消費能力僅能夠消費白米飯、開水,而沒自能力從事更多的消費時,消費心態還下致於造成「人吃人」的罪惡。但現在從外在來講,人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強,有錢去購買別人的肉體、靈魂;消費心態表現成行為時,就可能造成人吃人的罪惡。所以耶穌才會說,富人要上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從內在來講,這是因為人們缺乏教養、良心荒蕪、變質所致,是一個世界性文化失調的問題。
由於文化失調,社會的價值觀變成多元、多軌,互相衝突、重疊,形成從社會到人心的下安定,反映出人生命內部價值的迷失、愛的迷失、良知的昏昧,因為長久以來,人們缺乏真正的人格教養,使人的生活只維繫在外在的軀殼上。
中國人從滿清入關開始,就失去了教養。滿清用高壓懷柔的手段對知識份子進行鎮壓,結果使人文精神教養的活水源頭中斷,只能靠過去兩三千年留下來的禮教規模來維持社會秩序--這基本是一種「吃老本」的型態。
道德力量全部垮台
民國成立,五四運動之後,在西方文化強大的衝擊之下,則連這尸居餘氣的禮教也崩散了,使得維繫中國人教養的道德力量全部垮台,而導致今天世衰道微的現況。
其實現在社會還能夠維持一個大體的秩序,在底層所靠的,恐怕依然是一些殘留下來的老本。因為新的西方式法律的客觀作甲還沒有充份建立起來,仍舊依靠著傳統的人情及家族倫理。當然,由於所靠的是一些殘餘的力量,種種弊端也從此衍生。
就現象來講,這是過渡的,因為歷史本來就是辯證的,進三步退兩步、當它退兩步,往下掉時,這種功利的、消費的、剝削的心態就會浮現出來。當年孔孟老莊已看到這現象,所以才有「義利之辨」。「利」就是消費心態,一切人事物部是為了滿足「我」的自私動機而存在的犧牲品,「我」是唯一被關懷的對象。
而「義」就是「仁愛」、「博愛」,心情上是愛人如己,把所有與我相遇的人事物,都跟我一樣平等地列入一體的考慮。不只是人,連物跟我部是平等,不能為我而被犧牲、被糟踢。這就是愛物惜物之心,也就是「仁義」,是決定我們整個人生、社曾情調究竟是上揚或下墜的關鍵。
雖然這是過渡期,但一定要有越來越多的人反省這種自私重利的現象,尋求解答,才可能扭轉。更需要越來越多有良心自覺的人參與社會機構的運作,社會才能成為一個良心的機構,否則徒法不足以自行。
長遠地看,解決辦法是謀求教育改革。但在治標上,我覺得應該從整頓司法、政治的風氣著手;政治和法律畢竟是社會機構裡最強大而立即的力量,能最有效地解決明天的問題。
(曾昭旭為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洪淑惠整理)
阿盛:別以為經濟進步就夠了
我們的教育,不論是社會教育或學校教育,一直都有很明顯的「唯功利」傾向。政府總是強調經濟如何如何,過年時蔣經國總統也在電視上恭喜大家發財。似乎大家都只有一個方向,老百姓的思考一直被引導去賺錢,賺錢之外呢?
為什麼我會特別擔心這種情形?因為幾乎所有的價值觀念錯亂都是從這裡出發。
是不是應該有人告訴我們,在金錢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也值得去追求呢?
社會價值觀偏差
從現在的社會現象可以看出來,以作家、藝術家來講,有的人認為他們之所以社會地位不高,是因為賺不了多少錢。文人、藝術家一向窮酸,大家總認為如此,那麼,如果他們不窮酸,是不是社會地位就高一點?
許多很敬業、很努力在從事一些值得尊敬的事情的人,並沒有受到社會相對的尊敬,這就是整個社會慣值觀偏差了,為什麼致力文化事業的人不受尊重?為什麼演一場戲劇要被抽稅,要被當成生意人來看?
政有也經常以「治術」來利用文人、藝術家,把這些人拿出來當「樣板」,表示我們也很注重文化藝術啊!事實上你到文化中心去看一看,就會知道那算什麼文化中心。蓋音樂廳和國家劇院,事先也不徵求藝術工作者的意見,當官的怎麼決走就怎麼做。當官的未必懂文化,他沒有這方面的認知啊!蓋國家劇院,不請藝術家來商量,這是不是瞧不起他們?是不是認定了他們沒有社會地位,不能講話?
太過功利即是病態
假如這種現象一直發展下去,台灣可能會很「香港化」。「香港化」就是一種被殖民心態,反正也不求長遠,能賺錢就賺,能撈就撈,到時候該走就走,口袋裡有錢就行了,還搞什麼藝術文化!那些「東西」靠得住嗎!
難道時代進步就一定要這樣子?我覺得太過功利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病態,這才是真正值得所有住在台灣的人警覺改善的重點。
政府最好不要有意無意的過份強調經濟掛帥,這真的是不太好,應該把經濟成就當作一件平常事來看,不要那麼誇大,否則會造成誤導。
社會大眾最好別以為只要經濟進步就行了,大家吃得好、穿得好就行了,大家應該注意一下那些不應該因為時代進步就無條件被「淘汰」的東西,諸如倫常道德,這麼說,如果有人認為太迂,那麼,請恕我無禮,我要說,膚淺的人才會如此認為。
(阿盛為作家.楊孟瑜整理)
李亦園:我們的問題在目標不夠清楚
在我看來,人家樂、飆車、色情都是枝節的問題,在社會比較正常時,就會自然簡化。事實上,如果社會不把這些現象「特別化」,不故意先制止它,故心引起一些反應的話,可能不會那樣突出。
而我真正感到憂慮的是,因為整個政治不夠民主,或是還沒有真正跨進民主,所帶來的一些特權和特別的人際關係--強烈的父子軸為模型的關係,這才是問題的根源。
不解決這些根本問題,即使把大家樂、飆車、色情都去掉,還是會有其他不正常的社會現象出現,不過形式不同而已。所以,治本之道還是在於形成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結構;形成自由判斷、自由教育的合理環境。一旦如此,特權自然解決,目前的社會現象便會納入比較合理的管道。
在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目標很重要,怎樣才是最合理的民主?什麼是最適合我們民族生活的基本態度?傳統的價值中那些地方值得保留?
社會缺乏思辨能力
我們的問題在於目標不夠清楚,不知道應該民主到什麼地步,一直在徘徊、懷疑,或者打折扣。比方說,文建會所標榜的文化建設,就沒有勾畫出一幅清楚的藍圖,使得五、六年來,文化政策始終搖擺不定。
照理說,大家樂、飆車是文建會應當檢討的問題,因為文建會一直在精緻文化上努力,卻沒有找出合理的、青少年可以走的道路,沒有落實到社會的最底層。假如六年前訂下肯定的目標,相信今天這些現象至少會好一點。
找出這個目標是政府的任務,同時也是民眾的任務,政府如果在好的、合理的狀況下,可以引導民眾實現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
過去三、四十年來,一方面是政治環境,一力面是危機心理,我們的教育一直只教應該怎樣,沒有教為什麼應該這樣;使得整個社會缺乏思辨的能力。解嚴是一個轉機,大家心態比以前開放了,而開放的意義在於能夠改變一些基本觀念和社會結構。照目前這樣繼續發展下去,反對的力量越來越強,也許互相激盪一下,會越來越開放,但如果我們不做任何改變,反對力量越來越大,社會將變得更動亂,這點當然是我最不願看到的。
(李亦園為清大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陳郁文整理)
吳念真:有錢又俗氣的社會
每次看到學者專家在談怎樣解決大家樂、飆車,我就覺得很荒謬。今天即使你解決了大家樂和飆車,依然很難料到明天又會出現什麼更可怕的狀況。因為整個社會的本質沒有變,這個社會充斥有錢又俗氣的人,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謂俗氣,基本上是人的本質越來越糟糕,所有的人都以利益為著眼點。在追逐的過程中,錢和物質是永遠沒辦法滿足的,而且就不會想到其他,只會用這一點作為人的價值評斷標準,作為一個奮鬥的目標。
人家說暴發戶最可怕,他有錢可以做任何事情,而做的事情都沒有水準,台灣現在就是這樣。你不要跟他談法治,他要錢的時候,才不管法治;因為所有的人不會尊敬你守法,而會尊敬你錢賺得多。
危機來自教育
這個危機的最大來源是教育的方式。不只是學校教育,而且包括家庭教育。爸爸媽媽是怎麼長大的,大概根深柢固如此,再慢慢熏染小孩。他進入學校,學校也沒有給他一個空間去想其他事情、去存放另一個價值。整個教育環境,已經逼使人不得不朝「錢」看。
人在這個社會裡,沒有價值標準,除了爭錢外爭不到其他東西,他只好爭最快的,那就一定會發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沒有了精神導向,他一定會弄最快的來出名。
我覺得現在已經是病態了,這完全不是自然的現象。這社會是有病的,我們一直不承認整個制度是有病的,最後我們一定要付出代價。
有人講,我們三、五年後會改變,我很悲觀,我不相信,我認為就算從現在開始做,也需要二十年以上的時間,教育方式要全部更換。
影響教育最大的是什麼?是政冶嘛!是怎麼樣的政治團體,用什麼樣的心態在辦教育,就可以影響教育的品質。政治氣氛使得教師無法教導學生自由思考、自由涉獵,他們只有一個選擇;順著上頭的意思。因此,小孩子從小就會看人家的臉色做事,長大以後就會說謊。因為只有說謊的人可以生存。
不治病源治病徵
我們知道得肝癌會發燒、會痛、大家樂、飆車就像是這個病徵,而有錢又俗氣則是病源。問題是常吃什麼的人會得肝癌?常抽菸喝酒的,得肝癌的機會就大--我覺得這就是人的問題,即教育制度的問題,現在社會發燒了、痛了,但醫生還沒診斷出是肝癌。所有的人都避諱去談主要的病源,只談一些病徵。光講病徵是沒用的,今天痛完,明天還是痛。
有人說,在民主改革的過程中,這些社會現象都可能發生,調適過程恐怕要三、五年。我覺得錯了。以前沒有解嚴,硬壓抑的話,雖然不知道何時爆發,起碼可以維持一種表面的平和。現在把蓋子掀開了,很多問題都出來了,出來了就一定要改;而要在三、五年內改好,我覺得不可能。現在比以前更好的機會是,我們可以看到問題在那裡,以前也許看到了也不講。它可能提供社會強烈的危機意識,是一種警告,一種「風暴來了」的感覺。
我不敢給別人建議。就我的經驗,社會出現這些現象,我會站在比較觀察的角度來看,看它為什麼會這樣。我個人是以哀矜毋喜的心態來面對的。
(吳念真為電影劇作家.洪淑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