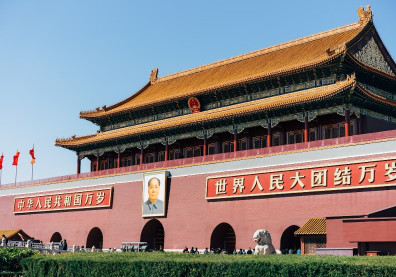一九九五年底,日本國會通過建立科技政策架構的「科學技術基本法」。今年七月,國會通過在末來五年基礎科學研究的發展上,投入一千五百五十億美金,這項經費與前五年比較,成長五0%,被視為是各界企圖培育日本科學界愛因斯坦的動作。
一向「改革」科技能力強大的日本,應用研究能力雖強,卻面臨基礎科學能力不足的事實。許多科學家表示,過去日本研發經費多著重於應用科學,對基礎科學多所偏廢。諸多科技產品的概念不是來自於自己的基礎科學研究,威脅著日本經濟發展的實力與競爭力。
日本經濟企畫廳官員宮崎勇表示:「再不改變我們的體系,日本不僅會被工業先進國打敗,也會被快速成長的開發中國家擊垮。」
泡沫經濟後的日本,科技與經濟的發展危機一再浮現。進入九0年代,許多新興的商業科技,像是電腦、軟體及半導體,日本拱手讓給再度崛起的美國。曾經出現過一百七十五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美國,基礎科學能力強(美國企業AT&T的貝爾實驗室,曾出過七位諾貝爾獎得主),搶回科技龍頭的地位。
美國英代爾領先日本NEC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商;微軟、網景及昇陽等美國軟體公司在今天的多媒體世界,藉由訂定技術標準及專利保護,廣獲華爾街讚譽。
前有美國,將日本拋在後,後有新興工業國,緊追不捨。台灣及韓國在電腦、電視及半導體方面透過更為精緻、有特色、效率及彈性的生產,事實上已能跟日本競爭,也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科技競爭實力。
科技是唯一道路
隨著台灣新興產業像是資訊、光電、精密機械及生物科技領域的興起,高科技產業儼然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一九九五年台灣科技產業值已達二一三億美元以上,高居世界第三位。
由於資訊工業的蓬勃發展,台灣已成為世界重要的個人電腦製造重鎮,因此每年對個人電腦及周邊的半導體零組件需求不斷增長。四年間台灣半導體產業成長五.四倍。去年半導體產業營業額總值已達一千四百八十億元,使台灣成為亞太地區最重要半導體市場、全球第四大半導體市場,僅次於美、日、德。維持、推進這樣的科技實力,國科會主委劉兆玄表示:「政府協助高科技廠商開發技術時,必須更往上游推進才行……。」
韓國對於高科技的研發,早已起步。在歷經數十年高度經濟成長後,面臨經濟蕭條的南韓政府與工業界,很快看到:高附加價值的科技發展,是南韓經濟繼續行進的唯一道路。
一九九二年,由科學與技術部負責督導成立了一個跨部會計畫--聯合有關部會共同從事研發。這計畫分兩類、十一項,一類是韓國特殊高科技產品的技術研發,像是半導體的記憶晶片、ISDN、高畫質彩視、智慧型電腦及汽車科技等;另一類則是可以提升經濟社會水準的基礎研究,像是超大型積體電路的發展,環境、生化科技及能源資源等。
幾年下來,研究經費也不斷投入,一九九四年民間與政府共投入一.八億美元的經費;一九九六年擬繼續投入美金七億元,南韓不僅展現對科技發展計畫的延續、一致與政策的協調性,也表現出對基礎工業架構及基礎研究體系的整合能力。
如今南韓的科技及經濟實力異軍突起,直追日本。韓國的三星電子公司在一九九四年就成為世界最大的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簡稱DRAM)晶片的生產國。韓國有自信在公元二千年追趕上七大工業國。
重視創造力
其實,急速發展的亞太國家爭相加入高科技研發的競逐,是回應世界的產業趨勢及環境資源。(見一七四頁表一)迎接二十一世紀,美、日、德、英等國曾針對末來的產業技術趨勢進行預測調查,這些重要的產業領域包括材料、能源、資訊、機械、生物科技、人類社會及環境,都是需要投下大量時間、大筆經費研發的工業。回應這樣的世界趨勢,抵擋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日本最大的一股科技逆流,這一波試圖讓日本科技實力脫胎換骨的科技改革計畫,會成功嗎?
在這項計畫中,經費將用於改善日本各大學的基礎科學研究,更新研究機構的設備;增加技術人員與博士後研究員,改善上游研究員例行工作的負擔;並將研究人員終身聘雇制政變為彈性雇用制,增加競爭,以發展研究。日本當局期望在下一世紀能跨入生物科技及航太工業的科技領域。
改革氣氛從政府、學術界到企業界,瀰漫整個日本,產生一些影響。日本企業界現在理想的形象是一個藍眼睛、四十多歲,被哈佛退學,看起來像小伙子的資訊時代太陽神--比爾.蓋茲(B. Gates)。在談到日本的未來時,日本人幾乎無法不提到這位神話式的人物,一些新的企業學校也打算積極培育「日本比爾蓋茲」。於是,日本又開始談起高科技產業需要創造力這個話題。
日前一項調查顯示,日本四一%的主要的企業,雖然還是強調工作的熱誠、合作以及對企業的忠誠,但是,相較於前,更重視創造力。
需要更創意的思考
但是,改革在進行,卻不光只是充足的野心、掛在嘴邊的創意人才培養以及進口、改良美國科技這麼簡單的事,日本必須建立起真正自由的研發空間,讓科技產業所需的創意思維出現。
日本一些科學及企業家顯然對此不抱樂觀。工業研究員東野進說,看看日本的小孩和玩具,就不難理解日本有創造力危機。有一些日本人則認為傳統日本的經濟文化,也許可以創造出一大群忠誠和效率的「工蜂」,卻無法出現創意的天才。
另外,愈來愈多人對這個充滿規範及服從的文化網絡感到窒息。櫻花銀行總裁末松建一和他的同僚對日本的前途都有危機感,他表示:「除非日本學習如何更創意的思考……,否則日本的末來可能會非常蕭條。」
創意的思考來自突發奇想,日本的教育體制則從不鼓勵具有奇異想法的人。大學被退學,靠著寫遊戲軟體,創立日本方形軟體公司(Square Software Company)的阪口伸,在女兒小學時就讓她前往加州讀書,他表示,他很反對日本學校普遍存在的機械式背誦,對日本的教育,他的看法是:「這是個強調服從的系統。」
從學校、企業到社會則不鼓勵「嘗試和錯誤」。日本通產省工業財政局局長田中武雄說:「一旦你在這裡失敗了,你不但被視為輸家,還會被放逐。」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中心國際事務日本計畫的分析家凱斯則表示:「在美國,每個蓋茲典型的成功故事背後,會有五千個失敗的案例。日本要擁有一個蓋茲,必須嘗試數千個失敗,他們允許這種狀況嗎?」
很多日本優秀的科學家及技術人員則寧願留在美國或歐洲國家從事研究,不是因為日本經費缺乏,而是這些國家較允許冒險。一九七二年就在麻省理工學院作博士後研究的田中豐一,發現了可以解釋分子鏈的行為。他表示,在日本,他不相信他的研究會有這麼大的突破。
國內創意文化不足,若再加上體制封閉,無法對外引人創意的活水,日本欲邁向科技基礎大國的政策實行,可能成效不彰。
多一點彈性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日本大學及研究機構仍維持「鎖國」的狀態。由於語言的限制及文化上不易接受外國人,外國研究人員要進入日本的學術體制難於登天。日本一百所大學中,只有二十五名外籍人士。
東京帝大百分之八十的教授畢業於目前所任教的系所,缺乏外來刺激,對於吸收新而完整的科學知識及國際上的學術交流都是障礙。
不管有多少零件有待汰舊換新,日本各界其實已經注意到國內基礎科學發展的不利條件。
一些年輕企業開始鼓勵企業成員冒險。三十九歲日本軟體銀行創立者孫正義認為,年輕一代的企業家較不受限於過去日本式經營作風與思維,「他們比較開放、多一點彈性並且比較西化。」美國商業週刊表示,在政府強力的改革政策下,也許這一群企業家是一股不容忽視的改革推動力量。
新加坡大學東亞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副所長吳根水(譯名)在說明新加坡的科技發展與經濟狀況時,道出日本、韓國、台灣等國家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為了經濟的永續發展,所共同面臨的科技發展瓶頸與選擇,他表示:「新加坡必須選擇合適的發展以符合需要,因此新加坡的工程師及科學家必須快速爬上科技的階梯。」在面對亞洲各國競相投入經費研發,發展高科技的狀況下,台灣的科技體系如何因應?
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表示:「台灣的科技發展仍末上軌道。」他認為台灣想要建立的科技島,其概念應該是以科學技術帶動生產力,但台灣的產業技術仍是從國外引進。另外,台灣科研經費比率相當低(一九九四年全國研發總經費一一四七億元,和日本日立公司的研發總經費相當),顯示出科技持續發展的隱憂。受限於台灣中小型的企業體,個別企業研發能力不足,而有能力的大型企業則是研發觀念不足。
曾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貝爾實驗室半導體主任羅義安表示,台灣對基礎科學研究似乎不太重視,他認為基礎科學要有長足發展,政府必須先訂出國家科學發展水準,使經費配置有一致性,不會因經常變動而影響研究,基礎研究是長期的工作,穩定的經費來源很重要。
仍待突破
其實,除了經費、研究人口(見下頁表二)、科技發展所需的法律架構及政策的協調、整合能力,台灣相較於韓、日,條件都差很多。當台灣還苦於找不到可以建立促進科技發展的法律體制時,南韓早在一九六七年,為了確立整體推動跨部會協調科技發展政策就制定了科學技術振興法,而後為了有利於民間企業的研發、國家R&D計畫的推行等,都依序建立可以依循的法源基礎。至於日本國會今年六月甫通過增加大量研發經費的「科學技術五年計畫」,正是依據延宕二十幾年、去年通過的科技「基本法」。
衡觀台灣產業的發展史,人力的品質恐怕是目前唯一還能引以為傲的。八0年代,留學生配上台灣自己所訓練的人才,讓高科技工業生產能急速進展。
據統計,台灣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八年,超過十一萬二千六百位學生出國讀書,大部分是到美國,將近一半的學生研讀科學、醫學及農業。一九八三年,當政府嘗試將這些具有專業訓練的外國資源引回台灣時,吸收回來的不僅是科學與工程的知識,還有美國企業管理與生產的經驗。一些專門的領域像是電子、電訊及資訊科技產業,就在這種條件下被建立起來。
李遠哲以他在國外學術研究機構多年的經驗表示:「台灣一般科研人員的能力都不錯,但是沒有能夠充分發揮。」的確,不足的科學資源及環境,讓科學家無法心無旁驚地完成研究工作;學術機構飽和,每年六千名歸國的留學生以及台灣自己培育出來的博士生,沒有得到合適的研究訓練及職位安排,整體社會更缺乏培養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的氛圍。
這些缺乏誘因的狀況,讓台灣學生逐漸遠離基礎科學研究,也讓既有的科學家、研究人員在面對長期的研究歷程中,承受更大的壓力。
今年九月舉行的第五屆全國科技會議對於科研經費的彈性應用與數額(八七年度科技經費將增加四十到六十億,國科會希望二千年科研經費投資可達國內生產毛額的二.五%)、研究人口的養成、科技發展所需的法律架構及國家高科技體系的建立,都有明確的討論與政策宣示。落實這些政策,為科學人布置一個適合研究的環境,讓人才適所,在台灣經濟正待突破的關鍵時刻,不啻是重要的課題。
「高科技產業無疑將是亞洲未來發展的重心。」奈思比在「亞洲大趨勢」一書中如此表示:維持亞洲各國經濟發展的顛峰與永續發展,正繫於這一場高科技研發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