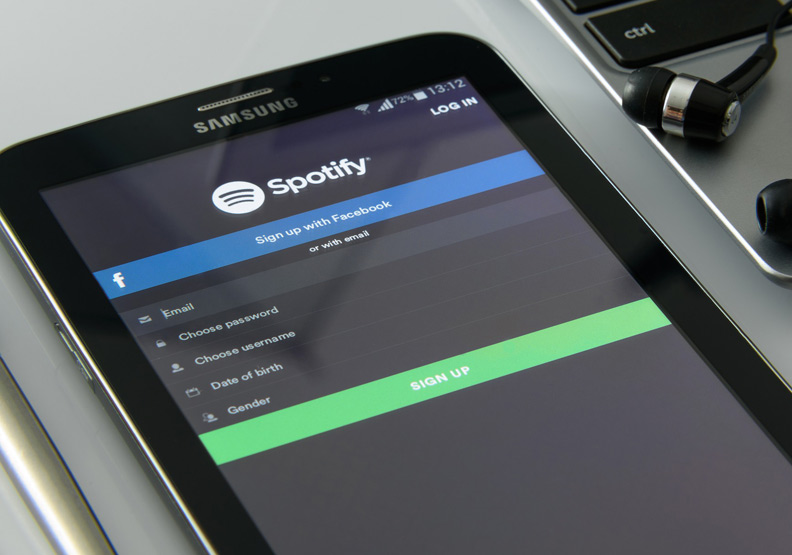Spotify 從「管道」躍上「平臺」
這也是Spotify 篤信的真言。這是一家來自瑞典的數位新創公司,目前經營全球最大的音樂串流服務,大受歡迎,有超過一億的音樂愛好者,使用Spotify 聆聽喜愛的歌曲和專輯。
Spotify 的商業模式,破壞的是蘋果的數位音樂商店iTunes;而iTunes 過去也曾經破壞了音樂產業長期以來,在實體店面銷售唱片及CD 的商業模式。音樂產業對iTunes 可說是又愛又恨:一方面,蘋果數位商店吃掉了音樂產業的一大塊利潤,但另一方面,iTunes 願意與內容製作者分享收入,而不像是稍早前的其他服務,從事的多半是非法的點對點檔案分享。
比起線上音樂商店,音樂串流是一種更根本的破壞式創新,因為它所創造的平臺會讓價格與產品脫勾、讓成本與消費分離。
大多數用戶都能免費享受服務;付出的代價不是金錢,而是個人大數據資本主義資料(也就是說,他們願意接受專門針對他們的廣告)。
截至2017 年,Spotify 共有五千萬個「Premium」用戶,每月只要付出少少的十美元月費,就能無限存取超過三千萬首歌曲,不論是想要聽個不停、或是任意跳過許多歌曲,都毫無限制。而且,省著聽也不會有什麼好處。Spotify 這個音樂市場的機制,與傳統市場不同,價格幾乎完全喪失了傳統上提供資訊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各種不同的訊號,例如用戶都在搜尋什麼音樂、誰又跳過了哪些歌曲、哪些歌曲的分享數比較高。
音樂產業原本屬於「管道」型商業(相當倚賴零售通路),早已大受破壞式創新影響了,而Spotify 將「管道」轉型為「媒合平臺」(媒合的對象是聽眾與音樂,以及廣告主和群眾),付費聽音樂只是這整件事當中,比較次要的資訊角色。對我們來說,Spotify 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其組織結構。
「小隊化」的管理體系
Spotify 成立於2006 年,兩年後推出入口網站。公司創辦人為瑞典創業家艾克(Daniel Ek)和羅連松(Martin Lorentzon),但對於音樂串流業務有興趣的,絕不只有他們兩位;於是幾家串流新創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也就此展開。
但與其他競爭對手不同的地方是:艾克一方面是Torrent 的前執行長(Torrent 公司以方便民眾分享檔案而聞名),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如何在崇尚平等主義的瑞典商業文化中,管理由一群自信滿滿的程式員所組成的快速成長公司。
有人說艾克就像是《湯姆歷險記》裡的湯姆,跑到了正吹著創業熱潮的斯德哥爾摩:他找到了一道圍牆,再讓別人來油漆。
但他真正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讓每個人都用自己認為最適合的方式來油漆。Spotify 的管理文化可說是與權威控制完全相反,艾克借用了「敏捷軟體開發(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方法」的原則,整合成為他所謂「小隊化」(squadification)的管理體系。
這裡所稱的「小隊」(squad)會完全負責某項產品的特定方面(例如搜尋功能、或是使用介面)、或某些商業活動(例如某特定市場的銷售)。小隊裡不會有特定的老大,只會有一位所謂的產品負責人,負責確保團隊每個人都能夠得到做好工作所需的一切資源。產品負責人也要注意小隊自訂的目標和期限,但不像是傳統的團隊領導者,小隊裡的產品負責人並沒有強制執行的權力。
另外,小隊還有一位「敏捷指導員」,但他也沒有強制執行的權力,而是負責培養並促進團隊合作。
這一切背後的概念,都與傳統階級分明的企業大不相同。成員不用去問主管,因為你其實沒有主管。你該做的,是用資料來實驗、找出證據,然後與隊友、與其他處理相關問題的小隊、又或是你認為公司裡對特定問題有足夠知識的任何人,一起分享這些資訊。在取得意見回饋之後,自己(或整個小隊)做出決定,並盡快實施。過程裡如果有任何問題,就是你負責解決。
為了促進合作,避免各成員或各小隊各行其事、不相往來,Spotify 還架構了兩種組織:其一是,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人,須跨越小隊,橫向組成「分會」(chapter);其二是,處理類似專案的不同小隊,須組成「部落」(tribe),人數不得超過一百五十人;而在「部落」這個等級以上,還有「行會」(guild)。這整套架構的主要目標,就是促進全公司上下的資訊及知識流動。
為了確保業務策略和決策一致,雖然Spotify 的組織表是流動的,但還是有「系統負責人」和「首席架構師」這兩個職級。只不過,實務上就算是這兩位最高層的管理人員,也沒有下命令的權力。他們的身分就像前面提到的小隊產品負責人和敏捷指導員一樣,主要做的就是溝通協調—如果希望看到自己的意見能促成行動,只能軟的靠說服能力、硬的靠資料證據。
對於這種重視意見回饋和輔導指導的企業文化,Spotify 深感自豪。只要能學到教訓,就算失敗也沒關係(事實上,有些小隊甚至會有「失敗紀錄牆」,強調自己學到了哪些教訓)。這種企業文化的核心,在於把「回饋和教訓」與「工資和績效」的討論分開,談到工資和績效的時候,還是採用比較形式化的階級結構—雖然談到要學習教訓的時候,同儕的意見非常重要,但講到個人的工資和績效問題,就不是由整個小隊來討論。
Spotify 認為,這樣一來,小隊裡面不用怕給別人負面評價,也就能夠促進理性公開的意見回饋。Spotify 甚至還開發了一項內部工具,希望彼此多多互相給予回饋。
在企業中引進市場機制
Spotify 小隊模式背後的概念,與創辦人及員工團隊的價值觀不謀而合。這套做法之所以能成功,部分原因在於Spotify 所處的產業並不是法規森嚴、紀律嚴謹的產業(不像是醫療保健或金融業等等),而是一個競爭激烈、必須持續創新的領域。也有部分原因在於,Spotify 的組織架構非常適合數位新創公司—因為資料豐富、且容易取得。
但還有另一個原因,讓Spotify 選擇小隊這種模式。除了前面所提那種共產主義式的願景,以及看似擁抱了小型、可適應、鬆散有彈性的組織模式,我們也會看到Spotify 正在向其組織結構,注入一點屬於市場的DNA。畢竟,分權決策正是市場的特色,把這種極端的分權做法帶進企業,就是讓企業帶有一點市場風格。
Spotify 這個例子之所以有趣,在於這家企業避免成為傳統企業的方式,就是讓自己成為一種混血的組織:有些企業的成分、也有些市場的成分。
在企業中引進市場機制,並不是什麼全新的概念。雖然做法各有不同,但其中的共同點都在於把部分的管理決策分權出去,採用更像是市場的機制。像是強鹿(John Deere)公司之所以能從曳引機製造商,轉型成為連網農業(connected farming)的世界級領導者,靠的就是改變企業文化,走向「以自我組織的團隊,推動更快、更分權處理」的決策方式。奇異(General Electric)和西門子(Siemens)也發現中央決策太過頻繁,有時也鞭長莫及,於是推動將供應鍊和生產操作的決策權,分權給地方單位。媒體巨擘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為了推動加速創新,也舉辦各種概念競賽,不僅是找出好點子來頒發獎項,更透過湯森路透內部的創業投資基金為其融資,將好點子化為現實。
隨著市場獲得新的競爭動力,企業會發現,自己得要苦苦追趕。很有可能,我們在未來的企業會看到更多的市場DNA、更多的分權、更多的內部競爭。
但是,在企業打算擁抱市場的某些基本特色時,我們建議:企業可能也要調整如何擁抱的策略。市場本身正從「用金錢來潤滑」,走向「由富數據流來推動」,因此企業如果是擁抱、而非抵抗富數據市場,結果或許更有利。關鍵就是要瞭解,這些新市場其實需要許多元素,除了有豐富的資料數據流,也得有適合的演算法和機器學習系統配合才行。種種元素在市場情境中結合之後,對企業的決策者和市場參與者都一樣有利,能夠在擁有多項偏好的情況下,找出最適合的媒合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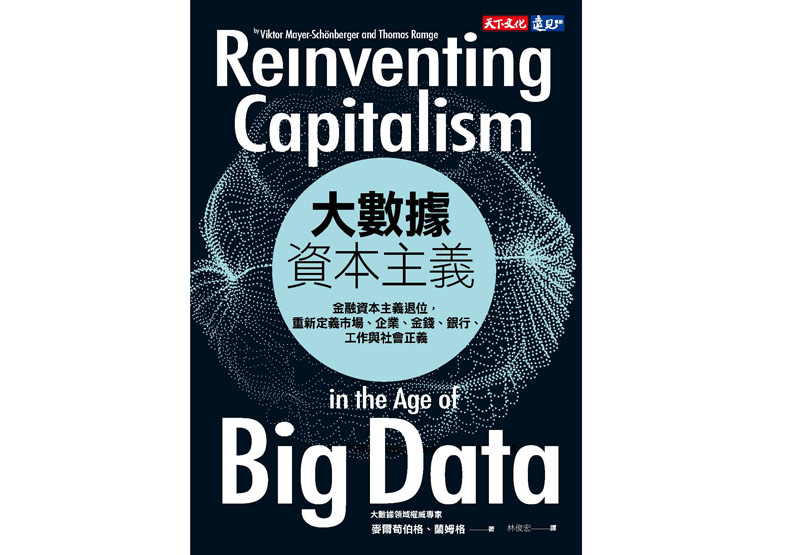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大數據資本主義》一書,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蘭姆格(Thomas Ramge)著,林俊宏譯,天下文化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