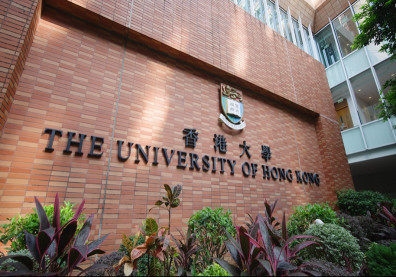傍晚六點鐘,上海下班的尖峰時間。一列由浦東陸家嘴金融區開往浦西方向的地鐵,結結實實塞進一大批下班人潮,將人們由新開發的浦東區辦公樓,送回浦西的繁華街市。車上乘客摩肩擦踵,幾無「立錐」之地。空氣裡瀰漫著各式各樣的體熱、香煙味、香水味,混合著焦躁的情緒,蒸發在車門開闔之間。如同世界其他大都會的捷運系統,上海地鐵乾淨、可靠、準時。但是引人注目的是,車廂裡的熱鬧非凡和混亂狀態。
車廂裡音量分貝高得嚇人,鬧哄哄的車廂裡,乘客之間正興高采烈地談天說地。聰明、麻利、激動、而又深具感染力地兀自說著,上海人的非凡活力,表露無遺。難怪散文大師余秋雨曾說,「到上海旅行,領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果不其然。
同樣身為華人,台北捷運裡的乘客不管再怎麼擠,也一定是和他人保持一個禮貌的身體距離。但是在上海,很難與旁人保持「安全距離」。
才剛剛在地鐵樞紐的人民公園站停妥,車門一開,人潮便如水庫洩洪般「爆」散出車廂;進出車廂的兩方猶如近身肉搏,誰也不讓誰;要是有人下車讓出空位,上車的乘客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搶成一團,就像電視節目裡的「大風吹」搶位子遊戲,十分狼狽滑稽,完全沒有秩序可言。但是上海人並不以為忤,他們很務實,而且善於競爭。
每當華燈初上,到上海著名的外灘萬國建築群前散步,瀏覽壯麗輝煌的夜景,是遊客到上海最常做的事。但在外灘堤岸步道前,川流不息的賣花小販,彼此搶著生意,其生存之道令人刮目相看。一位外地來的遊客天真婉言地問兜售玫瑰花的少女,「請問地鐵站怎麼走?」賣花的上海姑娘辛辣地回她一句,「不買花就不告訴你!」上海人精於算計,而且重視自身利益,完全不是「買賣不成仁義在」這回事。但是上海在外人眼中「現實」「貪小惠」「混亂」的印象之外,卻也意外充滿了另一種「秩序」。因為研究上海里弄建築,而需要走訪上海的東海大學建築系講師郭奇正,就曾有難忘的經驗。有次他不慎將昂貴的相機遺忘在出租車上,心理想著「完了!一定找不回來!」沒有想到出租車司機還在下車原處等著他。因為上海出租車發票上詳細列明車號,想賴也賴不掉,出租車司機怕人告發,丟了飯碗,大多很守法,現在上海人也懂得「小不忍則亂大謀」。
廣納百川的海派氣味
上海人精於算計,心眼兒細,但是他們同時也作風海派,廣納百川,對於外來文化,接受度很高,而且接受了之後還會將之積極改造,融為上海生活的一部分,最明顯的就在於上海吃的習慣。
暮春時節,上海已逐漸脫離冬日的陰冷潮濕。中午午休時分,穿著藏青色水手服的中學生,迎著春光成群結隊地逛著馬路,人手一杯來自台灣的珍珠奶茶,快意地度過悠閒的午後時光,這種飲料在上海是如此普遍而老少皆宜,讓人幾乎感覺不到它是「舶來品」。下班時間,來自台灣的可頌坊麵包店裡擠滿人潮,趕著回家的上班族撿著所剩不多的法國可頌,盤算著做為明天的早餐,西點麵包,就和豆漿、燒餅一樣,成為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從飲食文化的豐富,更能體會到上海接受外來文化的開闊胸襟。在上海,「吃」的豐富選擇,跟許多國際性大都市已經能夠平起平坐;光是中菜就流行有粵菜、川菜、寧波、杭州、湘菜、清真、新疆、傣族等菜系,而且上海人均能將之同化為「海派川菜」「海派粵菜」等口味。來自國外的法式、義式、德式、美式、日式、韓式、泰式、越式等國際主流菜系,選擇之豐富自不待言,連馬來菜、加州式烹調、印度料理、土耳其菜、黎巴嫩菜、斯里蘭卡菜、加勒比海料理、墨西哥菜在上海都不難找著,許多餐廳強調好吃,而且正統,由外籍主廚親自調理,這點連台北也比不上。
相對於擁抱外來文化,走在上海街頭,也可以覺察出上海人崇洋的潛意識。
一家大型百貨公司就直接在廣告打出其賣場「洋派、海派」的訴求。一向以偶像明星為促銷策略的百事可樂,在上海除了使用華人熟悉的港台明星促銷,在南京西路鬧街上的大型廣告看板,用的卻是英國足球金童貝克漢(D. Beckham)等人做為代言人,如果不是上海人熱愛足球,或是對金髮碧眼的洋人素有好感,百事可樂恐怕不會花大錢做這樣的策略布局。
上海百貨公司裡的服飾品牌,不論中高低檔,幾乎80%的品牌都有洋名字,以博取上海人的好感。對於西方流行的敏銳度,也明顯高於中國其他城市。
對於上海人的崇洋,對大陸消費市場有深入觀察的太平洋百貨大陸區執行董事王德明分析,長久以來上海一直是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也是所有外國進入中國的窗口,所以上海人接受西洋文化、受到西洋流行的衝擊也最大。
上海人好還要更好
崇尚外國文化、好求小惠以及「務實」的上海習性,其實歸根究柢,就是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讓自己看起來更體面,過得更舒服。在這一點,上海是野心勃勃的,有著積極進取的心,也有努力向上看齊的能力,而且上海人的眼界很高,身段擺得不低,即使好了還要更好。
在上海最受女性喜愛的高級百貨公司伊勢丹,論硬體設備及服務,在上海已算無懈可擊,但是一個紮馬尾的上海小姑娘,還是眨著精細描繪的眼,眉毛一揚對同伴白了一眼,「我看伊勢丹這電梯是很慢的呀!」開了眼界的上海人,隨時對現狀不滿意,永遠追求更高的目標和生活水平。
王德明也舉例說明上海人的眼界高,挑選能力強。早期許多台商以為上海是「丟垃圾」的地方,把賣不掉的商品轉銷到上海,「結果一件也賣不掉,」王德明形容,「上海人要的是全世界最新、最流行的東西。」
上海人如何在十年的時間自我提升,飛快躍進?曾經在1990年代開始前到過上海的台商們不約而同地回憶,「當時一出虹橋機場,沿途真是一片漆黑啊!」曾幾何時,四通八達的南北高架、內外環道路、地鐵、輕軌和數不盡的摩天高樓已經照亮了上海的天空。
看一下這樣的數據,就能瞭解上海人在近十年來如何急起直追,積極建設:在1990年時,上海不過只有七百多棟高層建築;2001年時,上海市區的高層建築已多達三千多棟,其中二十層以上的就占一千三百多棟,還蓋出了中國第一高樓——金茂大廈。
自從1986年中共國務院批准「上海城市總體規劃方案」後,加速了工業布局的調整與市政、交通、住宅環境的重新規劃,上海又重新變成中國商業、金融、服務業的中心熱點。
上海的重點建設區放在南京東路、淮海中路、西藏中路、四川北路等主要商業街道,以及豫園老城區、上海火車站前新發展的閘北不夜城。浦東更是大興土木重新改頭換面,設立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闢筆直寬敞的遠東大道,建立張江高科技園區,並將這個城市對外的空中港口,設在浦東新國際機場。
千禧年前後的上海,如同德國的柏林,像一個大工地般如火如荼積極建設,廣邀世界知名的建築師競圖,要讓世人眼光的焦點聚焦在上海。
不過上海比柏林更幸運;柏林是因為新德國遷都於此才大興土木,上海則是從半世紀的沈睡中醒來,急著趕上世界的腳步,沒有政治的包袱,全力發展經濟,就如同海派作家張愛玲在半世紀前寫道:「呵,出名要趁早啊!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上海人飛快地前進。
不只是萬丈高樓平地起,2001年的上海也有許多修繕的工作持續地進行中,新舊建設,一手做來,目的無非就是為了要在國際露臉。有了風光的財富五百大會議(Fortune 500)為其建設的成果背書,上海迎接2001年下半年的APEC亞太經合會更為起勁。走在市區的街上,不難看見紅色布條「迎接APEC,改進市容」橫亙在每一幢搭起的竹鷹架,等待整容「拉皮」的建築物上,宣示上海重新出發的決心。
重拾昔日榮光
入夜之後走在上海街頭,鑽土機依然「轟隆轟隆」響個不停,焊接的火花四濺在街道,打地樁、修路等工程持續進行,套句花旗銀行從前的廣告詞:「The city never sleeps!」(這城市永遠不眠!)這話挺能傳神描繪眼前上海的實幹精神。
上海曾經有許多的世界No.1,為上海攏上了燦爛的光環,那時上海有著遠東最豪華的飯店、遠東第一高樓、從蘇伊士運河到白令海峽間最昂貴的建築等輝煌;如今上海決心要再重拾往日榮光,積極地城市建設,造出亞洲最高樓金茂大廈、亞洲最高的電視塔東方明珠塔、中國最大的購物中心港匯廣場、最大的百貨零售業浦東第一八百伴百貨等。
藉著這些龐大的都市建設,上海成功凝聚起市民對自己城市的驕傲。一片介紹上海的光碟上就野心勃勃地寫著:「要看兩千年的中國,就看西安;要看一千年的中國,就看北京;要看百年的中國,就看上海,」顯見上海人已自視為中國潮流的領導前鋒。
在層層拔地而起的高樓中,上海的城市規劃也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要快速創造出摩登現代都會的外貌,曾經以法國梧桐夾道的優雅綠蔭而聞名的上海,也相當重視都市的綠化和都市風情的塑造。光是在淮海路,上海市捨得在寸土寸金的商業街沿線,闢建淮海公園,塑造都會閒逸;在新天地附近將大批石庫門居民遷動,請來美國著名的SOM公司規劃大型人工湖及遊憩公園;也在雁蕩路劃出步行街,模仿巴黎香榭大道的露天咖啡座風情。
走在高層辦公樓林立的陸家嘴綠地,抬頭四顧,竟會覺得這個四面為玻璃帷幕所包圍的公園,竟有些像紐約的中央公園,為城市裡汲汲營營的上班族提供一個放鬆心情的去處。上海似乎有心在向上攀爬的過程中,吸取西方都市成功的規劃經驗,建立一個兼容並蓄的都會,可以像東京、紐約、巴黎般繁華進步,又能夠如同雪梨、溫哥華般休閒舒適。
在新舊之間掙扎
但是上海在過於快速的前進步伐中,也處處讓人感覺到新與舊、進步與落後、西方與東方、快與慢、安全與危險等衝突的拉据。
在上海十年的快速發展中,許多硬體的城市建設已有了國際性大都會的面貌和格局,但是上海人還在快速的變動中,學著做為一個摩登都會人。在這樣繁華的都會,街頭卻還要豎立「七不規範」標誌,要人不隨地吐痰、不丟紙屑、不亂穿馬路……等。可是說時遲那時快,往往一口痰便飛到你腳邊,街頭的行人也從不理會紅綠燈,永遠「要快不要命」。
上海有市級優秀建築三百三十七處,曾經華麗而精美的建築古蹟,在上海市區比比皆是,這也是這個城市最豐富的資產之一。但是急於現代化的上海人在不斷的破壞中,建造新生活。世界知名建築師貝聿銘在上海的祖屋,就在無情的拆遷建設中,硬生生地被宣判「死刑」,急得大建築師親自出面呼籲保留。
上海的新舊掙扎,就是如此劇烈。
上海的建築讓這個城市充滿了昔日的輝煌和揮之不去的靈魂,是一個充滿著1930、1940年代藝術裝飾派(Art Deco)風味的城市,絕少東方城市能保存如此多的藝術裝飾派線條,至今餘韻繚繞,揮之不去,但上海人卻對這樣的寶藏渾然不知。
精美而破敗的建築,散落在上海的街道,看起來優雅迷人,但是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風霜,也逐漸顯露出老態。
當觀光客駐足欣賞這些美麗的街頭風景,卻往往很難體會居民的困苦,一位居住在虹口區洋樓裡的老太太,就忍不住抱怨自己的房子遇到雨天就是「外頭下大雨,裡頭下小雨」,還要遊客替她「向上級反映」。
許多摩登的上海年輕人對於自己城市的歷史所知不多,因為過去整整一個世代的人全部將精力消耗在文革十年的破壞中,沒有人告訴他們曾經的過往傳奇。
但是在經濟開放後,卻因為一種集體的時代氛圍而追求一種懷舊,這種情懷,也在善於鑽營的上海成為一種商業訴求。於是許多懷舊商店、懷舊酒吧便趁勢而起,興起一股潮流,成為既要「瞻前」也要「顧後」的一種矛盾心情。老一輩的便對這股懷舊熱不以為然,「這些小毛頭,又沒經過上海昔日的繁華,懷甚麼舊呢?」
用敏銳的心思遊上海
遊走上海,要準備一把放大鏡,帶著和福爾摩斯般大偵探的敏銳心思,深入城市的身世,將這個大都會抽絲剝繭,找出它享樂的、物質的、歷史的、滄桑的、斷裂的不同風貌。金嗓歌后周璇半個世紀前唱出「夜上海」,那種「華燈起,車聲響,歌舞昇平,」的迷離,不知道現在拿來做為上海的背景音樂,是不是依然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