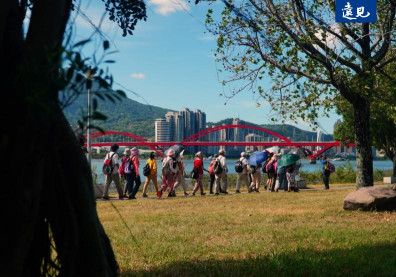【亞洲地方創生】一位雲科大的大學老師,長達十年陪伴同一個小鎮進行地方創生。小鎮文創創辦人何培鈞感恩這樣的陪伴,也認為大學的課程可以搬到地方,以創生做為教學的現場,讓大學的人才就是地方的人才。
我的人生非常幸運,遇見一位能夠陪伴地方十年以上的大學老師,雲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的張文山。
從我擔任民宿管家、成立小鎮文創、舉辦竹山光點小聚、活化竹山台西車站、到建立亞洲創生數位匯流中心,一路以來,在所有艱難的現場過程當中,這位老師一直是相當重要的合作夥伴。
他是唯一一位看著我們逐步成長的大學老師,也是最深刻理解我們精神的大學老師。

他每年總是帶著學校的師生,進場到竹山場域,進行經驗的傳承,也把竹山累積的能量,帶到其他的鄉鎮協助更多偏鄉,我們經常互相勉勵,彼此學習也相互珍惜。
大學被過度計算的指標所綑綁?
事實上,台灣的大學教育體制正面臨許多嚴峻挑戰,無論是少子化的招生、趨勢多變下的學校定位、績效壓力下的教師升遷,以及解決台灣社會未來困境等問題,都是現今大學的考驗。
這不禁讓人疑惑:當台灣高等教育體制,已經出現各種嚴峻挑戰的當下,還有能量能夠解決社會問題嗎?
當老師已經被量化績效制約,壓迫到還能有時間進行社會問題的沉澱與思考嗎?
學校唯一能獲得信任的體制,彷彿是需要透過許多獎項與名次。台灣的大學是否為了競爭國際與國內排名成績,也正面臨著被過度計算的指標所綑綁?
還要問的是,一所大學的自信,除了排名之外,是否還有更多可做的事情?
台灣民間社會對於大學的期許,除了數據指標之外,是否能夠尋找出一所被地方真正需要的大學呢?

或許就像張文山師生,對地方創生的投入。
尤其,南投竹山的光點小聚連續十年舉辦,幾乎每場次他都親自參與,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何等珍貴的事情,畢竟沒有任何預算與經費支持。但是,文山老師卻不斷鼓勵大家,一定要努力的舉辦下去,才能夠找到自己由下而上的力量。
每次看見文山老師充滿熱情參加小聚,提供許多大學的知識,導入許多產學合作資源,帶動返鄉青年,以及試圖影響更多學校師生,進場到竹山進行自我探索學習,那些日常的地方陪伴所淬煉的點滴,逐漸成為地方與大學之間,彼此重要關鍵信任的積累。
大學的課程就是地方的課程,大學的人才就是地方的人才。
這樣的信任,或許,也是一所大學能夠充滿自信的重要來源,而非僅有來自大學排名的形式而已。

師生與地方一起探索,互相扶持成長
然而,在目前的大學體制下,很難引導老師透過教育現場,找到自己能夠投入,又同時滿足學校績效預期的地方。
如果老師個人都無法充分尋求自我,並實現熱情於教育現場當下,那麼一所大學又如何能在周遭鄰近的小鎮、農村與部落中尋求一個可持續的發展關係呢?
畢竟有太多時候,學校的計畫偏向短期,地方的期待卻是長期。
大學師生經常因為計畫結束之後,就沒有再回到當地去,而地方沒過多久,又有其他大學師生團隊,帶著不同計畫過來了。

因此,大學無法長期深耕地方,地方也無法持續反饋學校,彼此之間,都聚焦在計畫的成效上,而失去了社會責任的連結維繫,以及人才持續培育的關鍵累積。
如果一直都是屬於短期計畫與地方互動的形態,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從計畫的本質著手,當然可以短期合作,但是人才培育教學場域,卻是可以長期建立。
學校應該要讓老師、學生與地方一起探索,互相扶持,共同找到自我成長的平台。
像文山老師,就經常邀請竹山青創團隊、地方竹藝業師,以及非營利組織到雲林科技大學,成為大學課堂的業師,也帶著學生與他一起到竹山場域,試圖將大學校園內的教室移動到校外的鄉鎮當中。
大學學生流動到地方,地方在職生回到大學,人才流動需要長期經營。
如此一來,便創造了更多與地方實務經驗連結的機會,打破大學體制下的課堂教室與授課形式,讓地方與學校彼此之間建立一個中介課程。於是,連動了地方的行動參與,也擴大了學生的學習視野。

還有一個重點是,如果大學學生持續在地方長期累積,不要輕易離開,未來就可能留下來。
因此,今年(2022)竹山小鎮文創除了增收雲科大的校外實習學生進駐到竹山場域之外,每年也同時推薦許多優秀的地方人士,成為雲科大的「地方創生智能設計碩士在職專班」新生。
大學生能進駐到地方場域來學習,地方場域也能夠號召更多在職學生,重新回到學校進修。我們想做的是「讓大學學生到地方來,地方在職生重回學校去」,建立彼此持續不斷流動的人才狀態。在民間,不斷尋找一所被地方真正需要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