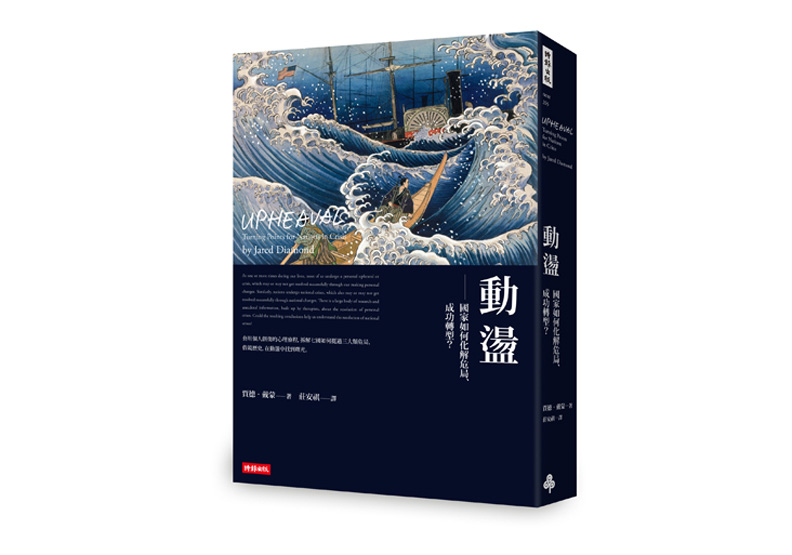從澳洲的角度來看,澳洲的身分認同,在1972年似乎突然發生全面性的變化,當時,澳洲總理高夫.惠特蘭(Gough Whitlam)領導的工黨,23年來首次掌權。他初上任的頭19天,甚至在任命新內閣前,便與副手展開澳洲選擇性變革的速成計畫,其速度和全面性,當代各國望塵莫及。這19天的變化,包括:軍事草案(停止國家徵兵);由越南撤出所有澳洲軍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國聯和聯合國交給澳洲,託管半個多世紀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禁止以種族選擇來澳參賽的海外運動隊(特別針對南非的白人隊伍而立的規則);廢除英國榮譽制度(騎士、官佐勳章OBE、爵級騎士勳章KCMG等)的提名,並以新的澳洲榮譽制度取而代之;還有——正式拒絕白澳政策。一旦惠特蘭的內閣人選獲得同意,就在速成計畫中,採取更多措施:投票年齡降為18歲;提高最低工資;賦予北領地和澳洲首都領地,在聯邦參議院中的代表權;在上述兩個領地成立議會;要求工業開發提供環境影響聲明;提高對原住民的預算;女性同工同酬;准許無過錯離婚;全面的醫療保險計畫;教育方面的重大變化,包括廢除大學費用,增加對學校的經濟贊助,以及把贊助高等教育的責任,由各州轉到澳洲聯邦。
惠特蘭正確地描述他的改革是,「承認已經發生的事」,而非憑空而起的革命。實際上,澳洲的英國身分已逐漸褪去。1942年,新加坡淪陷帶來首次的大震撼;1951年,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代表了初步的覺醒,共產主義威脅東歐和越南則是警告。不過,在新加坡淪陷後許久,澳洲仍然對英國懷抱期待和支持。1940年代後期,澳洲軍隊在馬來亞與英軍並肩作戰,對抗共黨叛亂分子,1960年代初,他們也在馬來西亞屬的婆羅洲,與印尼滲透分子作戰。1950年代後期,澳洲允許英國在偏遠的沙漠區,測試英國原子彈,以維持英國作為獨立於美國之外的軍事強權。1956年,蘇伊士危機,英國攻擊埃及,遭到國際譴責,澳洲是少數幾個支持英國的國家之一。1954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首次訪問澳洲,受到親英民眾的熱情歡迎:75%以上的澳洲人民走上街頭,為她歡呼。可是,1963年,當女王再次訪問澳洲,亦即英國首次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兩年後,澳洲人對她和英國的興趣已不復見。

在惠特蘭正式宣布之前,澳洲的白澳政策也開始類似地分階段解體。1949年,准許日本的戰時新娘入境,是第一階段。根據可倫坡亞洲發展計畫(Colombo Plan),1950年代,澳洲總共收了一萬名亞洲學生。1958年,取消鄙視移民的聽寫測試,同年的移民法,允許「傑出優秀的亞洲人」移民。因此,1972年,當惠特蘭宣布廢除白澳政策,並否決所有官方形式的種族歧視時,引發的抗議,遠低於廢除已實行一世紀的政策所會有的反應。1978年至1982年,澳洲收容中南半島難民人口的比例,超過舉世任何國家。1980年代晚期,近一半的澳洲人不是在國外出生,就是雙親之一在國外出生。1991年,亞洲人已占澳洲移民的50%以上。時至2010年,實際出生在海外的澳洲人比例(25%以上),乃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以色列。這些亞洲移民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他們的數量:雪梨的頂尖院校70%以上都是亞裔學生,2008年,我在昆士蘭大學校園內看到的亞裔學生,似乎占學生數量的絕大部分,現在澳洲醫學院學生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亞裔和其他非歐洲裔。
在政治和文化上,澳洲也有其他改變。1986年,澳洲終止了英國樞密院的終審權,進而廢除英國主權殘存的痕跡,澳洲終至完全獨立。1999年,澳洲高等法院宣布英國為「外國」。文化方面,1960年代,在澳洲獨領風騷,以肉派和啤酒為代表的英國烹飪,已讓多樣化的國際料理,大大擴展了美食風格,而非僅是1960年代的義大利、希臘,以及偶見的中國餐館。有些澳洲葡萄酒,今天,也榮登世界頂級之殿堂。(提示:我特別推薦一款很棒,但價格實惠的甜酒,迪伯多利酒莊(De Bortoli)的Noble One;好喝,但價格不那麼親民的佳釀,奔富酒莊(Penfolds) 的Grange紅酒;還有價格實惠,添加白蘭地的,莫里斯酒莊(Morris)Rutherglen Muscat的加度葡萄酒。)1973年揭幕的雪梨歌劇院,如今被成為澳洲的象徵,也是世界現代建築的偉大成就,由丹麥建築師約翰.伍重(Jørn Utzon)所設計。

我們是誰的論題,不僅關於澳洲的現實身分,也包括每一個可能的象徵身分。澳洲的貨幣,是否應該像英國一樣,採非十進制稱作鎊,或應該有澳洲自己的獨特稱號,例如roo(「袋鼠」kangaroo的縮寫)?(最後的決定是放棄澳鎊,改用十進制貨幣,採用美國或國際名稱的「元」。)澳洲的國歌,是否應該沿用《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1984年,英國國歌終於被《前進,美麗的澳大利亞》[ Advance Australia Fair ]所取代。)澳洲的國旗是否仍該保留英國的米字旗為基底?(現在仍然保持如此。)1915年,英勇的澳洲士兵在加里波利對抗土耳其軍,捍衛英國利益的事件,是否仍該做為澳洲最大的全國性慶祝活動?還是應該改由1942年,英勇的澳洲人在新幾內亞的科科達小徑上對抗日本人,保護澳洲的利益,獲得勝利來取代?(依舊是紀念加里波利戰役的澳紐軍團日。)以及,澳洲是否應該以英國女王為元首,還是該成為共和國?(仍然奉女王為元首。)
澳洲如何融入我們的危機,和選擇性改變的框架?
比起我們所討論的任何國家,澳洲的中心問題,始終是關於國家身分,和核心價值觀的爭論:我們是誰?澳洲是否為英國白人的前哨基地,靠近亞洲,卻對亞洲鄰國一無所知?澳洲人是否為忠誠的英國臣民,需要英國的認同才有自信,得依賴英國保護,認為自己的國家在他國不需要自己的大使,且為了表現對英國母國的忠誠,志願送大批人到對英國有戰略重要性,卻與澳洲不相干的偏遠的他方赴死?又或,澳洲是否為鄰近亞洲的獨立國家,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外交政策和大使,與亞洲,而非歐洲的關係更密切,且傳承自英國的文化內涵,是否與時俱減?直到二戰後,這個論題才開始變得認真,且持續至今日。就在澳洲爭論自己作為大英帝國海外前哨基地的身分時,英國也在爭論著自己身為該(正在衰落的)帝國的驕傲中心之身分,並努力爭取新的身分——和歐洲大陸密切相關的非帝國強權。
二戰以來,澳洲愈來愈展現出誠實自我評價的主題特性,因為澳洲人已開始體認到澳洲在現代世界情勢中的變化。澳洲人不得不認清,他們以往最親密的貿易夥伴英國,而今,只是一個小貿易夥伴;他們先前最大的敵人日本,現在,卻成了他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而且,澳洲作為英國白人在亞洲周邊的前哨基地,這種策略也不再可行。
澳洲變革的動力部分來自外在,部分則來自內部。部分動力來自英國國力衰退,英國海外帝國的終結,以及日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崛起。同時,部分動力來自國內,因為移民,使得澳洲的人口不再以英裔為主,轉而為與日俱增的亞裔,以及非英裔的歐洲裔,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政策的抉擇也有所不同。
澳洲非常明顯地說明了選擇性改變和建立圍籬。重大的變化包括,澳洲人怎麼看待自己有了轉變;制定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再交給英國決定;愈來愈多元化的族裔和文化(在城市比在鄉村地區明顯);以及在政治和經濟定位上,朝向亞洲和美國。但另一方面,其他重大事項並沒有改變。澳洲政府仍然是議會民主國家,仍然與英國保持重要的象徵關係,例如英國女王照舊是澳洲的國家元首;澳洲的5元鈔票及硬幣上,仍保有女王的頭像;澳洲國旗上,依舊可見英國的米字旗;澳洲按例保持高度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和強烈的個人主義;澳洲社會的澳洲風格依舊鮮明,例如對運動的熱忱:尤其是採澳洲規則的澳式足球(澳洲發明,只適用於澳洲)、游泳,以及英國的板球和橄欖球。澳洲的領導人們也參與這種全國性的休閒活動,即便有危險性:總理哈洛德.霍特(Harold Holt),1967年在任時,在水流強勁的海域游泳時,不幸溺斃。
大部分國家在做出許多選擇性改變時,都是經年累月,單獨進行不同的改變。澳洲總理惠特蘭,卻在1972年12月1日至19日,為期19天之內,旋風式推動多項改革,是少數以統一計畫同時進行多項變革的例子之一。
擺脫地緣政治的約束這個問題,對澳洲非常重要,而這種自由(或缺乏這種自由),則隨著時間起了變化。二戰以前,海洋保護澳洲免受任何實際的攻擊風險,正如美國獨立後,也依靠海洋的保護,直到2001年9月11日,世貿中心遭到恐怖攻擊為止。自1942年2月19日,日本轟炸達爾文以來,澳洲人已經意識到,他們的國家不能再免於外在的限制。
然而,即使在1942年之前,歐洲主導的澳洲社會,也必須依賴友邦的協助:最初是英國,在第一艦隊抵澳之後的幾年裡,英國甚至提供食物,後來又提供防禦;但是,從二戰起,則仰賴美國。雖然澳洲在達爾文遭襲前,從未面臨直接攻擊的風險,不過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法、德、美國和日本的軍事和殖民,擴張到太平洋島嶼,確實造成澳洲人的隱憂。澳洲指望英國艦隊的保護,導致1930年代,未盡自我防禦之責,並任由軍隊萎縮。
這70年來,澳洲的改變並非針對迫切的危機,而是出於二戰以來,長期發展的漸進過程,而澳洲的英國認同從現實反轉為神話,致使這個過程加速。雖然澳洲人可能不會在自己身上使用「危機」一詞,我認為,把澳洲視為經歷了一場緩慢進行的危機有其用處,因為澳洲的選擇性改變問題,與其他因應突發危機的國家,所面對的問題相類似。在那方面,澳洲最近的變化,和德國同一個10年的變化雷同,當時德國也發生了緩慢的變化。在澳洲一系列的緩慢發展中,當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時刻:特別是「威爾斯王子號」和「反擊號」的沉沒、新加坡投降,以及達爾文的空襲,這幾件事,都發生在71天內。只是,澳洲的危機和變化,並不像1853年7月8日,培里准將率軍艦抵達明治時期的日本;1939年11月30日,俄羅斯襲擊芬蘭;1973年9月11日,皮諾契特政變和阿言德死亡;以及1965年10月1日,印尼的政變,和隨後種族滅絕般,驚天動地的打擊。
澳洲重新評估其核心價值,及其一連串選擇性的改變,肯定尚未結束。1999年,澳洲公投是否該放棄以英國女王作為國家元首,變身共和國。儘管公投以55%比45%的票數未過關,不過換作幾十年前,連要舉辦這項公投,都會讓人有無法想像之感,甭說有45%投「否」的可能性了。生於英國的澳洲人比例正迅速下降中;看來,澳洲再次舉辦是否成為共和國的全民公投,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況且,這回投「是」的可能性會更高。在10年或20年之內,亞裔人口可能會占澳洲人口及國會議員的15%以上,也會占澳洲頂尖大學學生50%以上。澳洲遲早會選出亞裔總理。(在我撰寫本文之時,一名來自越南的移民,已經是南澳州的總督。)隨著這些變化的展開,澳洲保留英國女王作為國家元首,貨幣上,印有她的肖像;國旗上還看得到英國國旗,豈非太不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