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插畫家Gary Baseman 舉行了一場頗盛大的巡迴展覽《歡迎來我家》(The Door is always Open)。以家為名,展場便布置成如家庭般的配置。有前院、客廳、餐廳、臥室、遊戲間、書房、走廊、工作間、小巷以及後院。只能走啊。」母親頭也不回地說。
前院佇立著雪人Happy Idiot 和冰淇淋Creamy,組成一個溫馨的歡迎隊伍。和我同時進去展場的,有一對母子。小孩約莫才三歲,指著各個角色一一詢問:「這是什麼? 」年輕的母親則耐心回覆:「這是冰淇淋呀,這是雪人呀,」進了客廳、餐廳,孩子依舊舉著天真的小指頭,指向每一個物件問:「這是什麼? 」「這是小惡魔唷,這是魚啊,你喜歡吃魚嗎? 」母親回答,不忘跟孩子多些互動。
到了臥房。孩子上前指指床單上的印花:「這是什麼? 」因為印花的面積不大,母親無法一眼看出它的形體,便更靠近些仔細看了,「是蝙蝠。」她認出來了。
「他們在幹麼? 」他抬起頭問。
母親沉默。
那隻蝙蝠正試圖從剖開的人體裡吸血。我說「試圖」,因為在插畫家的設定裡,他是一隻夢想成為吸血蝙蝠的果蝠,無法真正吸血。但那被斬裂的身體的確存在,也反覆出現在其他作品裡頭。他的圖畫中有許多斬剁、犧牲、刺穿、囓咬、吞噬的意象。他慣用讓顏料在形體邊緣流下的手法,也使人聯想到滴落的血。
那母親在大床前站了一陣子,也許在思考該怎麼解釋,但她終究沉默地帶著孩子離開那一張床。
這不就像是人生嗎? 父母竭盡所能(若他們沒有失能的話)為孩子擋下一切他們認為不適合讓孩子知曉的事,然而人生總有一天會走到父母都啞口無言的地步。
另一位我很喜歡的童書作者Maurice Sendak 也很擅長「藏」東西。他用細膩柔軟的筆觸把憤怒、恐懼、死亡、被拋棄的失落、性和罪,藏進野獸、大狗狗和小孩之間。他畫《廚房之夜狂想曲》,裡頭有小孩被放進火爐中烘烤的情節;在《野獸國》裡,當小男孩要離開時,野獸們哀傷地說:「為什麼要走呢? 我們這麼愛你,我們會把你吃了。」在《咕嚕咕嚕碰! 生命不僅只是這樣》裡,獅子說:「請吃掉我,生命就只是這樣了。」
許多藝術家都將血腥殘忍的意象藏在甜美可愛的角色塑造裡。這些藝術家都明白,早早告訴孩子世界滿是陰影並沒有什麼不妥,甚至是有益的。孩子其實充滿焦慮,而大人一直告訴他們「一切都很美好」,那些隱約的不安在心中造成矛盾,分裂成陰暗的魔物。
不說,是一種最恐怖的表達。
心理學家曾實驗:人們以愉悅的表情說著傷人的話,會造成對方的困惑。人是以表情及肢體動作來判斷對方情緒的。因此他們以可愛形象騙過觀者,訴說一個個挫折且殘忍的故事,向孩子傳達:「嘿,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唷。」也讓成人以比較不恐怖的方式,接受人生的醜陋。可愛的造型,讓他們有了被細看的可能。
作家Alain de Botton 在一次訪問中說:「我們的時代有個錯誤的成見,認為讓一個人高興起來的唯一方法是告訴他高興的事。而實際上,告訴他一些誇張的悲哀的事,效果要好得多。」而叔本華說:「也許可以這麼說:『今天很糟糕,而且以後只會越來越糟,直到最糟糕的事情發生。』」正是,這是個糟糕的世界。承認這件事,便能快樂地向前走。
當我看見提姆波頓《牡蠣男孩之死》裡頭的各種黑暗角色:生來便不被父母喜愛的牡蠣男孩,最後還被親生父親當作補品一口吃下肚;雙眼插上鐵釘的男孩、全身髒成灰黑色的垃圾女孩等畸零人角色,真心覺得他們比迪士尼裡任何一個眨著水亮大眼的角色都還要討喜。
給孩子沮喪的權利,給他黑暗,允許他哭。哭完了,孩子會自己找到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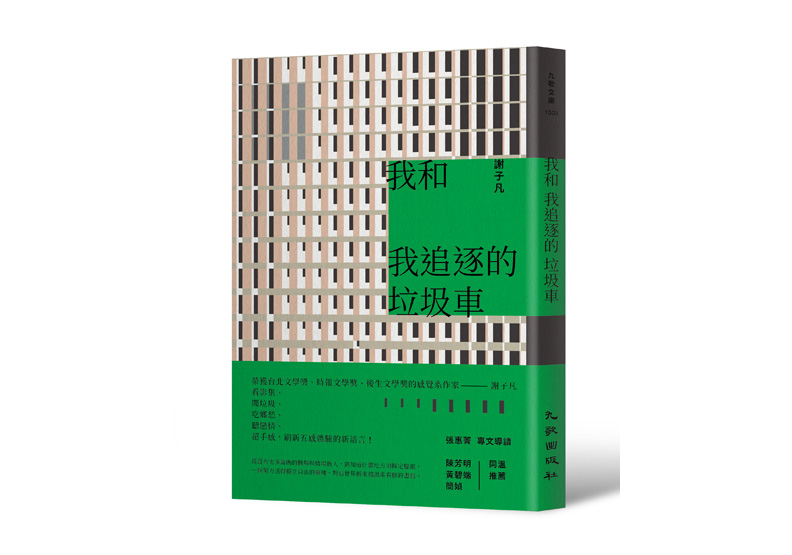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我和我追逐的垃圾車》一書,謝子凡著,九歌出版。
本文節錄自:《我和我追逐的垃圾車》一書,謝子凡著,九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