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15日,坐落在高雄縣燕巢鄉(編按:2009年高雄縣市合併,現為高雄市燕巢區)的義大醫院開幕。
鋼鐵業起家、義联集團董事長林義守曾經罹患肝癌,做了換肝手術,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他發願要蓋「一所最好的醫院」,便在一片荒蕪的田園中,蓋起這所五星級的醫院。
義大醫院從動土到開幕,其實外界都不太看好,不少人挖苦:「燕巢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怎麼會有傻瓜來蓋醫院?」
如今,來到義大醫院的,盡是開車從交流道下來就醫的民眾,還有不少人扶老攜幼遠從外縣市過來。院內除了五星級的硬體,醫術高明的醫師才是讓病人絡繹不絕的關鍵,一字排開的醫師陣容中,最具號召力的金字招牌,自然非杜元坤莫屬。
帶領「杜家軍」南下打天下
杜元坤在長庚醫院前後待了近二十年,離開的主因在於醫療理念與院方扞格不入。
在杜元坤的心裡,「病人最大」,別人認為沒救的病人,他也願意收。但院方認為,他做了太多沒必要的治療,影響醫院營運成本,雙方時有口角,爭執到最後,長官訓他:「你不要以為自己很厲害,那麼多病人看的還是長庚醫院這塊招牌。」
杜元坤反駁:「病人是為了找我看病,才會來長庚醫院。」因為立場不同難有共識,最後總是不歡而散。
這些都被當時的整形外科主任陳宏基看在眼底,有天便對杜元坤說:「既然你在長庚醫院這麼不開心,要不要跟我去南部打天下?」
「南部的哪家醫院?」杜元坤問。
「叫『義大醫院』,還沒蓋好,我們可以重新開始。」陳宏基答。
「還沒蓋好?可以信得過嗎?」杜元坤語氣難掩懷疑。
在陳宏基的安排下,杜元坤還是與董事長林義守見了一面,林義守打聽過杜元坤的薪水,願意給他雙倍,但他更在乎的卻是「自由」。
「我願意開一些在健保制度下可以幫醫院賺錢的刀,但也要請您同意,讓我做一些不會賺錢,但有意義的手術。」杜元坤強調。
林義守同意杜元坤的要求,雙方一拍即合。
杜元坤要離開長庚醫院的消息隨即傳開,很多人認為不可能,因為他是院內的當紅炸子雞,還是副院長的熱門人選,怎麼可能放棄已經打下的事業?
為了宣示離開的決心,杜元坤在院內的忘年會上,當著骨科大老面前說:「有志氣的話,就跟著我走,我帶你們去金銀島,挖到寶藏,大家同享;如果沒有寶藏,我養你們。」立刻引起現場騷動。
當時的長庚院長陳敏夫也表態慰留,但杜元坤心意已決,「我就是要證明,我的病人多,不是因為長庚醫院廟大,而是靠我自己的本事。」
而在杜元坤號召下,當時長庚骨科的19名醫師,其中五名子弟兵隨他南下,等於走掉三分之一,而這支來自林口長庚的「杜家軍」,也成為義大醫院開院以來最堅強的團隊。
勇於打破醫界舊習
杜元坤是義大醫院第一任的骨科部部長,他 2004 年初就到職,醫院還未完工,閒不下來的杜元坤,就帶著長期合作的手術房助手徐德金,到高雄各大醫院開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做這些手術不但分文未取,還自掏腰包付徐德金車馬費。
徐德金曾經問杜元坤,為什麼要做這些免費手術,他回答:「我們從事醫療工作,要有俠義之心。」
義大醫院正式開幕那天,手術室開始啟用,第一台手術就是由杜元坤操刀,這也是義大醫院的第一台顯微手術。
創院之初,杜元坤原是骨科主任,他指派子弟兵于尚文醫師負責脊椎、顏政佑醫師負責關節重建、馬景候醫師負責骨折外傷,高逢辰醫師則負責運動醫學。在他領軍下,義大骨科獲得病患好評,為了擴大服務的能量,骨科正式升級為骨科部,由杜元坤出任部長,底下分設脊椎、關節重建、骨折外傷、運動醫學等四大次專科,2011年又成立手外科。
從住院醫師開始,杜元坤就不是乖乖牌,升上長庚外科部部長後,他有很多改革的想法,卻礙於施展空間有限,但來到全新的義大醫院後,更可以放手一搏。
首先,杜元坤打破台灣骨科因循多年的手術特權。
杜元坤解釋,外科界是師徒制,住院醫師跟著「老師」(指主治醫師以上的醫師)做手術,老師開什麼刀,學生就可以跟著開。弔詭的是,當學生通過專科醫師考試,成為主治醫師,可以獨當一面時,老師擅長的手術,他卻不能碰,只能去做那些不常見、困難度高、健保給付低,老師不太願意做的手術。
杜元坤對於這樣的陋習,相當不以為然,因此極力改革。在義大醫院的骨科,年輕的主治醫師只要想做的手術就可以爭取,完全不設限。另外,杜元坤給主治醫師5年時間,去摸索選擇自己想待的次專科,而且選定後,還是可以開其他專科的手術,這種開放作法,在台灣醫界可說是一大創舉。
創新晉升、薪資制度
至於主治醫師的晉升和薪資待遇,不同於醫界的慣例,杜元坤也大膽創新。舉例來說,每家醫院的主治醫師名額有限,總醫師就算拿到專科醫師的執照,也未必能留下來當主治醫師,通常還是得看老師、主任的意見;義大骨科的作法是名額不設限,由科內所有主治醫師一起投票決定,能否留下來晉升為主治醫師。因為採記名投票,為了避免有人揣摩上意,杜元坤刻意排在最後一個投票。
薪資方面,也打破金字塔式的作法,骨科部的所有收入,根據工作表現合理分配,不再是少數人拿走大部分報酬,所以義大骨科主治醫師的薪資也高於同業。杜元坤認為,醫界重視資歷輩分,但很多「老師」功成名就後,往往就停止成長,甚至為了避免學生成為競爭者,設下諸多限制,固守自己的優勢。但杜元坤反而是不斷致力於手術的創新,每開拓出一個戰場,當發展成熟後,就留給學生經營,自己又去尋找新戰場。
義大骨科的另一大創新與特色,就是「國際化」。由於杜元坤的手術享譽國際,各國都有醫師前來義大醫院擔任研究醫師,除了看杜元坤手術,也要上台報告,接受批評。
為了培養並提升院內醫師國際化的能力,杜元坤用英文教學,骨科每週兩次的晨會,也一律以英文報告。這在台灣骨科界是首開先例,後來慈濟醫院、榮總也採類似作法。
學習慾旺盛,是杜元坤不斷成長的主因。他每次出國開會,都是實實在在地「開會」,除了自己演講的場次,其他時間都專心當個聽眾,連非他專業的講題,也會抱著吸收新知的心情全程聽完。而且會後隨即搭機返台,完全沒有任何「放鬆」行程。旁人看他,生活樂趣實在太少,只有他自己清楚,學習就是最大樂趣。
向副教授學習的教授
在美國進修就做過研究的杜元坤,到了義大醫院後,也想要學習如何組織團隊來推動研究計畫。自認沒有受過相關學術訓練的他,竟做出一件讓眾人跌破眼鏡的事——報考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不同於學界,通常得具備博士學位,才能晉升教授。醫界只要在醫學中心教學,並且持續有SCI論文發表,就有機會晉升為副教授、教授。
由於杜元坤於二○○七年報考成大時,已經是副教授資格,因此面試時被問到報考動機。他誠實以對:「我的目的不是為了學位,而是想跟著你們學習如何做研究。」
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是工學院,杜元坤考上後,還認真地和大學部學生一起修工學院學分。博士班第二年,杜元坤已經晉升為教授,但是有些研究所的老師還只是副教授,狀況變成副教授指導教授,難免有點尷尬,老師還對他說:「你已經是教授,可不可以不要念了?」
「我當然還是要念完。」杜元坤強調:「我跟著你們學習,你們就是我的老師,不會有任何問題。」目前在義大醫院週邊神經與復健研究室擔任研究員的蔡依蓉,是杜元坤的博士班學妹,因為一起上「醫學影像」這堂課而認識,由於杜元坤經常得從高雄趕去上課,常請蔡依蓉幫他占位子。
「跟多數學生一樣,我通常是挑靠教室門口的位子,但杜院長一定要坐前三排、靠中間的位子,我為了幫他占位子,只好跟他一起坐中間。」蔡依蓉笑道:「所以,我可以為杜院長的出席率作證,他除了出國開會,否則一定會來上課。」
期末考時,醫學影像這堂課除了需要寫程式,還必須上機Demo,同時回答老師的問題。蔡依蓉回憶,當時杜元坤先進去考試,考完出來還陪她坐在階梯上,提示老師會問的問題,「那時候他已經是醫院副院長,但是在校園裡,不論是對老師或同學,他都是客客氣氣,完全沒有架子。」
還清家中九千萬債務
除了帶領義大醫院骨科部,杜元坤回南部到義大醫院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要解決家裡龐大的債務。
從小衣食無虞,杜元坤從未對家中的財務傷過腦筋。怎麼也沒料到,父親過世後,母親才向他揭露,家中財產所剩無幾,還欠下九千萬元債務。杜元坤不敢置信。原來父親晚年因為糖尿病纏身,事業幾乎全數停擺,旗下七、八家公司早已不再運作,而母親又受人慫恿投資錯誤,虧損後又去信託貸款,債務越滾越大。
面對九千萬元的債務,身為家中長子,杜元坤責無旁貸。他自知,光靠當醫師的薪水,只夠支付貸款,若要還清家中債務,就必須處置父親所留下來的資產,包括公司、房子、土地等。
舉例來說,杜元坤父親曾在台南市區蓋了一幢七層樓透天厝,原本打算留給兒子開業,後來因故作罷,房子就一直閒置。為了還債,杜元坤決心賣掉這棟房子。只是買家知道他有債務壓力,故意壓低價錢。杜元坤沉住氣,不急於出手,先重新裝潢房子,再請朋友出面賣屋,最後比之前被砍的買價,還多賣了兩千多萬元。
至於其他公司,杜元坤也善用相同的「包裝」之道,提升公司價值,再找買家。他逐一出清,而所有處分資產的所得,都用來還債。
「賣公司時,要和等著領退休金的『老臣』談遣散;賣土地時,要與掮客周旋。我只是個醫師,哪裡懂這些,只好硬著頭皮一件件處理。」杜元坤透露,他前後花了12年,和弟弟、妹妹合作下,才終於還清負債。
自杜元坤到高雄後所做的每件事情,不論是領軍義大醫院的骨科部、攻讀成大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班,或是償還家中龐大的債務……,對一般人來說,能夠完成其中一件事都屬不易,杜元坤卻一一做到,而且為了替醫院衝業績,平日還有大量的門診和手術,能力和毅力都非常人所能企及。
杜元坤深信,人的潛力無窮,只要設定目標,一路堅持做下去,最終一定會有所成就,而他就是最好的示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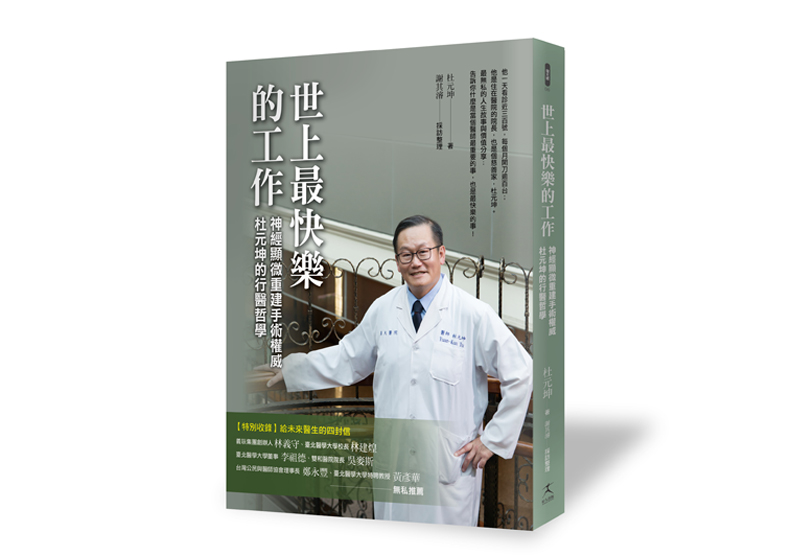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世上最快樂的工作:神經顯微重建手術權威 杜元坤的行醫哲學》一書,杜元坤、謝其濬著,好人出版。
本文節錄自:《世上最快樂的工作:神經顯微重建手術權威 杜元坤的行醫哲學》一書,杜元坤、謝其濬著,好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