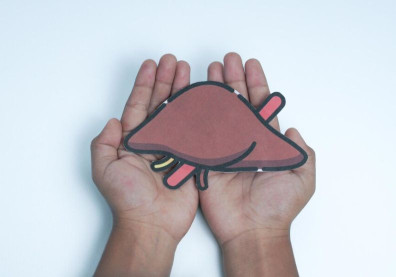有人說,切格瓦拉之所以會成為拉丁美洲的革命烈士,是因為他在24歲那年,騎乘著摩托車環繞南美洲,親眼目睹了貧窮的無所不在而深感震撼,自此埋下了他革命的種子。當他再度回到阿根廷的家時,他在一篇日記寫道:「寫下這些日記的人,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便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旅行的意義,除了點到點的移動,或許更是一種面對自我的深層反動,旅行結束後,世界如往常般運作,但反思過後的心境變了,世界也許就不一樣了。
2014年「香港占中」事件截至12月11日以警方清場收尾,香港人為爭取真普選的抗議運動維持了整整75天,在香港社運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章。理著極短的小平頭,林輝一坐下來,便分送我們「香港要普選」的貼紙,10月初,他本該在南美洲繼續環球的旅程,然而一聽說香港因為「雨傘運動」,被警方扔了數十枚催淚彈後,他決定暫停旅程,先回家。
從亞洲到歐洲、從中東到南美,22個月的時間,林輝的足跡遍布超過40個國家,他是香港先鋒型的社運人士,也是活躍於香港媒體的專欄作家、時事評論員,保衛天星碼頭、反高鐵及反政改的運動中,皆能看見他衝撞權威的身影。
相較於過去在社運裡的衝鋒陷陣,暌違兩年的抽離,他選擇靜靜的睡在街頭支持占中運動,偶爾在臉書上發文表達看法評論。他曉得香港將會因為這次的抗爭,而有天翻地覆的改變,對於占中運動所凝聚的後續力量表示樂觀,而這次他想花更多時間思考香港的處境與下一步。
就像他在旅途開始前問自己的:「我還能為香港做些什麼?」
■透過「移動」,看見世界
旅行是單純移動的過程,旅程結束便踏上歸途。但有一種移動,是流亡與逃難,是更真實的移動,因為那無法回頭,是無家可歸。透過這些移動的人們,我們看見世界的無奈,看見在希望背後的苦難。
熱愛旅行的林輝,家族本身就是一段移動史。每一代都在不同的地方出生,或許也造就了他血液裡喜愛冒險的心,以及對不同族群文化之間的包容。林輝對庶民生活、弱勢族群的詳盡觀察,都難以掩藏他的細膩感受。
活躍於社運圈的林輝,絕對不甘於只做一名旅者,於是他不斷的探索、發掘,兩年的時間,他親眼目睹了中國大陸鄉村裡的家徒四壁、敘利亞被綿延戰火摧毀的家園、遇見了無法離開西藏的藏人、經歷了印度大好年華的女孩,慘遭輪暴後的國內示威。
他的一位藏人朋友,花了27天翻過喜馬拉雅山到達尼泊爾,而過去數10年,已經有數以萬計的藏人,如此離開西藏。一名伊拉克女人,帶著孩子徒步走到敘利亞,卻遇內戰爆發,再度逃往約旦。如今這名女子無法工作、孩子不能上學,難民的身分,讓她與孩子們陷入漫長的等待,而在約旦和黎巴嫩,類似這樣背景的人,超過百萬。
面對這個世界不可思議的對立狀態,貧窮與富貴、文明與傳統、民主與獨裁,無盡頭的苦難,與相依而生的微小希望,彷若山脈深沉的回聲,身歷其中,林輝頓感自己的渺小。
對他來說,旅行不只是單純移動,更是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文化之間最真實的情感連結,而唯有讓苦難被看見,才能真正理解這個世界。愈認識這個世界,愈能用同理心去關心,旅途中所面臨的文化差異,孰是孰非,也都只有親身經歷了,才能有自己的答案。
■我們是獵物還是獵人?
這世上的受害者通常也是加害者,是獵物也是獵人。在這個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裡,仇恨與傷害環環相扣,而真正製造悲劇的,便是人與人之間冤冤相報,無止境的仇恨。
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曾形容,「我們環繞世界旅行的時候,第一件看到的是,我們的污穢,投擲到人類上。」在旅行的路途中,他往往看見西方文明對其他地區的摧毀。
林輝也曾在雲南麗江的大研古城有相同的感慨,一個享有近千年歷史的文化居所,被現代化的商店、旅店摧毀,他看不見屬於當地的「生活味」,於是他開始反思:「作為一個旅行者,到底是否也是摧毀別人民族文化的兇手呢?」
一直走在看見真實、理解他人的旅途上,他不斷在旅程中思考、尋求解答。
看遍了許多也許不會有盡頭的苦難,也許耗費一輩子仍難以解開的結,歷史從來都是各說各話,每段解讀都沒錯,但戰爭卻因此而來,那戰爭和仇恨是否就無可避免?
他的話語中沒有過多批判的煙硝味,有的是他對飽受戰亂波及人民的無奈,以及發自內心的擔憂與關懷。對他來說,真正製造悲劇的,不是難以解釋的歷史、不在砲聲隆隆的沙場,而是人與人之間無止境的仇恨。
戰火長年不斷的以巴衝突,仇恨的結看似永遠解不開,然而在東耶路撒冷,有個專門提供因為以巴衝突而失去親人者的心理輔導及互助小組,他們安排兩邊死者的親友一同參與小組,站在眼前的彼此,理應是「加害者」,卻同樣都是「受害者」,雙方之間的一個擁抱,便足以化解無數個可能發生的悲劇。
這讓林輝非常感動,沒有國族之別、對錯之分,所有的問題回歸到「人」,便能看清事情本質,「當我們理解真正製造悲劇的是『衝突』時,那我們爭的就是和平。」
回過頭來看香港,林輝觀察到,香港正面臨香港本土和中國人之間的族群矛盾。他形容,香港這幾年多了許多恨,這些恨來自於大量的陸客湧入香港,而這讓他很不安,「我們可以討厭中國政府,但不應該討厭中國人,」他認為,人與人之間善意的溝通,才有化解衝突的一天。
■革命自救,朝未來的星星前進
星星在黑夜裡的沙漠指引著旅者方向,即使四周是黑暗的,但透過微小緩慢的步伐,也要朝眼前的那顆星星前進。不遠,總會走到。
香港「雨傘革命」發生後,林輝在臉書寫道:「『雨傘運動』代表著一場溫柔但堅定的運動,面對狂風暴雨,我們絕不逆來順受。」
這就是林輝,走過世界後,他深知沒有自然而生的幸福,人世間的悲喜交集,都得來不易,就像他看見的那些與衝突並存的希望,都是靠著民間的力量,親力親為的展開自救。
站在翁山蘇姬在緬甸被軟禁15年的家門口時,他想起翁山蘇姬曾說的一段話,在沙漠中的旅行者,朝著引導方向的星星前進,最終便能獲救。
那麼林輝的星空呢?
相較於過去廣泛地參與許多社會運動,接下來他將專注深耕難民與少數族群的議題,這是他在這趟旅行中找到的星星,面對全球最弱勢的群體,林輝想試圖拉近他們與社會的疏離與隔閡。
「我希望可以看清這個世界,和令更多人生活得更好,」兩年的時間,他心繫香港,不斷的尋找世界和香港的連結,林輝不諱言,自己還沒有找到答案,然而在與其他人的靈魂相互碰撞後,或許答案已經不那麼重要了,因為答案終會在一次又一次的思辨與互動中逐漸成型。林輝只知道,兩年的旅行,讓他自己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