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的律動
春天會騙人,先以溫煦的天氣誘你整地種植,再以一場霜降讓你後悔。
朋友趁霜降前來我家後院摘野生薺菜,移植到室內盆栽,桌上還有發芽的大蒜和蔥。先後自臺灣探親回來的我們,聊了些故鄉事。從母親那兒學來的雪梨紅燒排骨還剩下一些湯汁,我添了些水,下了麵條煨煮,離火後臨時起意,丟一把芝麻菜進去,當是為朋友加菜。我們都是矛盾人。在臺時,一攤接一攤的家鄉料理伺候下,想念美國食物;才剛返美,卻又迫不及待地煮起家鄉菜,複製心底的味。
 這一天,她聊她的老家,我聊我的。
這一天,她聊她的老家,我聊我的。
我的臺南老家是三層樓的透天厝,一上二樓,左手邊是我的房間,與樓梯只隔一面牆。樓梯口前方有個中庭書房,穿過那兒才是父母親的房間。三樓是娛樂室和弟弟們的空間。這樣的房間配置讓我離一樓廚房最近,也讓身為長女的我有守護全家的使命感。但我卻最早離家在外生活,從十七歲延續到現在。母親掌廚的日子裡,我從未下廚,反倒常把房門關上,隔離吵雜聲和油煙味。
婚後回臺灣探親,母親仍天天為我做飯,想伸個手指頭進廚房裡都被嫌。我賴皮地放任自己待在二樓房間,一邊翻書,一邊聽廚房傳來洗菜的流水聲,拍薑蒜的砧板碰撞聲,起鍋的盤鏟觸擊聲。有時我會憑聲音預測母親下個動作,比如聽到冰箱抽屜開開關關的聲響,我幾乎可以確定接下來會有句:「咦,我買的東西怎不見了?」當所有聲音逐漸緩歇,我知道該下樓幫忙盛飯、端菜了。這些從有記憶以來早已麻木的聲音,因我婚前不諳廚事,從未用心聽。
有人說,大腦以影像處理記憶。我始終記得每次下樓,視線從廚房淺綠的地板延伸到母親的拖鞋,再到她略俯的背和切洗不停的雙手。一年又一年,母親的背越來越駝,身影越來越小,廚房越來越靜。對於不住老家的我而言,每一、二年才看到的親人,變化總是太巨大。
有一年,母親忙著籌備同學會的小旅行,我終於找著藉口占用廚房,煮了鍋自以為是主廚等級的海鮮義大利麵,末了還切些芹菜葉末,取代不易買到的巴西利葉。我常突發奇想地將東西食材合併演繹,自認順理成章地融合了臺灣成長、美國居住的背景。母親一邊用筷子夾著吃,一邊說:「幸福!幸福!這味不錯。」如此的反應我當然清楚,它與食物是否有驚天動地的美味無關,而是當天天掌廚的人成了被款待的人,那帶著被感激與被體恤的幸福,是外食無可取代的。在當下,兩個靈魂都受到撫慰。我在國外繞了一大圈才得到這個領悟。
 春天會騙人,常說沒啥鄉愁的我呢?其實,我也不是常常念著故鄉的人,總因那兒有親密的家人和年少熟識的朋友,有我的成長,遂而有了無法割捨的戀與念。現在,我偶爾做個母親曾經做過的菜,即懷念起老家,想起她一雙手為家人做過的無數桌料理,那幾乎是她一輩子的事了。
春天會騙人,常說沒啥鄉愁的我呢?其實,我也不是常常念著故鄉的人,總因那兒有親密的家人和年少熟識的朋友,有我的成長,遂而有了無法割捨的戀與念。現在,我偶爾做個母親曾經做過的菜,即懷念起老家,想起她一雙手為家人做過的無數桌料理,那幾乎是她一輩子的事了。
每一雙揮動的手、每一雙伸出的手,都有段食物旅程。 有人看手對你說線條有多美,我可能也會,但我還讀了故事。
當我猶豫食物怎麼拍,怎麼做造型,又或道具難確定時,最簡單的方法是請手入鏡,將文靜的氣氛混入人情味,刻劃出生活的律動。有手的畫面放入同理心的貼近感,引人多看幾眼,還有引導和延展視線的作用,我即可以少在其他造型下功夫。然而,手在本質上是配角,非隨意置入的畫面。
既然手會入鏡,難免會想拍出如手模特兒的纖細貌。其實,手瘦長的人同樣有忌諱的拍攝角度,而胖與不上相沒有絕對的關係,得斟酌的倒是別讓手搶走對食物的專注。我從產品攝影師那裡學到幾招手攝影的撇步:將手的立體形態拍出,讓手有點幅度;若手臂入鏡,別讓手臂與身體過近,免得都聚在一起,把肢體變寬了;拳頭拱起,以及手指併緊、手背全朝鏡頭的模樣,都容易成為視覺焦點,盡量避免;正面拍,多顯示細指尖;善用景深虛化處理;為求美好合適的拍攝角度,可讓模特兒暫時應攝影所求,改變用手的習慣,如從右撇子調為左撇子。
我希望在最順暢的情況下拍手動作,所以進行中的場景最自然。若是安排模特兒,我會請對方以較緩的速度動作,而非擺固定的姿勢等我按快門。若是多人入鏡,除現場宴席外,我請參與者先想好不會把食物遮住的動作,待要按快門了再擺出手來。相信我,動作擺久了看得出僵硬。
在有幫手或模特兒的情況下,要拍人的動作還算容易。若只有自己的話怎麼辦?最平常的應付工具是搖控器。另一個方法是很久以前一時興起想來的。當時,我將幾本書堆起來,叉柄夾在兩本書之間固定,然後捲幾圈麵在叉上,於是成就了一張貌似手拿叉子捲麵條的相片。書上放隻夾鉗亦有堆高固定的功用。
手豈止手,食物豈止食物,它們是想像、是意境、是可能性,具有召喚的潛力。有手的食物攝影觸動感情,有動態的食物攝影增添畫面流動,宛如邀請觀者來到你的日常。如此親密,如此美好。
以下是一些補充技巧:
—特殊美學表達除外,手的出現必得合理且自然。
—當手較接近鏡頭時,先減少手出現的面積,再透過對焦食物主體,以調出景深並虛化手,即能避免手過於搶鏡頭。
—當影像中有人出現,就有可能轉移焦點,即使只是手,因此拍食物通常不會讓臉入鏡,並得小心用景深處理。若影像中的人是你想強調的(如料理人),又或是生活場景則例外。
—手拿東西時,四根手指並列正對著鏡頭的模樣,會讓手的面積變大,惹人注目,我會特意避拍這樣的角度。
—手或食器勿遮住食物,好讓觀者盡情假想美味。
—若有一人以上入鏡,每個人的動作盡量不重複。
—手質感無須完美,乾淨最好,避免穿金戴鑽配玉。若是拍與烹飪相關的過程照,如揉麵糰,手上有些麵粉才合理且貼近實際。若拍攝種植或摘取,雙手亦無須過於乾淨,有些土,才有些意境。
—手捧拍攝主體如湯碗時,食器與手的比例得恰當。大手捧小碗,易削弱觀者對碗的注意力,可利用景深將大手虛化,或調整角度,僅讓少部分手或單手入鏡。手挑揀雞蛋等小食材或倒小瓶醬汁的考慮亦同。手與物體太近鏡頭,易彰顯彼此的大小差異。
—若身體進入畫面,模特兒身上穿的衣服須合時宜,比方不穿冬衣拍冰棒。此外,初拍時由簡開始,模特兒身上的衣服(即背景)盡量使用中性色彩和素面,待掌握了與食物的顏色搭配,才增加色彩性和圖紋。
—當手和食物的距離相近時,兩者的顏色盡量別太相似,以免劃分不清。
—不同角度塑造不同氛圍。正面直拍最直接,有「你就來看吧」的意味。背面、上方、側面拍,另有一番情境,像是你跟著鏡頭到人家家裡。然不論怎麼拍,都得先找出可拍出食物美感的角度,再把人放進去,相互協調搭配。
手帶入日常節奏。圖5-9,一張有人在切麵包的相片,讓你在看到麵包質地之時,亦藉由周圍的擺設去推測麵包是怎麼做的、要怎麼吃。而在似明又暗的光線裡,你猜想眼前是清晨的進食時光,卻也不禁想或許是麵包剛出爐的下午。再看他手上的麵粉似乎在說,麵包是自家手工製的。一些漫不經心的小細節,像是切麵包時掉落的栗子內餡和麵包屑、用過的烘焙紙和切下後擺著隨意姿態的麵包,都有各自的表情,讓一張食物照不再是靜態的影像,還有日常的活絡。進食照也是生活照,攝影師讓你看別人進食,就希望勾起你相近的心情,最好也能飢腸轆轆。
(圖說:手框住食物。圖5-10,雙臂形成的 V 形線條將視線緩緩延伸,我認為是相當迷人的。拍體積小又缺乏動靜的食材,如小馬鈴薯、豆子、小魚干和小果實,我用雙手托著食物的動作來拍,少做其他造型。這麼拍有助於視線放在拍攝主體上,且能展示它的比例。我透過微光帶出黃瓜洋蔥沙拉食材的亮,以展示的方式邀請你來看我的碗,簡易明瞭。手擔負握食器的任務,予人穩定的視覺。我用暗調將手暗化一些,但近光的地方仍是亮,好顯現手的輪廓。有光感的皮膚才顯立體和細膩。)
手可以演戲。圖5-11,我將啃得乾淨的西瓜皮放到背景,開啟了進行式,而手拿西瓜的樣子則賦予「欲罷不能啊」或「偷偷拿一塊吧」的風趣。手指的形態是另一關鍵,最好不要是容易引起注目的握合狀,而是微分開的。這張相片的動態尚來自盤上西瓜前後擺放的樣子。
手傳遞資訊。圖5-12,我將印度餅麵糰下鍋前的最後動作拍下來:麵糰發酵後,在輕撒麵粉的桌上將之分成八等分。對焦於正在整形的麵糰,彰顯了動作,點出了前景和後景。手和身體當背景,詮釋參與者,多了人味和空間感,備料遂成了頗受歡迎的動態食物攝影。為了告訴讀者麵糰塑形或甜點製作的過程,食譜書常為麵粉類食物多加有手的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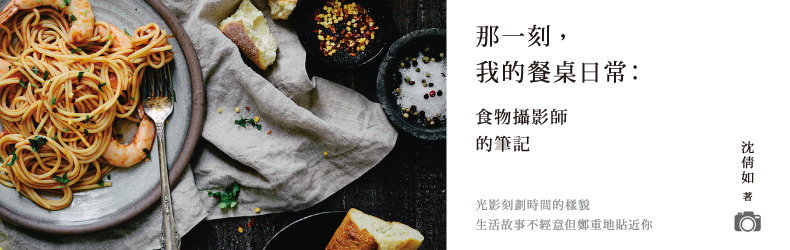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那一刻,我的餐桌日常:食物攝影師的筆記》一書,沈倩如著,時報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