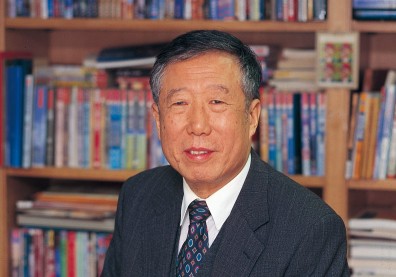另種特權,享受獨特的閱讀時光──陳千武、葉蔚南、楊翠、詹宏志
時間倒轉回1930年代,就讀臺中一中三年級的陳千武一身灰樸,臉上卻含光采。酷愛文藝的他已將臺中圖書館能看的書都看遍了,便利用放學等車回豐原那段時間,到中央書局去看書。天天站立書架前,將書一頁頁往後翻,兩眼掃描書頁,意識速讀吸收著。
圖說:中央書局是許多人的共同記憶。圓弧立面,柔和燈光,有溫度的階梯,溫馨拐角……,一個個成長身影經過、佇足留連,他曾經出現,喔,原來你也在這裡!(鄭硯允/繪)
一天,那看似書店主管的人向他走來,陳千武不好意思趕緊將書插回架上,兩腳打滑便要開溜。那人見陳千武要走,便喊住他:「嘿,你等一下。」
陳千武心底直覺不妙,擔心若要他買書,他可沒錢!
而對方卻問:「你剛才看的是什麼書?」
陳千武再將那書自架上抽出──
「啊,你喜歡文學作品?」
「是,我喜歡看!」陳千武的心懸吊著,不知接下來會怎樣。
「那你來。」那人便帶陳千武進到經理室,拿出他編的《臺灣文藝》讓陳看。
原來他就是張星建,陳千武從那時起才知道原來臺灣也有文學,張深切、張文環、龍瑛宗這些作家的名字開始進入他的視野。
張星建期待陳千武創作文學作品,留予後代作為文學資產,並要他以後別站著讀,可以到他辦公室坐在沙發上看書。
特別的待遇讓陳千武書讀得更多更起勁,也更熱愛文學。
「哇,多麼激勵人心!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便這麼被培育出來。」
「是啊,鼓勵求知,推廣藝文本是中央書局的創立宗旨,而後續的發展,也確實發揮了這項功能。」
「在中央書局享有特殊待遇的,可不只陳千武喔!」小凱顯然做了功課。
「啊,那還有誰?」
「葉蔚南啊!葉蔚南的父親是葉榮鐘。葉蔚南小時候父親便常帶他到中央書局,有時和朋友相約見面,有時進到二樓張耀錡的經理辦公室,和一群人聊天,那時候中央書局是『文化先』們談天說地的場所。」
葉蔚南記得讀初中時,父親有次帶他到中央書局,直接帶他進一樓辦公室找一位叫黃榮品的先生,告訴他,以後葉蔚南來買書請給他方便。從那天起,他在中央書局便享有讓同學羨慕的特權─買書可以記帳。
葉榮鐘對子女的教育向來費心,為鼓勵葉蔚南看書,採用了這種方式。如此一來,便可從月結帳單了解葉蔚南看了哪些書。葉蔚南回憶自己高中畢業前在中央書局買最多的書,除了歷史小說,就是英文小說。那時中央書局有一套簡易版的英文小說,書底有一段敘述:「只要能懂一千個單字,就能看懂這本書」,書裡還有這本書的單字介紹。葉蔚南便由一千字一直看到三千字的英文讀本。
葉蔚南記得1971年父親的《臺灣民族運動史》出版後,決定和母親前去美國探親,便到中央書局買了《英語900句型》勤加練習,琅琅上口。即便口音帶很重的日本腔仍不放棄,希望到美國可以和人溝通。回來寫的《美國見聞錄》也是由中央書局出版。
「另一個曾在中央書局享有特殊待遇的,則是楊翠!」
「什麼樣的特殊待遇呢?」
「楊翠與中央書局有著特殊情緣,除阿公楊逵偶會帶她去開會,另外,中央書局還是她專有的圖書館,書局裡的書她可帶回家看。」
「這事怎麼開始的?」
原來楊翠的姑丈就是中央書局的會計陳景陽,一天聽楊翠嚷著:「家裡都是阿公看的書,我找不到書看!」
姑丈疼惜她這樣愛閱讀,約定好如能將書保持完好,便可將書局的書借回家看。
那時楊翠小學五、六年級,從此她每星期都到中央書局借六、七本書,直到高中。她一開始先看兒童版的歷史故事,《東周演義》、《三國演義》,如薛剛鬧花燈、薛丁山、薛仁貴的故事,啟發對歷史的興趣;小六至國一開始看西方童話故事,如《伊索寓言》、《金銀島》、《湯姆歷險記》;之後看《亞森‧羅蘋》及《福爾摩斯》,那些書至今印象深刻,可說是她閱讀經驗最快樂的一段期間;另外如神祕百慕達之類的書她也很喜歡。
女中時期,中央書局是楊翠與臺中一中及其他文青約會碰面、情感連結的空間,而或許因自小在那借書,對它的主動性及興趣反而不若其它書局。1970年代後期,中央書局對楊翠而言只是眾多書局之一。
「可以盡情隨興享有整座書城的資源,感覺好過癮喔!」欣倫不禁羨慕了起來。
「是啊,尤其是在書籍流通還不是那樣豐沛的年代。」
「另一個人,他雖然沒有特權,卻因緣際會,讀了好多年以中央書局為轉運站的書。」
「有這種事?那人是?」
「詹宏志!」
詹宏志自小喜歡閱讀,草屯當時書的取得相當不易。家中無書,求知若渴的他幸虧有個在中興新村擔任公務員的姨丈,讓他有機會見著《胡適文選》、《朱自清文集》、蔣夢麟的《西潮》及羅家倫的《新人生觀》。
1960年代,臺北出版社及大陸圖書批發的書籍不直送偏鄉,詹宏志小學時,就讀臺中女中的姊姊長期幫草屯三省堂到中央書局取書,酬勞是那些書得在家中放置一晚,詹宏志因此得以遍讀那些書,馮馮的《微曦》、朱西甯的《鐵漿》 及司馬中原《路客與刀客》便是那段時間讀的。
臺中一中時期,除了學校圖書館和省圖,詹宏志也常到美國新聞處借書,享受不限冊數且可借兩週的便利。除此之外,他最常去的便是中央書局。中央書局規模大,書種多,具有許多大專及學術用書。二樓角落更有一般書店難得見著的臺灣商務印書館復刻版書籍,尤其人人文庫系列叢書,對他有極大吸引力。詹宏志為通學生,放學後喜歡逛書局,汗牛書局折扣較多,中央書局的氣氛沉靜、人文氣息濃厚且對顧客友善,最適合閱讀。
詹宏志認為在那物資匱乏的年代,中央書局以寬容大方的進步態度,默默照顧一世代人。讓許多知識分子自然留連其中,以它為開闊眼界的生活中心。中央書局的歇業讓許多人覺得感傷,一直覺得虧欠它一份啟蒙之情。
日治、光復,戒嚴然後解嚴,世事不停演變,中央書局屹立街角,懵懂的腳步陸續經過,有人因此清楚了志向,智識文心獲得了滋養。
光圈再轉,光亮名字接著一個,文學志趣於此溫馨傳承。
這回走進中央書局的是誰?誰在書架前閱讀?哪雙渴望文學的眼神徘徊、黏著於書架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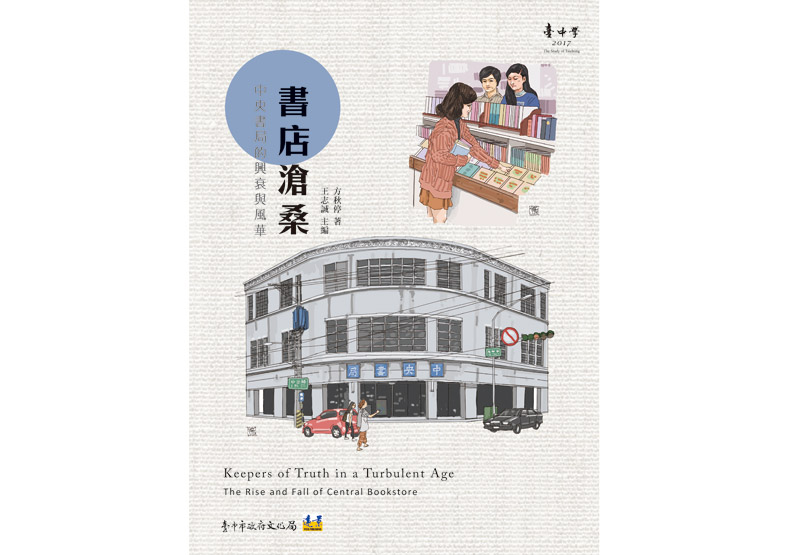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書店滄桑:中央書局的興衰與風華》一書,方秋停著,遠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