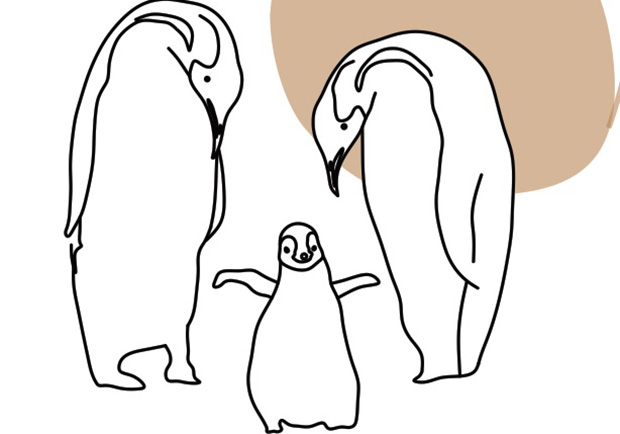(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助理教授/精神科專科醫師 陳嘉新)
我通常會跟不相熟的人這麼形容我的小家庭:「我們夫妻有三個小孩:一個四歲多的女生,然後是一男一女的雙胞胎,剛滿一歲。」從對方如何回應我這段陳述,可以推知他/她對於家庭的想像與理解。有些人的回應是:「好棒喔,一定很幸福吧!」有些人則會說:「真好,生小孩這件事情就一次解決了。」前者是浪漫化的情感投射,聚焦在生兒育女的美滿形象;後者則是意味深長的評論,顯然預設了生兒育女的最佳數量或者性別分布。不過也有些人直搗黃龍,問些實際的問題:
「那你全家出門陣仗好大,要換車嗎?」
(「您真有概念,我車子早換成七人座的,不然怎麼放得下三個安全座椅?」)
「你小孩要託給長輩照顧嗎?」
(「可是我們夫婦都沒有合適的長輩可以照顧小孩,這路行不通啊。」)
「喔,那你太太有要請育嬰假嗎?」
(「我們運氣好,剛好有保母願意帶雙胞胎,不過,你怎麼會提到我太太要請育嬰假這件事情?怎麼不問問我要不要請育嬰假?」)
這樣的對答還可以一直延伸,不過最後一個問題饒富趣味。如果繼續下去,我們還可以問:當小孩數目增加的時候,夫妻應該如何分配包含育兒在內的家事呢?畢竟,要不要請育嬰假以及誰應該請,都牽涉到如何分配有子女家庭的家務分工問題。
家務分工的性別意識形態
許多家庭都有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意識形態,這既區隔了男女不同的社會空間(家外/家內),也反映出個人對於工作與家庭責任間的區隔能有多大的支持。社會學家戴維斯(Shannon N. Davis)與格林斯坦(Theodore N. Greenstein)稱這樣的意識形態為「性別意識形態」。他們回顧社會學相關研究,歸納出以下幾個常用來測量性別意識形態的相關項目,包括:是否將經濟提供者角色視為優先、是否相信社會空間男女有異、職業婦女的家庭關係品質如何、妻職/母職與女性自我的關係、夫妻分工的家事效能,以及接受男性特權的程度如何。性別意識形態聽起來雖然抽象,但是這些測量項目卻跟家庭生活息息相關,包括了生育選擇、子女照護、家務分工、關係穩定度、關係品質、工作收入與教育等面向。(註一)
對於我們夫妻來說,在確定懷孕之後,最實際的問題便是:如何分配日後照顧小孩的工作?當時我雖已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卻還在醫院執業,有夜診也需要值班;而妻子在學術機構中的工作也相當沉重。要放下累積多年的研究所得,請育嬰假在家帶小孩,對我們兩個都有困難。所幸我後來剛好得到機會轉換工作,得以放下臨床醫療而發展社會研究的興趣。更棒的是,在妻子也不介意我的收入減少許多的情況下,我可以努力協調出比較平衡的工作與家庭生活。
社會的性別平權如何影響家務分工
這個經驗也讓我想到經濟基礎的重要性。就算我比較具有性別平權意識,但如果沒有雙薪收入的穩定基礎加上職業選擇的絕妙轉機,即便我想承擔多一些育兒與家事,也是不可能的事。同樣的,錢不夠,也就談不上換大車載全家出遊了。另外,假設我的妻子是家庭主婦,那麼我轉換工作的經濟衝擊就會比現在大,能夠調整家事分工比例的可能性也就較低。夫妻都具有性別平權意識與分擔意願固然很好,可是畢竟時間與體力都是有限的資源,夫妻雙方討論如何分配家務的同時,往往也得先撥撥算盤,確保如何才能維持家計穩定、衣食無虞。
社會學研究發現,家務分工除了受到性別意識形態的影響,最常舉出的另一套詮釋模型則是經濟資源模型,也就是以夫妻雙方的相對經濟收入來決定家務分工方式。這也是為何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會對家庭結構與分工產生深遠的影響。
不過,把我們夫婦的經驗拿來跟某些社會學研究對照,讓我有了另一個啟發。胡與賀茂兩位學者以中研院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進行統計,結果顯示:前述的平權態度或者經濟優勢並不太能解釋婦女家事工作的相對比率(該研究估計婦女負擔了約莫七成的家事勞動),關鍵在於婦女的職業地位。(註二)換句話說,家事與育兒分工不僅僅牽連到夫妻相對的經濟能力或者意識形態,某種程度也受到彼此職業位階的影響。我的妻子在上述研究的分類裡被歸類為「經理人或專業人士」,不論收入水平如何,這個身分本身就具有主張如何分配家務的正當性。如果再把職業選擇扣連到女性的教育水平提升與工作機會平等這些因素,那麼家務工作分配的議題還是跟家庭以外的社會議題有關,例如性別在教育與工作場域中機會是否平等。整體來說,要能夠扭轉不恰當的家事分工模式,除了組成家庭的成員要能夠開放地討論平等且貼切的分工模式,或許更結構性的關鍵還是在於性別平權的勞動場域與教育提供。
家務分工的實踐現場
脫離這些大尺度的描述,實際生活中的家務分配往往變動不居,缺乏定則,隨著不同時期的狀態與需求而逐漸演化。一般來說,運氣好些的家庭有長輩可以協助部分家務(但相對來說,同住的大家庭也意味著更多的家務量),而對於缺乏人力資源與經濟能力的家庭來說, 家務就只能分配給家庭內成員分擔了。以我們這種雙薪家庭來說,如果無法尋求其他家人的協助,勢必就要把部分親職外包,例如尋求日托的育兒服務。至於育兒以外的家事,就由我們夫婦拆分。拆分方式有時候是依照適性原則:我比較高,所以負責曬衣服;她比較擅長烹飪,所以大部分時間由她下廚。有時候則是依照工作性質來拆分,例如當老大還小的時候,我還在醫院上班,需要早起,所以會在出門之前負責餵飽小孩,然後帶去保母家。傍晚的時候,再看我們夫妻誰比較有空可以接她回家。另外,家務還會依照個人所學來分配,例如:因為我有醫療背景,我很自然便接手小孩生病時的求醫與照護;而因為妻子的學術工作取向,她就負責帶領小孩認識自然世界的奇妙。當然,有些親子活動是雙方都可以進行的,包括餵飯、換尿布、洗澡、讀繪本、做剪貼、講故事、出去玩。
去年雙胞胎降臨之後,家務與育兒的工作暴增,我們只好進一步外包更多家務。儘管如此,每天還是反覆重演薛西弗斯的神話:餵完小孩要換尿布、換完尿布了要洗澡、洗完澡了以後小孩又餓了。不甘心關愛被人分走的老大也不時發出抗議與哭泣。每天晚上我陪著老大入睡的時候,總感覺一整天好不容易推上山的石頭,明早醒來就要落回原位;而當我早上被兩個小小孩肚子餓的哭聲吵醒,揉著眼睛起床泡奶的時候,總是想到卡繆這麼描寫過薛西弗斯:「他勝過了他的命運。他比他的石頭更為堅強。」是啊,我要比那些奶瓶、尿布跟哭聲更為堅強。
當然,我這樣的描述或許過度聚焦在家庭生活的勞務強度與不免隨之而生的荒謬感受上,讓人容易把這些活動都想成了只是等待分配的工作,卻忽略了這些育兒與家務操持具有的正面情感回饋。前述家事分工的解釋模式雖然涵蓋了經濟資源、職業位階與意識形態,對於育兒部分的主觀情感因素卻較少著墨,然而這正是有子女家庭的家務勞動明顯異於一般勞動分工的地方:原本只會吃喝拉撒睡的小孩終究在你昏天暗地的忙碌之中學會爬了、學會走了、開始叫爸爸媽媽了。或者,在辛苦的家事結束,家裡地板又難得乾淨,髒衣服也都洗好曬好之後,能暫時享受到空氣裡面終於嗅到的一點秩序感⋯⋯這些無法計算、難以定形的小小愉悅,往往沒有列入家務勞動分配的解釋模型。也許它們終究是個人的虛妄意識,但或許也是這些主觀感受,支持著包含我在內的眾多家長,日復一日地執行親職,努力協商並操持著像薛西弗斯的石頭一般的家務。卡繆說的好:「掙扎著上山的努力已足以充實人們的心靈。人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註一:Davis, Shannon N. and Theodore N. Greenstein. 2009. "Gender Ideology: Components, Predictors, and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 87-105.
註二:Hu, Chiung-Yin and Yoshinori Kamo. 2007.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in Taiw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Studies 38(1): 105-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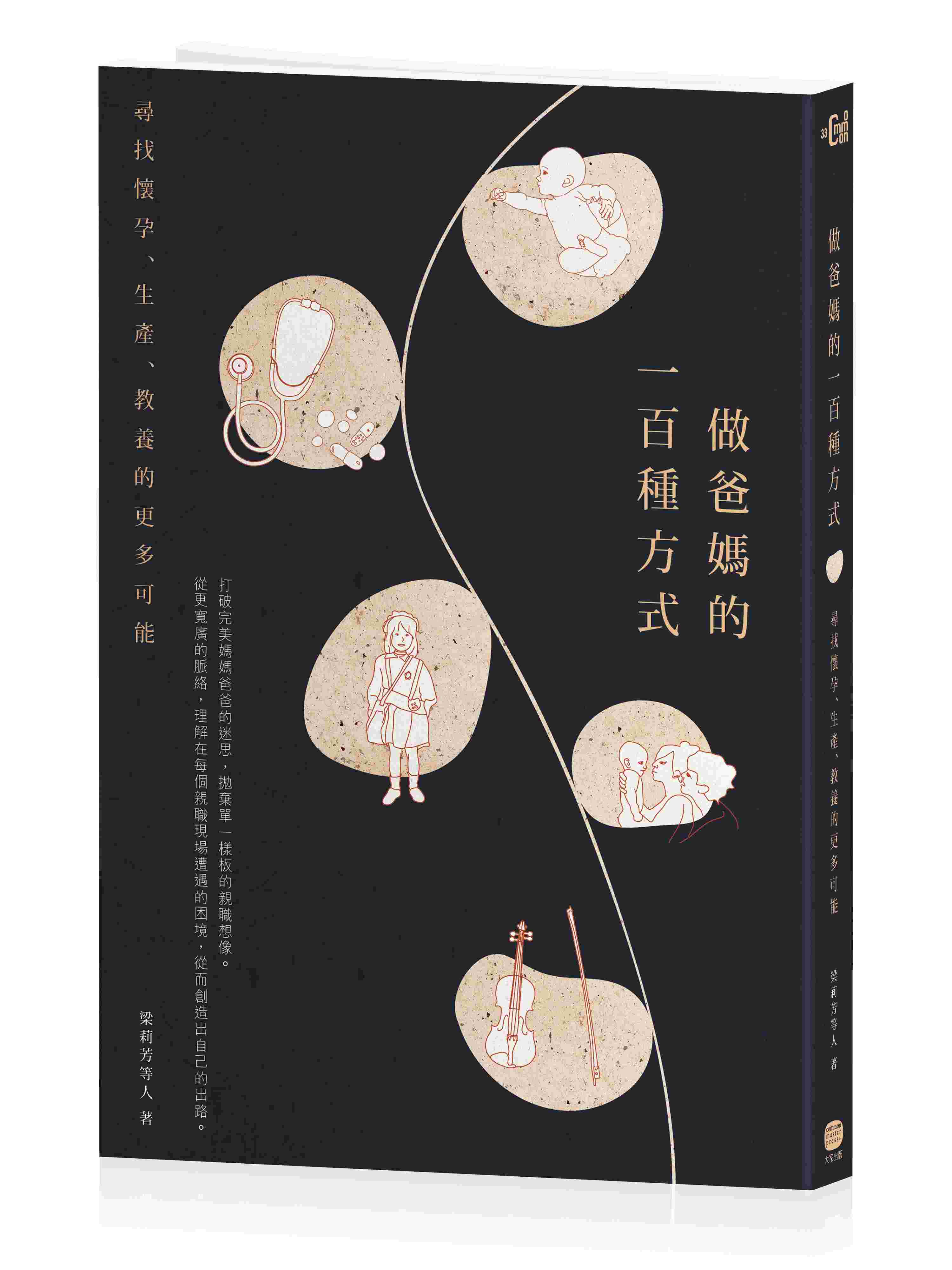
繪者:蔡芳琪
本文節錄自:《做爸媽的一百種方式:尋找懷孕、生產、教養的更多可能》一書,梁莉芳/等著,大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