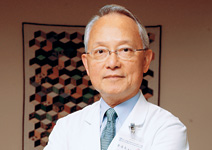那時,我不認識侯文詠醫師,卻很欣賞侯醫師的文章,尤其是他的洞察力與幽默感。做決定時,有點掙扎,最後還是拒絕了!因為該劇中所描繪的醫院文化與醫療行為,有不少是我一心想要去改變的。我擔心觀眾會將那些我不認同的醫院百態與我們醫院聯結在一起。
醫學教育是我長期投入的志業。所以,回國後,除了花很多時間參與醫學生、住院醫師、年輕主治醫師的臨床教學外,每年還固定回美國帶領杜克大學醫學院的臨床教育,所以,有機會經常對照兩地醫學生及住院醫師的表現。最令我憂心的是,20多年來,台灣醫學生、住院醫師與我交換心得時,大都談到醫師過勞及醫療糾紛問題,而比較少觸及如何把病人照顧得更好以及對未來職業生涯的想望。
在美國,儘管病人更在意醫療安全的問題,而且美國還充斥不少專門控告醫師的律師。但醫學生及住院醫師很少把醫療糾紛掛在心上。學習為病人解決問題,追求卓越是他們的目標。相形之下,台灣的醫學生及住院醫師對於他們的人生顯得消極、茫然。
他們的焦慮及疑惑,令我很是心痛。因而更加慶幸自己很早找到想要追隨的典範,而改變了我的生命。所以開始思考,如何讓這些年輕人也有和我一樣的生命轉折。
很幸運的,在1997年,嚴長壽總裁出了他第一本暢銷書《總裁獅子心》。他決定將該書部分的版稅捐出來做公益,再加上其他有心人士的捐助,讓我能夠每年送三至五位台灣醫學生到杜克醫學院與那兒的學生並肩學習,一方面是要讓他們去經驗兩邊醫療文化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深信教育環境和教師的態度決定教育的成果。所以,我想看看同樣優秀的學生,在不同環境,學習的動機、熱情和信念下會不會不一樣。試驗果然證實我的想法。讀者可以從《天下文化》出版的《杜克醫學院的八堂課》看到答案。
到美國才發現「原來醫教是這樣」
為這本書作序的侯文詠醫師說,他知道我回國後,一直在談醫學教育、醫療環境的改革。但是,直到看了這本書後,他才真正身歷其境地領會到原來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環境,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環境是這樣的樣貌。
難怪,有學生感歎「這樣的學習,只有『痛快』兩個字足以形容」,「我們已這麼習慣片段粗糙的教學或甚至沒有教學;習慣『學習得要靠自己努力』;不知道學生『學習』是理所當然的,而不是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的施捨,我真想為以前的自己哭泣,為國內多少和我一樣的學生流淚。」
侯醫師說,讀著學生的報告,幾度令他感動掩面,幾乎落淚。的確,20多年來,令我深深感到婉惜的是,我們的醫學教育體系,不但沒有激發國內醫療人才最大的潛能,反而讓不少人失去了理想,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