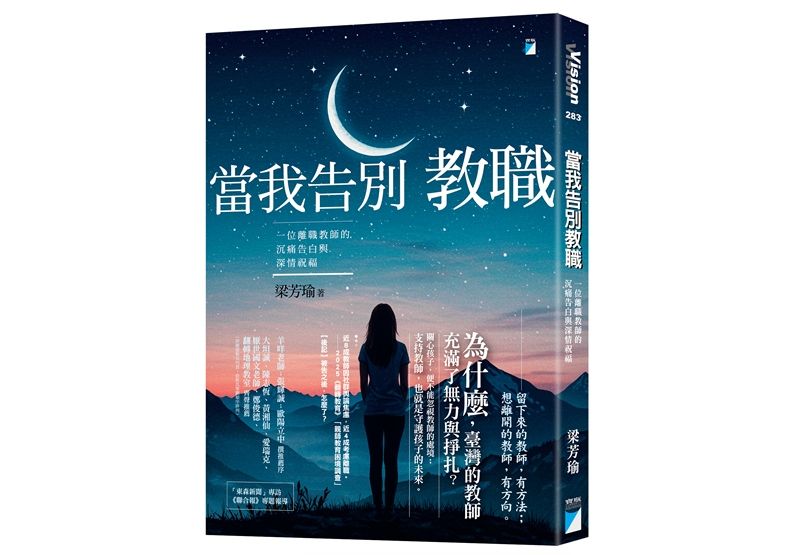她從小立志當老師, 且以榜首成績通過臺北市教師甄試,教學更是極受學生、家長及學校的信任與肯定,為什麼,12年後卻選擇離開?而且是毫無退路的裸辭?教師過勞、師道不尊、薪資脫節,這3大困境,成為梁芳瑜離開教職的主因。這本書渴盼臺灣的教師們被看見、被理解,能應對新時代的師生課題,也能好好照顧自己。(本文節錄自《當我告別教職》一書,作者:梁芳瑜,寶瓶文化出版,以下為摘文。)
校園的濫訴:為什麼親師天平漸漸失衡?
「運氣不會一直站在我這裡,好人也是會遇到壞事的。」我這樣想,是因為如今投訴教師太容易了,可謂「大投訴時代」的來臨。
由於少數的不適任教師惡名昭彰,又常被社群媒體推波助瀾,使社會氛圍中對教師的質疑與日俱增。
再加上進入少子化時代,每個孩子都是家長的心頭肉,一旦家長對教師稍不滿意,無論是管教或教學,一封黑函、一通1999、一篇公開貼文,就讓許多教師深受打擊,摧毀本該互相信任的關係,一步步造成親師對立。
愈認真的教師,被投訴得愈嚴重
這些投訴,不僅可匿名,還免責任、零成本。尤其令人心灰意冷的,大部分投訴的內容根本未上升到「不適任教師」的議題,而是該名教師不符合家長的個人期待,僅此而已,舉凡:作業出太少、進度教太快、穿著太前衛、沒提醒孩子吃藥、不選孩子當班長、夜間未即時回電……都有可能被投訴。
甚至,愈認真管教、愈費心教學的教師,往往被投訴得更嚴重。
王老師擔任七年級的導師,向來嚴謹、負責,期待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
班上有位學生常在課堂上嬉戲,而且每天遲到、遲交作業。王老師幾次提醒他要更加努力,養成好習慣,但效果有限。
某一天,王老師又在下課陪著學生補作業,一邊語重心長地提醒他,一邊拿出一封畢業學生的信,裡面寫道:「老師當初的嚴厲,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王老師想藉此啟發眼前的學生,卻只見他一臉不悅。
沒想到隔天,家長竟然到學校投訴王老師,認為他對孩子施加過大的壓力,全家人都因此徹夜難眠。
家長氣憤地說:「孩子哭了一整晚,說不想再上學了!學校教育應該讓人感到溫暖,不該讓孩子覺得害怕、麻煩。」
於是,校方請王老師務必調整教學的風格,以符合該家長的訴求。
王老師感到十分詫異且沉痛。
以往嚴謹、負責的帶班風格,深受學生和家長的信任,現在卻被認為是過失而遭受指責。
回到辦公室,王老師看著那封畢業生的信,陷入了沉思:「難道自己做錯了嗎?」再者,「究竟自己還能做些什麼? 」
學校的主力,從「辦學」變成「辦案」
校園裡,為了處理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投訴案件,「校事會議」(註)開不停,學校主力從辦學變成了辦案。
每一件投訴都要至少經過兩到四個月的調查。若結果無法令家長滿意,也可能再次收到投訴,所有的流程又要重跑一輪。
美其名說:建立夠多、公平、公正的案例,家長便會知道標準在哪裡而不再濫訴;然而,事實上,已經有多少行政人力、教師熱忱,折損在看不見盡頭的校事會議裡。
投訴的管道多元、快速、便利,開啟了大投訴時代。即使最後證明了教師的清白,家長卻不必承擔任何濫訴的成本,教師也得不到任何勞心費時的補償,何來的公平、公正?
想當然,親師之間本應保持的合作關係與天平,因此走向不可控的失衡。
2023年7月,超過3萬名的韓國中小學教師集結在首爾的光化門廣場。一名任教於明星學區的年輕教師,疑似因不堪家長霸凌的壓力而輕生。他們為此憤怒難平,想討回教師該有的保障與尊嚴。
據報導,近年來,韓國已至少有一百名教師以極端方式結束生命。其中最大的壓力來源,除了對於學生暴力的無可奈何,還有來自家長的惡意檢舉。
台、韓教育圈的環境或許不能一概而論,但是教師的處境卻十分雷同,尤其面對幾無門檻的濫訴,我們到底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繼續堅守教職、守護信念?
給留下來的教師:「自我照顧」的練習
給想離開的教師:「探索自我」的行動
無論哪一種選擇,都祝福教師們,更加靠近自己渴望成為的人。
祝福,每一位仍在現場的教師,自我照顧,保持初衷。
祝福,每一位選擇離開的教師,探索自我,海闊天空。
(延伸閱讀│別當朋友,當同學就好:年輕導師如何讓被全班討厭的孩子遠離霸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