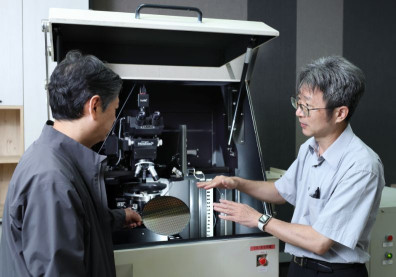薩泰爾娛樂《賀瓏夜夜秀》節目挨轟歧視身障者陳俊翰律師,引起社會大眾撻伐。人們總是堅信自己是善良公民,絕不會、也不想做出任何歧視行為。然而,歧視比想像中更普遍、常見。無論是帶有成見,或是對其他群體產生的敵意,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我不歧視」的可能性,實際上趨近於零。有沒有可能,我們其實只是「善良的歧視主義者」?(本文節錄自《善良的歧視主義者》一書,作者:金知慧,台灣東販出版,以下為摘文。)
第一次聽到「選擇障礙」這個詞時,我覺得相當有趣。聽起來就像是扼要地揭露了我「優柔寡斷」、「這樣做也不好、那樣做也不好」、「思考太多」的缺點。我在無數對話中,不斷使用含有自我貶低意義的話語;於是,這些話語終於闖下大禍。
那天,是舉辦關於「嫌惡詞彙」討論會的日子。由於有興趣的人太多,討論會還因此緊急轉換到更大的場地。以討論者身分一同出席的我,在討論會上使用了「選擇障礙」一詞。
那時的我,正好在陳述當人置身「這樣做也不好、那樣做也不好」的情況時,我們該如何做出決定的話題。討論會結束後,在前往用餐的公車上,與會者之一輕聲向我問道:
「您為什麼會使用『選擇障礙』這個詞呢?」
只是簡短的一句話,甚至也不是個問句,卻已一語道破我的錯誤。又或者更正確地來說,是指責了高談闊論著不要使用嫌惡詞彙的人,竟使用「選擇障礙」一事。
在那麼多身心障礙人士出席聆聽的場合,我居然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為什麼會使用「障礙」這個字。
即刻向對方承認自己錯誤的我,為此感到相當羞愧。然而,討論會已經結束,也早已失去向與會者們致歉的機會。該如何是好?
只是,有個奇怪的想法同時也在我的內心一隅萌生──「那句話怎麼了嗎?有什麼問題?」我開始啟動防禦機制,拚命否認那是個「問題」,並嘗試讓這件事變得雲淡風輕。
為了好好理解「選擇障礙」為什麼造成問題,我致電詢問投身身心障礙人士人權運動的相關人士。他向我解釋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有多常習慣使用含有「障礙」等貶低意味的用詞,並表示當任何東西被貼上「障礙」一詞,即意味著「不足」、「劣等」。在這樣的觀念中,「身心障礙人士」也因此被視作不足、劣等的存在。
我們其實都是「善良的歧視主義者」?
通話結束後,因而變得有些失神的我開始檢視自己。坦白說,我非常驚訝。「我居然存在歧視身心障礙人士的想法?」我不相信,不,是我不想相信。
上大學後,我第一個加入的社團是「手語社」。主修社會福祉學與法律的我,不僅鑽研人權議題,也修習關於身心障礙人士的權利與法律的課程。再加上,家人中也有身心障礙人士,所以向來自認很瞭解狀況的我,竟然存在歧視的想法?
同時,我開始理解了許多事。憶起當自己遭受歧視時,身邊的人卻全然沒有意識的經驗。舉例來說,關於以前在職場辦公室裡,有個像「名牌」的東西。
當時的我是約聘人員,辦公室的門上貼著一張以紫色紙護貝的膠膜名牌;而貼在正職人員門上的名牌,則是以硬木板搭配白字。
經過約兩年半後,我向那位同事提及兩者間的差異時,他才表示自己從未察覺名牌的不同。對他來說僅是看不見的「微小」差異,對我而言,卻是從上班到下班,開門進出的每一瞬間都猶如烙印著我身分的紅字。
仔細想想,所有歧視幾乎大同小異──受歧視的人確實存在,做出歧視的人卻視而不見。
歧視,是人們因為遭受歧視而有所損失的故事。幾乎不會有人靠著歧視得利,還挺身述說關於歧視的故事。
顯然是始於雙方立場不平衡的歧視,即使對所有人都不公平,但很奇怪的是,最終卻像只屬於受歧視者的事。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若以算術的方式思考,如果自己會有遇上受歧視的時候,即表示自己也有做出歧視的時候吧?
自此,我開始感到恐懼。原來歧視不再是與我無關的事。無論在教室、會議室、討論會場等任何地方,
我內化的歧視觀念隨時都有可能以某種型態的言語和行動突然出現。
於是,我決定開始研究。首先,我蒐集了各式各樣對少數群體的侮辱性字眼。這項基礎作業是為了藉由各種嫌惡詞彙,分析人們對少數群體存在何種形式的歧視觀念。
起初,我將注意力集中在網路四處可見的,近乎謾罵的言語。不過,隨著調查作業的進行,我才知道原來侮辱性字眼的範圍遠比想像來得寬,表達詞彙也可以極度隱晦。偶爾,甚至連說出口的人本身都沒有意識。
在以實際參與現場活動的社運人士與研究人員為對象蒐集侮辱性字眼的過程中,有兩句話吸引了我的目光。
「完全變成韓國人了。」
「請懷抱希望。」
這些被說是最具代表性的侮辱性詞句,前者是針對新住民,後者則是對身心障礙人士。我感到不知所措,因為這兩句乍看之下其實滿像是稱讚或鼓勵的話。就話者的立場而言,可能也真的是出於稱讚與鼓勵的意圖。

假如告訴說出這些話的當事者「這些詞彙可能對聽者來說是種侮辱」,他們會有什麼反應?假如他們以「我不是那個意思」反駁,又是否不再是個問題呢?既然只有受侮辱的人卻沒人做出侮辱行為,那麼受侮辱的一方是否就該忍氣吞聲或轉念呢?
這不是單純地不再提及某些詞彙就能被解決的問題。倘若不瞭解為什麼這些話語會變成侮辱,也僅是改用其他類似的話表達,或是不使用言語而改以視線與行動展現。
幸好,辨別這些詞彙為什麼成為「侮辱」的方法並不難。只要問問當事者就好,問問這些話聽在他們耳裡是什麼意思。
新住民表示,聽到「完全變成韓國人了」這句話時,會因為基於原本認為「不管在這裡生活多久,你也不可能完全成為韓國人」的前提,而變成一種侮辱。
此外,也歸咎出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或許不見得想要「變成」韓國人,為什麼非得要求他們接受「變成韓國人」是種稱讚。無論是不認為他們是韓國人,或是以韓國人為中心去思考,兩者都不是令人聽來愉悅的話。
至於對身心障礙人士說出「懷抱希望」,同樣也是因為前提而被視作一種侮辱。他們表示「懷抱希望」的前提,是基於對目前的人生沒有希望。
更根本的原因則是認為身心障礙人士的人生理所當然沒有希望一事;對他們來說之所以是侮辱,正是源於以自己的標準衡量他人人生價值的想法。
縱使身心障礙人士因社會條件而存在生活上的困難,對著他們說「懷抱希望」也很奇怪。因為身心障礙人士的問題層次不在於該不該懷抱希望,而是社會應該做出改變。
將我周遭的言語與想法一個、一個抽絲剝繭的作業,令人感覺彷彿是在重新學習這個世界。而我只是活在自己沒有歧視他人的錯覺與神話裡罷了。
直到連無意識都細細端詳後,似乎才可能稍微懂得真正平等地對待與尊重他人;意即發現了我不想承認的,羞恥的自己。
一直以來,似乎都活在世上的多數人皆與自己相同的錯覺與神話裡。看看那些以言行貶低與侮辱女性、身心障礙人士、性少數群體、新住民,卻又主張自己沒有歧視的人。
有些人對著性少數群體邊揮拳咆哮「因為愛,所以反對」,同時堅信這樣做才是愛的表現與正義。
無論怎麼說明「這種行為不僅是在否定另一群同為公民的存在,更是人格侮辱與暴力」,他們依然充耳不聞。
究竟該如何處理這兩條完全不見盡頭的平行線呢?兩者之間的距離,不會單憑時光流逝自然縮小;要求少數群體沉默的方式,不會終結這些情況。
既然結論是違反正義,當事人們當然不可能就此默默承受。只是,如果少數群體不停發聲,卻沒人願意聽的話,僵局也只會無止境延伸。那麼,我們到底能達成什麼「共識」呢?
本書即是始於如此既個人又社會的煩惱。其中還有希望的是,多數人都不想做出歧視的言行,只是看不見歧視的時候太多罷了。因此,到處都能遇見相信自己是善良公民,並且不會做出歧視的「善良的歧視主義者」。
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皆遵循著這項無法認知歧視的奇特現象而行。幸好,迄今已經有不少研究人員與學者持續提出豐富的研究與論點。追隨他們的研究成果,並將其投射自近來發生於韓國的事件後,開始與自己的想法做出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