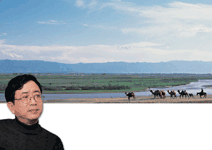從廢墟到廢墟
一
在甘肅的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這是自己文化考察的重要一站。
其實到甘肅之前,我去過的地方已經很多,但直到那裡,我才決定邊走邊寫。
甘肅的省會是蘭州,我在那裡來來去去也都以蘭州為據點。
開始接待我的是甘肅聯合大學。這所大學很奇特,本身沒多少教師,下狠心向全國請,儘量請各個專業最著名的,每請來一個,全校都聽他的課。結果,費用比養著一大批教師便宜得多,而排出來的授課者名單卻比任何一所國內名校都強。我的任務是連講半個月,天天陪著我的是忠厚樸實的范克峻先生,高大黝黑,戴副眼鏡,像一位鄉間秀才。
按照甘肅聯合大學的慣例,把我安排在金城飯店居住。這家飯店當時在蘭州算是「涉外飯店」,范克峻先生跨進去腳步都有點怯生生的。我因范先生的腳步,覺得自己不應該住在裡邊,便通過我們學院在甘肅話劇團工作的幾個畢業生,在他們劇團的一個小招待所裡住下了。
范克峻先生一看這個小招待所,堅決反對。因為那其實是小劇場後台對面的幾間陋房,廁所很遠,不供應伙食,隔壁講話都能聽到。但是我很滿意它的價錢,租一間,每天九角,還可打折成七角,多住一陣都無妨。
我住下後,經常要離開蘭州到甘肅的其他地方去。甘肅大,有些地方還挺遠,來去要好幾天,范克峻先生就會幫我把招待所的那間小房子暫時退掉,省下幾元錢。
那夜從劉家峽、炳靈寺回到蘭州,仍然住進那間小房子,發覺周圍有點熱鬧。一看,小劇場那天正在演一台以秦始皇兵馬俑為題材的舞劇,這兒是後台出口,整個院子全是黑衣武士,密密麻麻。天上有淡淡的月牙,院子裡有一盞昏暗的路燈,後台半開的木門裡映出一些斜光,這些黑衣武士都在隱隱約約間搖擺著、穿行著、舞動著,卻毫無聲響。我知道他們是在候場,但這情景一下子把我帶進了時間深處。
「余教授,您終於回來了!」聽到這聲音我回過頭來,看見隔壁房間的門開了,一位我不認識的先生在招呼我,他後面還站著兩位先生。經他自我介紹,才知道,他們是陝西省寶雞市話劇團的,他是導演,特地到蘭州來觀摩這台舞劇。他們和那台舞劇的導演、編劇、主要演員都聽說我住在這裡,一直等著我,想讓我對演出提出批評,可惜今天是最後一場了。當時,國內戲劇界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都還把我看作是他們的同行。
我對這位先生說:「戲已演了一半,再進去看就沒意思了。」他點頭,然後與我倚門聊了幾句。聊得投機,我就告訴他:「其實我的興趣已經轉移,不大看戲了。」
「轉移到哪裡?」他問。
「就這樣到邊遠地區考察文化,整體大文化。」我說。
「這會把您這位大教授累垮了。」他邊說邊瞭了一眼我小房間裡的簡薄鋪位。我剛才進門時把沾在鞋邊的大量泥沙跺在房裡的磚地上了,一眼看去十分骯髒。我的旅行袋很小,也全是泥漬,此刻正軟軟地癱在牆角。
「我這一生歷盡磨難,不怕苦。」我說。
「考察結果還寫書?」他問。
「可能吧。」我含糊地說。
「那我們是看不到了,看到了也看不懂。」他說。
「不會。」我回答得不清不爽。
他看我有點疲倦,讓我早點休息,我也就關門進屋了。
門邊有一個小窗,可以看到候場的古代武士還在月光下晃動。我看著他們,似被什麼吸住,一會兒覺得他們是虛幻的,一會兒又覺得自己是虛幻的。他們讓我站得很高,他們又讓我變得很小,我當然知道,這不是演員的力量。一樣的月光,一樣的地點,一樣的身高,一樣的容貌,不是在前台而是在後台讓我認祖,又讓我疏離。這是歷史的後台,我飄泊旅舍的窗口,卻讓我躲閃,讓我諦聽,讓我發呆。
二
這些天我已領略了太多的沙漠和廢墟,太多的寺廟和洞窟,都是一樣,讓我躲閃,讓我諦聽,讓我發呆。
我讀過很多解釋它們的規範文本,但一走到它們眼前就覺得全然不對。寫得並不錯,但沒有把最重要的東西寫出來。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好像只能感覺,無法概括。一經概括,感受立即受損,而且往往損及靈魂。
憑我對接受美學的研究,我知道,可靠的出路在於使自己感覺與眾多他人建立起一個「反饋流程」。今天的「眾多他人」是一個經歷巨大災難後重新甦醒的民族,我的父母之邦。災難使我們感到巨大的屈辱,災難結束後的開放使我們獲得了對比座標,更加沈重。
因此,我覺得,應該在考察途中說點什麼,與同胞們建立起一個「反饋流程」。
小房間的床頭有一張破舊的小桌子,我彎腰從牆角的旅行袋裡取出幾張稿紙,放在桌上,拿起鋼筆。用左手支頭想了一會兒,然後在稿紙上面端正地寫了四個字:文化苦旅。
歷來我的許多興奮,由筆尖而生。寫下這四個字後,好像挖開了一道小渠,一系列構思就源源不斷地湧出來了。我在稿紙上勾勾畫畫,定下一條條寫作方針。當我瞌睡上床,已聽到雞鳴。
第二天近午醒來一看,幾張稿紙上塗畫得亂七八糟,最後勾畫出來的其實只剩下十六個字,那就是:
遠祖廢墟,
當代愁慮;
一己筆觸,
世間話語。
這十六字,兩個對子,背後包含的內容不少,多數帶有挑戰性質,因此記憶深刻。我故意讓它們與「文化苦旅」同韻,便於記憶,其實它們後來一直指導著整本書的寫作,因此不會忘記。
我需要把兩個對子背後的挑戰性內容交代一下。
關於「遠祖廢墟」和「當代愁慮」——
把考察和寫作的重點放在古代遺跡上,包含著兩種選擇,一是古代,二是實地。
文革之後的文化焦點,主要在二十世紀的是非得失間徘徊。
對此我一直抱有歧見。我覺得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是非,很難梳理得清。在兵荒馬亂之中,雖然也出過一些傑出人物,但文化整體已進入衰敗化、應時化、實用化、政治化、極端化、瑣碎化的過程。我在撰寫作學術史論的時候,很少談論二十世紀,就是這個道理。自從開始投入大規模的實地考察,我更明白了,我們需要復興的中華文明,應該以偉大的唐代為中樞,前後輻射。甚至再往前推,推到絢麗而混亂的魏晉,推到氣魄雄渾的秦漢,推到哲思滔滔的戰國。
這不是向古代遁逸,而是對中華民族的再次崛起給予了更高的歷史期許。我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絕不是回到文革之前,也不是回到國民黨統治時期,更不是回到晚清時期,而應該尋找這個民族曾經有過的最高文化座標。只有這種最高文化座標,才是世界性的座標。
因此,我應該在這歷史轉型的關鍵時刻,帶著當代愁慮,尋找古代。
當時我心中想到的典範,是十八世紀德國啟蒙運動中寫《古代藝術史》的溫克爾曼、寫《拉奧孔》的萊辛這些人。他們沈醉古希臘,細細摩挲,從中伸發出震動整個歐洲的現代闡釋,直接呼喚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爾、貝多芬。在他們之前,德國是如此落後,在他們之後,德國文明光耀百世。而他們所做的,就是為了現代而尋找古代。
我必須尋找曾經發生過偉大歷史事件的文化現場。根據當代中國讀者的接受心理,我可能會運用更多的文學方式,先讓廢墟提醒自己,再讓我提醒更多的同胞:我們的土地上還保留著曾經偉大的證據。直到今天,我們還與這些偉大的證據相鄰而居。
不僅是曾經偉大的證據,而且還是失去偉大的證據。
這種感覺,即便是悲愴,也是宏偉的。帶著這種感覺徘徊在廢墟間,耳目特別敏銳,聯想特別豐富,最能確證作為一個從災難中跳出不久的中國文化人的身分。因此,表面上還是蹲在廢墟間,實際上已經更多地在問自己:我是誰?何以生長在這些廢墟之間?
我知道,這已經有了寫作的契機。
關於「一己筆觸」和「世間話語」——
文學寫作的基座是個體生命。
沒有個體的集體,是一種紙紮的龐大、空洞的合唱、虛假的一致,這是我們在文革時期天天忍無可忍的精神磨難,但在文革結束這麼多年後,還在延續。
我讀過國際間很多以個人話語闡釋大時間和大空間的傑作,但在我們中國,幾十年來培養成的很多「評論家」只會用集體話語來批判個人話語,而他們心目中的集體話語,又不知形成於何時,來自於何方。預計我的文章發表後遲早會遭到他們的批判,那麼,我乾脆把個人話語呈現得更加透徹,不僅語言風格是個人的,而且連選擇標準、觀察視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歸向於一己僅有。為了讓普通讀者明白這條寫作路途,我還會故意把個人對家鄉生活的回憶文章穿插其間。我心中的中國,如同茅舍船楫的家鄉;漫長的文明歷史,如同童年無鞋的腳印。一切由我個人體驗和吞吐,一切皆是五尺之軀的偶撞、偶遇、偶感、偶思,絕不接受任何異己的指摘。
用個人話語、一己筆觸表述大時間和大空間,我已在一系列學術著作中做過嘗試,但要用文學化的方式做得更加充分,必須通過更大膽的實驗。在這方面,支撐我的理論力量是利奧塔德關於「輝煌敘事」(Grand narratives)的論述。利奧塔德認為,現代使「自我」在文學中更加合法化了,但有兩種呈現方法,一種是把自我放置到一個具體模式中獲得解釋,可稱之為「細瑣敘事」(Little narratives),另一種就是把自我放置到一系列重大基元性課題中獲得意義,那就是輝煌敘事了,自我已成了宏大背景中的一個角色。
宏大中的自我也就是一種世間存在,只有世間才是我最宏大的背景。因此,我的這次寫作,有可能隨著自己的腳步,走出沙龍呢噥、酒吧喧囂、茶館清淡,走出一圈圈以各種名義築造起來的圍牆,走向平民天地、尋常巷陌。
我要以超過學古文、學外文、學奧義、學僻論的艱辛,學會世間話語。
三
范克峻先生聽了這個寫作方針,還沒有完全弄明白,就已經表示全力支援。這位斯文的老漢用渾厚的甘肅口音說:「我就知道,中國的雄魂在古代;我就知道,文章的極致是尋常。」我笑了。
「要不要把我家的一個破檯燈拿來?」他問。
「桌子小,放了檯燈就放不下紙了,有頂上的日光燈就行。」我說。
「要不要稿紙?可惜我們這裡的稿紙太薄。」他說。
「稿紙要。薄一點帶著輕,寄也方便。」我說。
於是我就開始了。
我無法事先向范先生誇口的是,我要在這間小屋裡開始的,是一個足以貫串我後半輩子的系統工程。我的文章表面上會是散落的短篇,否則很難進入尋常巷陌,但這些散落的短篇有一種內在的脈絡綰接,因此也可以看作一個長篇的自由章節。
它必須由一個鑰匙孔來開啟,打開中華文明的一系列重要話題。
只要找到這個鑰匙孔,也就找到了足以提挈今後萬千話語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正是在甘肅,這個鑰匙孔找到了。
是敦煌,是敦煌的莫高窟,是莫高窟裡的那個藏經洞。
為什麼?因為這個藏經洞藏下了中華文明最輝煌的年月,又被發現於中華民族最悲哀的時刻。它發現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個晚春季節,與八國聯軍發起向中國的攻擊幾乎同時。焚燒圓明園的烈焰即將騰起,遠遠地照見沙漠深處的這個洞窟,正悲嘆似地洩漏出唐五代和北宋的傲世餘光。
千年榮辱集中於一個洞窟,我去時,洞窟早已蕩然無物,只成了我的鑰匙孔。
那麼,嘎、嘎、嘎,《文化苦旅》的入口打開了。
先寫藏經洞,再寫整個莫高窟,再走開去一點,從陽關寫整個唐代。才寫三篇,我就感受到了一種把自己介入歷史、同時又把自己和歷史一起介入地理的痛快。
歷史縱然沈重,腳下縱然崎嶇,但我的步履應該輕快。因為只有輕快,才有廣闊;只有廣闊,才有浩歎。
因此,我既沈重又輕快地離開了甘肅,去尋找別地的廢墟和故跡。我覺得應該以一個不大的篇幅,勾畫出一個比較完整的中國文化的概念,而且是一個當代書生心中的中國文化概念。我所說的書生概念很泛,既不是江南才子、淮陽遺老,又不是燕京名士、川湘怪傑,但又可以包括他們。這一來,就要把圈子繞大。
下筆後最大的苦惱,是怎麼也擺脫不了學術習氣,這幾乎成了我的初寫散文的首要障礙。
例如,我早就明白,好的文學作品是一個充滿質感的感覺系統,因此必須避免邏輯結論。但是已經寫了那麼多年學術論著,腦子養成了邏輯整理的習慣,就像一個資深的清潔工人到別人家裡去做客,一進門就不由自主地整理起來,忘了在這裡自己並不具備整理的權利。
我一寫就明白,在散文寫作中,邏輯結論就像鐵柵欄,把感性世界的無限春色都關在外邊了。我既然從學術跳到了文學,就必須從頭來起。不僅要躲避結論,而且特別要尋找不可能得出結論的人文難題。
開首那篇「道士塔」,寫到敦煌藏經洞裡的文物被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險家運走,本有兩種相反的結論可供選擇:一是斯坦因他們盜竊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藏,應予嚴厲批斥;二是當時兵荒馬亂的中國無法保存這些文物,不如讓他們作為人類文化遺產,收藏在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館裡。這兩種結論中不管選哪一種,都能寫成痛快淋漓的文章,而且我也已經讀到過很多。但我的內心卻很矛盾,不知運送這些文物的車隊應該駛向何方。我設想,如果我早生一百年,會到沙漠裡去攔住斯坦因他們的車隊,與他們辯論,萬一他們辯不過我,又比較講理,把車隊留下了,我該怎麼辦呢?
這裡也難,那裡也難,我只能讓它停駐在沙漠裡,然後大哭一場。
想到這裡,我知道,文學出現了。出現在真實的兩難間,出現在孤獨的無奈裡,出現在質感的荒涼中。
於是,這也就成了我打開文學實踐之門的鑰匙孔。
多年後,我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
我有一個分工,把已經找到了結論的問題交給課堂,把能夠找到結論的問題交給學術,把無法找到結論的問題交給散文。
無法找到結論還寫,這不是太不負責了嗎?不,正好相反。世上有一些問題永遠找不到結論卻永遠盤旋於人們心間、牽動著歷代人們的感情。祖先找過,我們再找,後代還要繼續找下去,這就成了貫通古今的大問題。文學藝術的永恆魅力,也正是出現在這種永恆的感受和尋找中。
學術習氣對於文學寫作的損害,還有更具體的方面。例如,學術語言追求全面、完整、周密,而文學語言卻並不拒絕片面、殘缺、偏執。中國古詩中特別動人的句子,總是誇張醒目、癡拗驚人的。一旦用全面、完整、周密的筆觸一改,立即詩味全無。這個道理,我作為一個欣賞者、研究者和詮釋者都懂,但作為一個實際寫作者,就必須面臨一次次自我釋放。
甚至,在一件小事上我還絆了很久。我的散文寫作經常涉及各種典故,而很多典故往往存在五、六種不同的說法,七、八種有趣的考證。按照我的學術習氣,多麼希望在文章中一一羅列出這些說法和考證,然後說明我為什麼要選擇某一種,至少,讓我在注釋中發揮一下也好。但是,散文寫作不允許這樣做,因為這會使文氣受阻。即使躲在注釋中發揮,也會成為一種「後門口的炫耀」,令人發笑。
這一些,我都挺過來了。哪怕處處與學術有關,我也必須讓它們經過感覺系統的嚴格過濾,淬鍊成純粹的散文部件。開了這個頭,就愈寫愈順。因此,後來聽到有些批評,心中反而沾沾有喜,覺得自己的散文確實把那個「以學術代文學」的奇怪天地攪亂了,而這正是我所樂見的。
我不作任何辯白。沒有人為自己的散文作學術辯白的。這就像,我到茶館去喝茶,有人把茶鹼的化學分子式寫在牆壁上要與我討論,我只能端起茶杯輕輕搖頭:這是茶館,我在喝茶。
由於洗去了學術習氣,廣大讀者直接感受到了我誠懇的內心,隨之,也認同了我對中華文明的恭敬和憂傷。
四
蘭州那家小招待所往北走,有一條東西向的街,西邊有一個郵箱。我從這裡把《文化苦旅》的最初幾篇稿件,寄給《收穫》雜誌編輯部的李小林。
以後,走一路,寫一路,寄一路。沿途荒昧,看不到《收穫》雜誌,不知道這些文章發表後有什麼反應。
後來《文化苦旅》出版成書,既沒有開新聞發布會,也沒有開作品研討會,甚至,報刊上連一行字的消息都沒有刊登過,但很快出現了發行奇蹟,一版版地重印,沒完沒了。
我還是在外地考察,對發行情況並不清楚。也沒有與出版社簽過出版合同,出版社支付的是一千字幾元的一次性稿費,大約一共4000元錢吧,很快就在考察途中花完了。只是有幾次,在黑龍江邊境的黑河,在新疆邊境的喀什,在廣西邊境的憑祥,都發現了大批《文化苦旅》的讀者,我才知道這本書真是賣得很多了。
那些年從中國大陸向外國郵寄印刷品還要受到檢查,據報導,九十年代前期國內家長向海外留學子女寄得最多的書籍也是這一本。這讓我感動了好幾天。
最有趣的是,一位批判者撰文說,警方查檢煙花女子,居然從她們的提包中發現了《文化苦旅》。批判者想借此來證明這本書的低級和下流,而我卻暗自高興,並恍然大悟。原來有些文化人是害怕不乾淨的手來翻動他們的書,才印得那麼少的。我恰恰相反,只想躲避那個突然冒出來的「上流社會」,而不拒絕自己的書散落於尋常巷陌、淺樓窄門。
豈止是煙花女子。有一次,上海市提籃橋監獄的監獄長麥林華先生找到我,說很多犯人是我的讀者,因獄中無事,讀得特別專注。他們多次向監獄管理人員提出要求,希望我到監獄作一個報告,與他們見一個面。我去了,聽報告的犯人多達五千,中心會場坐不下,多數就在監房裡看閉路電視。我知道,犯人未必是壞人,壞人未必進監獄。因此,報告一開始就真誠地呼喊一聲「我親愛的讀者朋友們」,坐在中心會場的很多犯人擦起了眼淚。對我來說,讀者就是朋友,不管他在哪裡。
真正的高雅群體也沒有拒絕《文化苦旅》。
在一個山道間初見詩人余光中先生時他並不知道我是誰,下山後託一個朋友送這本書給他,他當夜就寫來一封信說:「只讀了三篇,就可以斷定,這是第一流的散文。」後來,他又在多個國際學術研討會和其他重要場合高度評價《文化苦旅》。
白先勇先生讀了這本書後,立即動員爾雅出版社的社長隱地先生,趕緊爭取這本書的台灣版權。隱地先生本人也是詩人,溫良忠厚,嗜書如命,與他的夫人林女士一起,以極大的熱忱投入了這本書的出版和闡釋事務。當時的台灣出版社對全球華文閱讀群落的影響,遠遠超過大陸出版社,更何況爾雅早已信譽卓著。很快,按照隱地先生自己的說法,這本書在台灣已經「家喻戶曉」。這可能有點誇張,但後來我每次去台灣,從海關、安檢,到旅館、售票處,工作人員看到我的通行證總會像老朋友似地招呼一聲:「哦,是您啊!」
有的則不動聲色地問一句:「還在苦旅?」
有的順口遞過來一個建議:「下一本該寫台灣了。」
我喜歡台灣的整體文化氣氛。在台灣幾乎見不到那種只知不斷誹謗他人,卻不讓人知道自己做過什麼學問、寫過什麼作品、從事什麼專業的所謂「文化人」,這讓我又驚又喜。民間的文明程度更為可喜,那次在台北看法國的奧塞美術展,提了一個印有展覽圖像的口袋出來,不管是搭計程車,還是到醫院看病,司機、護士一見那個口袋都會聊幾句歐洲現代派藝術,而且都不太外行。據一本書的書名顯示,讀我的書也一度成了那裡的一種時尚,那本書的書名是《到綠光咖啡屋,聽巴哈,讀余秋雨》。台灣讀者接受我,更有另一番意義,因為我所寫的一切曾經受過太多非文化的政治阻隔。
但是,後來幾次去台灣,卻讓我有點傷感。文化氣氛被愈來愈強烈的政治對峙所沖淡,很多傑出的文化人不是政治化了,就是找不見了。這就是說,文化還在,卻已不成為公眾共用的強大結構。其實,政治爭逐再響亮也是一時的、局部的,如果沒有全民文化素養的制衡,什麼壞事都會發生。中國大陸的「文革」之所以能夠發生,除了政治因素之外,還因為早已經把很多最基本的文化「革」掉了,還嫌不夠,再「革」一次,結果只能社會失控,一片混亂。台灣萬不能把自己好不容易在災難歲月保存下來的最值得珍惜的東西丟棄了。當然,這只不過是一個旅行者的粗淺感想。
《文化苦旅》跨地域的持續暢銷給了我一種信心,決定把已經開始的考察和寫作的實驗繼續向前推進,甚至推到邊緣狀態。
一般說來,一旦擁有了大量讀者,就很容易產生一種擔心,怕任何新的嘗試會使老讀者不習慣,結果走向了保守和停滯。我的內心正好相反,把擁有讀者當作了非前進不可的責任。這就像在一個龐大的集會中我說了一番話全場安靜,大家都以期待的眼光看著我,我是順著剛才受歡迎的語勢說下去,還是趁機更換一個更重要的話題?我選擇了後者。
我知道,生在現今,世情紛雜,人事煩忙,要讓世界各華人社區裡的讀書人,特別是海峽兩邊的讀書人,都比較願意讀某個人的書,這種情形不多了。我既然碰巧成了這個人,那麼,也就承擔了一種話語使命。
中華文化本來就具有比舞龍舞獅、唐裝茶餐更厚重的分量,因此很需要有人來講述。但是,對於那些特別深奧、尖銳的部分,也能進行社會性講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