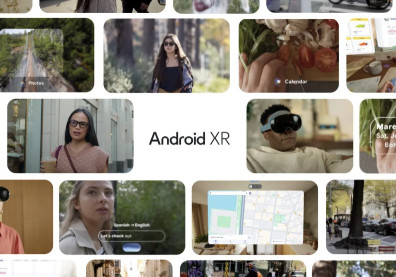編按: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及高社交程度是讓丹麥成為世界上最快樂國度的原因之一。丹麥人經常面對面互動,凡事分攤共享、不講究正式、步調不匆促。品嘗甜食時拋掉罪惡感,享受吃下的每一口甜蜜滋味,不錯過眼前的美好。簡單說,寵愛自己,與親友家人共度美好時光,珍惜每刻當下,正是HYGGE精神的根本。
沒有人是孤島
孤獨(loneliness)對人體有害,2006年加州大學針對3000名患有乳癌的女性進行研究,發現相較於社交連結較少的患者,朋友圈較寬廣的患者生存率多達四倍。一年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團隊發現,調節癌症免疫反應與腫瘤成長速度的基因,會因為社交互動的多少而觸發或靜止㉗。
以上都是具有突破性的大發現,而現在我們只需要觸控螢幕就能在社交圈新增好友,這應該表示不再有人會感到孤獨,因此人人都無比健康的時代已經降臨。然而,並非如此。事實上,孤獨人口的比例正在上升,根據2013年「終結孤獨行動」(Campaign to End Loneliness)的調查統計,單是英國就有約80萬人長期處於孤獨狀態的人口,而在2014年,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發現,全歐洲之中,英國人和德國人與鄰居最不親近㉙。
美國的狀況也不怎麼樂觀,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4年的普查,正處於孤獨狀態的美國人「前所未見的多」。這些調查結果顯示出面對面交流的重要性,500名永遠不會見面的臉書好友,無助於減緩社會疏離感。而現代人只要獨自坐在舒適的扶手椅上幾乎就能完成所有該做的事,更是讓人際疏離的狀況日益嚴重。我們越來越少在推著購物車逛超級市場時遇見鄰居,而是用虛擬購物車裝滿商品,唯一的互動對象則是送貨員;越來越少和同事面對面討論,而是透過電子郵件聯絡;也越來越少在影城和其他觀眾一起看電影,而是在私人領域觀賞串流影片。以上種種改變固然便利,卻也阻絕了社交互動的機會,更潛藏危害生理與心理健康的危機。
在《衛報》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發展心理學家及作家蘇珊.品克(Susan Pinker)寫道:「就像我們需要食物、水分和睡眠才能生存一樣,真誠的人際互動也是生存的必備條件。社交頻繁而有凝聚力的社會,例如被譽為『藍色慢活區』(Blue Zone)的義大利薩丁尼亞島(Sardinia),居民之所以能擁有長壽、健康且快樂的人生,正是因為他們利用行動裝置輔助面對面互動,而不是以前者取代後者。」
丹麥人與其他相當國家的國民相比,並沒有比較長壽或比較健康。但如果各種全球幸福指數是值得參考的數據,丹麥絕對是屬於比較快樂的國家,而原因之一應該就是高度的社會凝聚力。
相關的統計數字如下:2010年,78%的丹麥人每週至少會與好友、家人及同事一起進行社交活動,高於全歐洲平均的60%;95%的丹麥人表示自己擁有在困難時可以依靠的親友,比全歐洲的平均數字高出7%。在我看來,以上兩件事明顯有相關性:丹麥人能夠擁有穩固的社會連結,是因為他們願意花時間定期與人直接互動。
社會的連結是幸福的關鍵之一
我的工作室位在家中花園的一角,外頭的人行道比小屋低了幾英呎,所以即使有人經過,我也不會看見。此外,每週我大約有一半的時間是處於獨居狀態,因為小兒子去找爸爸了,再加上他不久後就要上大學,這間平房裡很快就會只剩我一人。正因如此,有時候我在生活中完全不會見到其他人。但這沒什麼好介意的,畢竟我喜歡獨處,也會定期和朋友圈及男友見面。我和母親及兄弟夫妻很親近,這些都是我在艱困時刻可以也曾經依靠的人。所以儘管我經常孤單一人,我並不覺得孤獨。
我比較不擅長的是經營與同事和鄰居這類點頭之交的關係,除了短暫在辦公室當過臨時工之外,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在家工作,從來沒有養成圍在飲水機旁邊閒聊的習慣。而儘管我住在村莊裡,卻沒有融入這裡的生活型態:我不在社區的小店裡買東西、不參加慶典,也從不參加在教堂大廳舉辦的電影之夜。兒子還小時,放學時間,我總會徘徊在小學遊樂場的邊緣。
還有,雖然我是網球社社員,卻從來沒有參加過社團活動。一部分原因是,我天生不善社交;另一部分原因則是,這些年來搬過兩次家的後遺症。
離開第一任丈夫,並遇見第二位成為我前夫的男人之後,我全面退出原本就所剩無幾的村莊生活。因為我不喜歡讓只在商店見過幾次面或是只因為小孩一起玩耍而認識的人,得知我私人生活混亂的一面。總之,我的計畫是在小孩畢業後立刻搬家。承租小屋期間,對我來說是與孩子共度珍貴且親密的時光,接著,我開始把注意力放在新丈夫位於倫敦和多塞特郡的住家,試圖培養出歸屬感。
第二段婚姻仍以失敗收場,因此我必須離開前夫的住家,斷絕先前經營的人際關係,並且徹底搬回格洛斯特郡,感覺像是全部重新開始一樣。新平房位於之前承租小屋的同一個村莊,但坐落在另一側。
比起我和第一任丈夫買下的屋子,新房子位在山丘的更高處,等於是全新領域。我也懶得和鄰居解釋,其實自己從2003年就已經住在村裡。我猜想如果他們知道我已經在這裡住了十年,應該會因為我只認識一小群人而感到奇怪。
我也對自己的人際網如此狹窄感到疑惑,卻沒有想要改變現狀,直到我開始了HYGGE實驗。
我在研究過程中接觸到哥本哈根的幸福研究學會及其在2014年發表的報告《快樂丹麥人》(The Happy Danes),其中探討了丹麥能長期維持高幸福指數的原因。而以「公民社會」為題的章節,開頭如下:
「許多研究幸福的學者都同意,社會關係是人感到幸福的關鍵⋯⋯良好的鄰里關係、參加足球比賽,或是參加集郵社,都有助於增進幸福感。」
過去三十五年來,我堅決不參加任何形式的社團,這種反感情緒應該是源自曾經短暫加入女童軍的經驗,而且當年純粹只是為了能參與每年一度的露營活動。當時我其實是想模仿《燕子與鸚鵡》的角色南西(Nancy),對於生活在帳篷裡抱有浪漫的幻想。
露營的前幾個月並不歡樂:女孩子心機招數盡出,會議冗長又無聊,千辛萬苦只為了獲得募款徽章。最後終於到了活動當天,我因為感染德國麻疹只能立刻回家。我掛起海軍藍色的尼龍裙和(沒有徽章的)聚酯纖維襯衫,從此拒絕參加任何團體活動—直到《快樂丹麥人》這份報告迫使我重新評估一切。
報告中並沒有特別提到HYGGE,但讀到「丹麥社會凝聚力特別高的原因」這章時,我發現丹麥人熱衷於和親友及鄰居一起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這也和HYGGE文化的盛行有關,於是我決定加入當地的慢跑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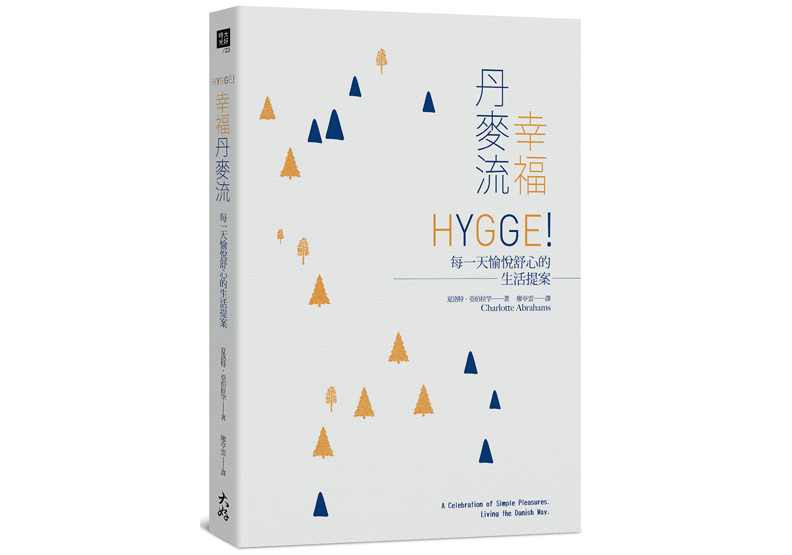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幸福丹麥流: HYGGE!每一天愉悅舒心的生活提案》一書,夏洛特.亞伯拉罕(Charlotte Abrahams)著,大好書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