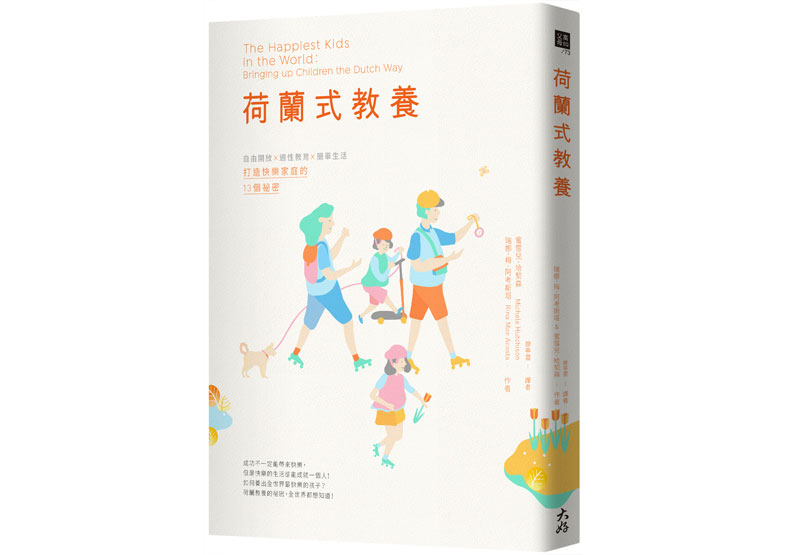不崇尚競爭的荷蘭小學教育很有趣,沒有所謂「班上第一名」的目標可以追求,中學教育也是相同的道理。只要進入特定的類組就讀,平均分數只需要保持在滿分10分的6分──也就是及格分數,就能繼續接受這個程度的教育。(本文節錄自《荷蘭式教養》一書,瑞娜·梅·阿考斯塔著,大好書屋出版。)
在此,我必須清楚說明,荷蘭的成績系統和英美不一樣,並非根據百分比計算。
在荷蘭,錯誤就扣分,而滿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大多數的學生,分數都會落在六到七分,而這樣的分數就足以取得畢業證書。
以高中畢業來說,平均分數為六.四,僅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學生能夠取得平均八分的成績──這已經算是非常高的分數。
在學術類組(VWO),如果學生能夠以及格的成績畢業,表示他們的程度足以在大學取得一席之地,絕對不會有在英美氾濫的「成績灌水」問題。正因如此,學生不會為了擠進大學追求最高分,競爭狀況也不至於惡化,似乎是相當公平而且可避免精英主義的教育體系。
文化歷史學家何爾曼.普萊(Herman Pleij)近期發表了有關荷蘭認同的研究「絕對有可能」(Moet Kunne),其中詳細說明了荷蘭的教育政策。
他指出,荷蘭教育政策聚焦在最大範圍具備中等能力的一群,而不是成就最高的一群:透過把中心目標設定在「讓最多學童與學生拿到文憑」,也就是將所謂「中庸之道」概念貫徹到各個層級的教育系統。因此,及格成績就夠好了,而如果想要表現得更好,完全是個人選擇。
(延伸閱讀│瑞典文化:「沒人需要成為鑽石。」就算沒發光發熱,社會仍接納你)
亞里斯多德的「中庸之道」(golden mean)指的是平衡的中間點,可以避免兩個極端的缺失,這是荷蘭思維裡很重要的中心概念。前文提到的常見用語「不必大驚小怪,眼前的情況已經夠瘋狂了」(Doe maar gewoon dan doe je al gek genoeg),也是相同的道理。
儘管學校裡沒有強烈的競爭氛圍,荷蘭人還是在注重想法、有創意以及具備創業精神的事業表現傑出:看看那些知名的荷蘭藝術家、設計師和建築師,更不用說有二十一名諾貝爾得主來自荷蘭。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維基百科上的荷蘭發明列表(包括DVD、CD、藍芽和Wi-Fi)。
然而,現在的荷蘭教育制度卻也面臨一些內部批評聲浪:荷蘭國內有一波新勢力主張:讓強者更強。普萊則公開反對這種做法,他認為「適中」及「平均」是荷蘭體制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這能囊括和保障最多數的學生。如果改成重點培育表現最佳的極少數人,將會降低人民整體創新能力以及整個國家的發展與健康。
目前荷蘭學校制度的優點,在於積極延長孩子的學習之路,而不是讓他們為搶奪第一名而相對削減了學習的機會。
我決定和認識最久的荷蘭好友艾文以及她母親,談一談學校的事。艾文和我年齡相近,她的大兒子和我兒子在托兒所變成最好的朋友之後,我們也變得熟識。艾文是個身形勻稱的金髮女性,先生是前奧運選手──和她同樣高大且一頭金髮,夫妻和兩個可愛又喜歡運動的兒子是快樂的一家四口。
一個夏日午後,艾文和母親一起來到我家,享用午茶和花色小蛋糕。
艾文的母親寶琳是位七十多歲的優雅女性,曾經在教育部門擔任特殊需求顧問。
她說自己不怎麼在乎三個小孩就讀的是哪一種學校,之後接受的訓練類型才更重要:「你是什麼樣的人才是重點,你的興趣是什麼?青少年時期在週六打什麼工?如果你想讀大學,就需要VWO證書。至於是以六分或十分拿到證書,根本無關緊要。」
總之,最後她的三個孩子都從事了和訓練領域不太一樣的工作:一個女兒本來念法律,現在則是為兒童製作影片;另一個女兒在學校是專攻南美洲研究,現在卻在百貨公司就職;艾文接受的是護理師訓練,現在則是自由作家。
對她們的母親來說,這證明了一件事:到頭來,學校生涯並沒有那麼重要。
我問艾文對兩個兒子有沒有什麼期望,她說:「如果他們想要走運動這條路,我希望他們可以進去好一點的隊伍。至於在學校方面,大概,只要他們開心就好吧,至少有一部分是這樣。不過,我也有點私心,希望他們有好表現。」
我不認為艾文真的屬於那一小群集中在富裕區南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Zuid)和谷伊(Gooi)──這一帶鄰近希爾弗瑟姆(Hilversum),是荷蘭最像好萊塢山莊一帶的地區──的高標準家長,她自己也證實了這一點:「就算哪個兒子沒有進入學術類組,我也絕不會煩惱到睡不著。」
(延伸閱讀│在平淡的赫爾辛基住14年,她體悟北歐人無法以金錢換算的「從容」)
競爭的弊病
在我的人生中,我發現從學校和大學的競爭氛圍(我總是拚命想成為最優秀的一群),過渡到沒有考試和比較指標的工作生涯,是相當困難的過程。競爭激烈的童年很容易讓人在往後的人生中時常感到失望。當評分制度消失,自尊心的來源也隨之消失;於是有人可能會用財務狀況、銷售數字衡量自我價值,或者投入大把時間為孩子尋找「最好」的資源。
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承受這種源於競爭的壓力,我寧願他們學會如何珍視自己的成就,而不是需要外界不停的稱讚或肯定他們「比其他人好」。
在《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的一篇文章中,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研究教授彼得.格雷(Peter Gray)寫出了他認為美國教育所出現的問題,不過我覺得,套用在英國也適用:在學校,孩子很快就了解到自己對活動的選擇和對能力的判斷都不算數;老師的選擇和判斷才重要。然而,老師難以預測的是,你可能認真念書卻還是拿到很糟的成績,因為你不懂老師究竟期望自己學會什麼,或是猜錯老師想要問的問題。在絕大多數的學生心中,課堂的目標不是習得能力,而是好成績。
把重點放在成績和考試結果,會造成學生錯失教學過程中其他同樣重要的事:學習科目相關的廣泛知識、啟發智能,以及擴展視野。畢竟,隨著好成績而來的工作機會和物質享受,並不是孩子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事物。
不過,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即使在小學,荷蘭學生每年都要接受兩次正式考試,測驗重點主要是閱讀和算術能力。
這些考試算是必要之惡,而且會盡可能以低調的方式進行。考試成績並不會讓學生本人知道,也不會以成績單的形式交給家長,只有在每年兩次的家長之夜可以讓父母快速一瞥。
考試可以輔助家長們去判斷,孩子在十一或十二歲時適合接受哪一類組的中學教育。但是並沒有所謂的總分,學校也不會蒐集或比較學生的考試成績──如我先前所提,荷蘭根本沒有所謂的「第一名」。
(延伸閱讀│亞裔價值觀 vs. 美式競爭力!用嶄新策略養育「乖乖牌」孩子)
荷蘭教育成功的關鍵
這種不崇尚競爭的態度在學校生活的其他面向也顯而易見:當我兒子第一次參加學校運動會後回到家,我想都沒想就問他跑步有沒有贏,他卻一臉疑惑地看著我。
難道他們沒有比賽跑步嗎?嗯⋯⋯,確實有,他們有一起跑步。不過他選擇等朋友追上來,手牽手,一起跨過終點線。
顯然,運動會的重點不在於贏,基本上也沒有什麼贏家或輸家之分,畢竟連獎牌、獎牌或隊伍都沒有,孩子一群群的在運動場上跑來跑去,嘗試各種不同的活動和挑戰,像是充氣溜滑梯、彈簧床城堡和撞柱遊戲,以及跑步、跳躍等等體育活動。
這和我小時候參加的運動會一點也不像,我被第一個欄架絆倒,從此留下一生難以磨滅的記憶,當時甚至連我的朋友也忍不住笑了。
OECD 2015年的「生活狀況」(How's Life)調查,衡量了許多OECD國家的幸福程度,其中荷蘭小孩是承受最少「課業壓力」的兒童。而不出所料,英語國家如愛爾蘭、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孩子壓力最大。
在「喜歡學校」的學童人數上,荷蘭獲得高分,而且綜合統計調查中所有項目之後,在「孩子在校的快樂程度」方面,荷蘭顯然表現最佳。
也許是因為荷蘭將技職學校納入教育制度,大多數的孩子在19歲前都有持續接受教育,僅有非常少比例的孩子提早離開學校。
有趣的是,荷蘭小孩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也獲得高分,雖然西班牙和土耳其的排名更高(這項同樣由OECD執行的全球調查,主要是衡量學生的閱讀、數學和科學能力),英國和美國僅分別排名第26和36。
荷蘭教育體系證明了,學業成就未必要建立在精英教育和激烈競爭之上。
另一項近期的OECD報告也顯示,荷蘭教育制度注重高標準的教育,據該報告指出:「學校優質的表現,加上仰賴實做以及實際鼓勵孩子運用想像力的教學方法,就是荷蘭教育成功的關鍵。」
離開學校之後,荷蘭人仍然維持高教育水準:根據針對16歲到65歲成人的PISA統計數據,荷蘭人在數學與讀寫熟練程度的平均分數排名第三,僅次於韓國及芬蘭。
(延伸閱讀│丹麥人4點就下班,競爭力卻世界第一?「人生優先順序」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