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五○年,全英格蘭的第一間咖啡屋正式於牛津開業;一六五二年,倫敦也出現英格蘭第二間咖啡屋。一六六○年後,咖啡在民間相當受歡迎,政府也開始對咖啡課稅,但民眾對咖啡的熱情依然未減。雖然有人認為喝咖啡會導致不孕,但咖啡屋仍一家接著一家開。一六六三年五月,倫敦至少就有八十二間咖啡屋,到了一七○○年至少暴增到了一千家左右。在布里斯托、約克、埃克塞特、巴斯、諾里奇、大雅茅斯、徹斯特、普雷斯頓(Preston)、華威、愛丁堡、格拉斯哥還有其他大城市都有不少咖啡屋。這些咖啡屋只服務男客,所以裡頭除了女服務生清一色都是男性(這或許解釋為何熱衷於咖啡的男性都沒有小孩)。只要你是男性,不管身分或階級都能到咖啡屋消費,當然前提是你要負擔得起。倫敦的洛伊德咖啡屋(Lloyd’s)與加拉威咖啡屋(Garraway’s)主要是服務商人。聖詹姆斯咖啡屋(St James’s Coffee House)與可可樹咖啡屋(Cocoa Tree)是政治人物聚集的場所──如果你是惠格黨黨員,就去聖詹姆斯咖啡屋,托利黨成員則是去後者。如果你想討論宗教信仰,最好到聖保羅教堂附近的咖啡屋,因為在其他咖啡屋內不能討論這些議題。如果你熱愛文學,那麼柯芬園的威爾咖啡屋(Will’s Coffee House)便是首選,因為約翰.德萊頓常在那裡發表他對最新書籍或劇作的見解,成為眾人的焦點。
一般的咖啡屋只會有一個房間,裡頭擺幾張桌椅讓客人使用。有些咖啡屋的室內空間則較寬敞。來到布里斯托,走進約翰.金伯(John Kimber)經營的大南方咖啡室(Great Lower Coffee Room),能看到三張桌子,周圍擺放了座椅、長椅、板凳,屋內有時鐘,櫃台上有一疊咖啡杯盤和玻璃杯,室內還有一座火爐,地板是由原木板鋪排而成,空氣中飄著咖啡以及菸草的氣味。第二間咖啡室位於二樓,內部擺設與一樓大同小異,只不過裡頭還有沙發、鏡子跟窗簾等奢華的家飾。就跟某些酒館一樣,有些咖啡屋老闆也用歷史文物來吸引顧客,其中有些例子令人捧腹大笑。像是在倫敦的某間咖啡廳,就以具有「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太太的侍女的姐姐的帽子」為噱頭來招攬客戶。只要付一便士的入場費,想在裡頭待多久就能待多久,還能喝著用一個個大甕煮出的熱騰騰黑咖啡,一邊抽著咖啡屋提供的裝了黑菸草的煙斗。喝咖啡的同時,你還能閱覽店家挑選的週報跟通訊報,或是跟「俱樂部」(club)的夥伴聊天、談論彼此關心的大事。在這個時期,「俱樂部」的意思是一群會定期聚會的朋友,以非正式約定的形式彼此平均分攤喝咖啡的費用。
想自己買咖啡在家泡也行。一六八九年以前咖啡每磅三先令,後來政府提高消費稅後,價格就隨之上漲。到了一六九○年代,每磅單價來到六先令。如果要在家喝咖啡,需要購入咖啡壺以及瓷杯。咖啡壺平均價格約為六便士,不過進口自中國的瓷杯每個則要一先令六便士。但是咖啡相對來說還是一種只會出現在公共場合的社交性飲料,如果在十七世紀有人躲在家中喝咖啡,那可是相當古怪的行徑。自己在家喝酒很合理,喝咖啡就不行。但是不管你在哪喝咖啡,就是有人對咖啡充滿意見。《抗拒咖啡》(A Satyr against Coffee)一書作者就提到,「把老舊、破碎的皮革拿去燃燒、搗碎成粉末,製造出來的氣味就是咖啡的味道:聞起來就像舊鞋……就像馬匹清洗池的氣味,就像女巫從死人骨頭中提煉出來的汁液……來自異國的屁味。」
一六五○年代末,皇家交易所附近的咖啡屋開始販賣中國茶。這款飲料很快就受到民眾歡迎,只不過價格相當高昂。第一批引進茶葉的商人將價格訂為每磅十英鎊。一六六○年,咖啡屋老闆湯瑪斯.加威(Thomas Garway)希望拓展茶葉生意,將價格降到每磅十六先令,並且廣為宣傳。這種行銷策略果然奏效。佩皮斯在一六六○年九月二十五號喝下生平第一口中國茶。當年底,政府也開始對茶葉課稅。一六六四年後,東印度公司開始將茶葉運進英格蘭後,茶葉價格就趨於穩定:最頂級的茶葉每磅三英鎊,最便宜的每磅一英鎊。來到復辟英格蘭,你一定會對茶葉的普及程度感到驚訝,只不過此時的茶種跟你的想像有所出入。此時期流通於市面上的主要有三種茶葉,而它們全來自中國(印度茶葉要到十九世紀才會引入英國)。寶希茶(Boehea)的茶葉呈現黑色,放入水中煮滾後的液體呈現褐紅色。第二種茶葉名叫辛格羅(Singlo),這種茶葉呈現藍綠色,其香氣之濃烈能重複回沖三到四次不成問題。第三種茶則稱為賓茶(Bing)或帝國茶(Imperial),這款綠茶也是單價最高的茶葉。以我們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復辟時期民眾泡出來的茶都不夠濃厚,而且他們也不會在茶裡加牛奶,很多人會在茶中加糖或蛋黃。
雖然品茶也是社交活動,不過茶跟咖啡的不同之處,是民眾喜歡約在朋友家裡喝茶。若要招待身分尊貴的賓客喝這種高級的飲料,就得準備等級相當的器具:茶壺、瓷杯、瓷盤、糖碗還有銀托盤。杯盤組和茶壺理應使用來自中國的瓷器,而東印度公司當然也樂得提供這些商品──每個瓷盤售價四先令,茶壺十先令。除了瓷壺也有英格蘭製造的銀製茶壺。一六七○年起,倫敦的銀匠開始用銀製作喝茶器具。富裕人家都希望擁有一套專屬茶具,藉以展現身分地位,也間接讓喝茶成為一種在家進行的活動。不僅如此,在保有隱私的家中,女性能跟朋友在家泡茶、喝茶,也是對男性專屬的咖啡屋文化的一種反動。從沃本修道院的支出帳單來看,就能發現貝德福伯爵跟伯爵夫人從一六八五年就開始品茶,而且他們喝的茶還比咖啡多,甚至投資了幾組茶具和茶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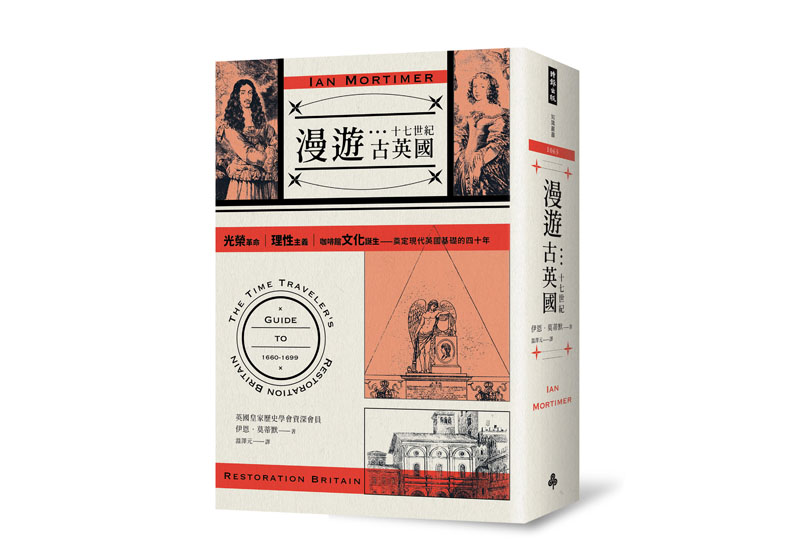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漫遊十七世紀古英國:光榮革命、理性主義、咖啡館文化誕生,奠定現代英國基礎的四十年》一書,伊恩・莫蒂默著,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