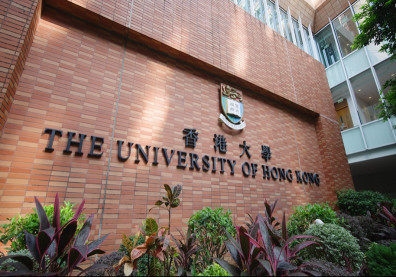感性與理性兼蓄並攬,交光互影,是黃碧端散文的最大特色。她作品的各篇之間,雖無一定的內在關聯,然其基本的理性論旨卻脈絡一貫,構成一個有機的中心體系;這體系,用理趣等字眼絕對無法涵蓋,準確地說,應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性格與精神之顯現,只有如此宏觀的歸納,方可說明黃碧端散文的思想風貌。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中國古代稱為「士」或「士大夫」,有其特定的歷史成因和精神指標。根據余英時先生的看法,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發韌於春秋戰國,定型於秦漢,嬗變於魏晉南北朝,以後各代皆有所傳承,形成了一個綿延不絕的傳統;近代的五四運動,也是此一精神的賡續與發揚。
余英時在《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中指出,中國士的傳統最重要的思想精髓,便是:內心的自覺(群體自覺與個體自覺),思想的解放(從社會綱紀秩序的建立到個體自由的放任飛揚),精神的自由(獨立思考與懷疑、批判傾向之強調);士必須以文化的傳薪者自任,高舉著理想主義的火炬,秉持其理性思考的特質,發為文章,為天下清流,發展出對整個文化與社會的深厚關懷;士必須超越他個人的利害得失,不畏強權,做群眾的代言人,彰顯正義與促進社會的進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弘毅之士,一向廣受社會尊敬,而其精神意態也是眾人望風景從的標竿;此外,士並不是道學家或狹隘名教的維護者,乃
是站在文化溯源和理性認知的基礎上,作「哲學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其理論的範疇並不局限於國家社會,也可提升到宇宙秩序的抽象思考世界。
穿裙子的士
我讀黃碧端的散文,便感受到中國傳統中「士」的精神氣質。她的文章,洞察世事,練達人情,內涵質樸密實,說理周詳深遂,讀後常常給人以融會與相知的欣悅。而對於社會上的種種不平與不義,她勇於批判,表現出高度的反思能力。歷史學者普謂「士必為男性」,而環顧今日學界,竟有許多如黃碧端一樣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饒有成績的女性,說她們是「穿裙子的士」,誰日不宜?
水淨沙明的境界
《期待一個城市》,所代表的是黃碧端散文的另一種向度,題材內容和表現形式都與她以往寫的文化評論不同,且更富文學性和藝術性。由於篇章不像報紙「方塊」那樣受到限制,在立意和述論上均有更大的發揮;感性與理性平流並進,相互輝映,灑脫自如,使讀者充分浸浴在她哲思的豐饒與文字的美感中。看完這些作品,不禁驚歎作者的學養豐碩,見多識廣。大千世界林林總總的現象,通過她的觀照,總能達到一種水淨沙明的境界,予人以最深的感染和頓悟。這樣的寫作風格,使我想到法國散文家蒙田(Montaigne)以及古羅馬作家西塞羅(Cicero)的作品,它們都有一種以小見大、執簡馭繁的能力,有時即使記錄純個人的精神生活,也能使人
推延到磅礡恢宏的大群體精神。
涉獵之廣、思考之深
第一輯「創造力的弔詭」中的主題文章,是少見的力作,其中有許多創見,言人之末曾言。作者舉出文學藝術史上的一些人物案例,以闡明創造力的微妙與神秘。古人有云「詩人不幸詩家幸」,而黃碧端所說的「弔詭」,是她發現「賜與創作能量的和扼殺創作生命的,常常是同一個力量」;藝術家的理性與非理性,正常與脫序,永遠是最不可思議、最難解讀的謎題,我們只能像作者一樣喟然歎曰:「然而對創造力來說,更大的弔詭來自那位更高的創造者!」這樣富有悲憫的推論,與宗教學、藝術心理學和遺傳學關係密切,黃碧端做學問涉獵之廣、思考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第二輯「舞台」各篇,均為討論戲劇藝術和現代劇場的,這是她任職國家兩廳院時的學術感思,論述嚴謹,觀察敏銳,可以稱得上舊學新知雙勝,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這些體認大多是通過各國戲劇團體來華演出的實際印證,特別值得重視。莎士比亞不在圖書館而在戲園裡成長,才能寫出那樣富有生命力的戲劇,同樣的,一般人的「書齋論劇」也絕對比不上「劇場論劇」來得鞭辟入裡。當年黃碧端從中山大學教席被借重到兩廳院時,很多朋友擔心事務性工作會影響到她的治學,讀了這輯文章,覺得她「未受其害,反得其利」,這是在學院中絕對得不到的意外收穫。
第三輯「期待一個城市」,收入多篇具有現實意義的論述,這使我聯想到現代美學的一個分支--環境美學,它也是生活美學的一個從屬。這是近十多年新興起的學科,在西方先進國家正逐漸受到重視。黃碧端對城市的期待,包括都市的文化建設、「市場機制」與文化的互動關係、視聽美育的落實等,而這正是環境美學所關心的範圍。我們深盼有更多像她一樣的有心人,大家合力去追尋現代生存環境的審美要求和審美規律,進而創造富而好禮、洋溢詩韻書香的美好社會。
第四輯「閱讀」分量亦重,主力在探討印刷書與電子書閱讀與閱聽的平衡問題,剖陳當前社會病態,扣緊青年次文化紛紜多變的脈絡,洞燭機先,目光遠大,是難得一見的深度文化評論,這又顯示出她懷抱知識分子獻身參與的意向,不過都是藉著從容優遊的隨筆小品形式來體現,面貌親和,深刻入理,使人樂於接受。有人說黃碧端「兼有學者與創作者之長,說理處,舉重若輕;抒情時,優美動人」,絕非虛譽之辭。輯中其他佳篇如〈張愛玲的冷眼熱情〉、〈恐詩症〉、〈當典型成為夙昔--紀念張繼高先生〉等,均有與時下流行看法迥異其趣的創發,顯示出豐沛的理性認知與雄厚的學識基礎。而行文篇幅簡潔,不蔓不枝,映照出一位可敬愛的現代學人清澈的心靈倒影。
(本文作者為《聯合報》副總編輯兼副刊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