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問題是做比較時出發點的基礎太薄弱。人們一般假設,分裂的德國跟分裂的朝鮮半島差不多相同,而前西德大約相當於南韓,前東德大致跟北韓一樣。但是沒有一個假設能經得起仔細的觀察。
是的,德國被分割成兩半,就跟朝鮮半島一樣。但這也幾乎就是全部的相同點。德國的分裂起因於二次世界大戰,身為侵略者和大屠殺者的希特勒和他的政權被戰勝的這項事實。許多德國人把國土分裂當作懲罰接受。相反的,朝鮮半島是日本的殖民地,也就是軸心國的受害者,一九四五年慶祝從壓迫者手中解放出來。之後的國土分裂,從過去到現在都被認為是歷史上極不公平之事,這就是兩韓都對所謂的強權有極大不信任感的原因之一。
從國際法上來觀察也可以發現明顯的差別。直到一九九〇年,德國隸屬於四國共管的狀態,也就是由四個占領國共同負責,雖然大部分的民眾最後幾乎感受不到。盟國管制委員會首先被二加四協定取代,德國的完全獨立自主權一直到一九九一的這一步才算重新被建立起來。所以德國統一的時候,仍有幾萬名外國士兵在德國的領土上。
相反的,到一九四〇年代末期,蘇聯和美國已經從朝鮮半島撤兵。美國人是因為韓戰再度回到朝鮮半島,但是在完全不同的法律規範下。現在還有大約兩萬五千名美國士兵駐紮在南韓,但不是占領,而是在一種正式結盟的框架下。朝鮮半島完全獨立自主只規範在結束韓戰而簽訂的和平條約中,聯合國也參與其中。
在德國統一的進程中,一直必須把第三勢力的法律要求考慮進去,這個情形在兩韓的例子上卻無關緊要。前總理柯爾需要來自倫敦、巴黎、華盛頓和莫斯科給予的綠燈通行許可;相反的,南北韓人一定會很高興能得到鄰國和結盟夥伴對統一進程的支持,但在國際法上並沒有必須與他們協商的義務。
政治和意識型態上也有很大的差別。如果把一八七一年帝國的建立當成基準,一九四五年德國雖然還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但是已經有一段比較長的啟蒙傳統和民主前身。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瑪共和國的失敗、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過等等令人震驚的經驗,替東德和西德一九四五年後政治階層的自我認知奠定下基礎。
兩韓的情形正好完全相反,國家統一的局面已經存在幾世紀,但是對民主和啟蒙的認知卻非常有限。現代國家意識的形成是對十九世紀末期日本入侵時所做的反應。一九一〇年成為殖民地以後,朝鮮組織獨立運動,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的暴動中達到高峰。一九四五年後,對殖民統治者日本的抗爭決定了政治菁英的自我認知,一九五〇後再加上韓戰。
德國絕大部分的人對國家主義情感持拒絕態度,至今也以懷疑眼光加以審視,但是在兩韓,國家主義是統一議題中被各方接受的核心成分。它蘊含的內容廣泛,例如願意為了統一不惜犧牲,南北韓人將統一的理想價值明顯地估計得很高,特別是他們希望達成統一後,能增強與鄰國打交道的力量。
比較官方對統一問題的態度,一九八九年的德國和二〇一四年的兩韓也有很大的差別。東德很早就放棄原本甚至寫在國歌歌詞裡(讓我們為你盡一份心力,德國,統一的祖國)對德國統一的願望。西德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還不願意放棄統一的主張,但事實上,大家已經認清必須接受兩德分裂的事實。就算人們現在不樂意再提起,其實西方人當時就快要承認東德是獨立自主的國家。當何內克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在波昂進行國是訪問,走紅毯經過禮賓衛兵時,他同時能聽到東德的國歌和看到東德的國旗。西德的基民黨甚至考慮更改黨章,讓承認東德的過程沒有阻礙。德國是在幾乎沒有準備的情形下遇到統一的機會,很矛盾的是,這卻幫了個大忙。我們經歷到的快速進程,如果處在有兩個既定針鋒相對的方案並存的情況下,想必會艱難許多。
相反的,統一是兩韓不可更改的國家信念,雖然這份熱情在南韓特別是因為擔心支出過高而有消退的跡象。一個在南韓做的民意調查發現,支持統一的民眾人數從二〇〇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四左右,降到二〇一三年的百分之五十五。在同一個時期裡,反對人數從百分之十五升高到百分之二十四。除此以外,南韓人對兩部分國土再度統一的展望也越來越悲觀。二〇一三年有大約百分之二十六的受訪者認為統一不大可能,是二〇〇七年的兩倍。針對人們認為統一能帶來哪些利益一題,主要的答案是混亂的國家主義以及對國家安全的擔憂。那些把改善北韓人民生活當成必須統一的理由的人,二〇一三年只占五點五百分比,而百分之四十的受訪者把歸屬感當作主要原因。百分之三十一的人認為統一最重要是可以避免第二次韓戰。但是在南韓,對民族共同點的感受看起來至少與對北邊鄰居的恐懼重疊。南韓於二〇一四年五月公布了一項民意調查,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把北韓視為敵對的國家。
北韓沒有類似的調查,那裡只能聽到官方的意見,而這個意見是嚴格主張統一。
德國和朝鮮半島在地緣政治的位置上同樣也有差別。德國位於大陸的中心,一九八九/九〇年,兩個敵對勢力陣營的界線穿過這裡。相對的,朝鮮是亞洲邊緣的一個半島,只有三個鄰國。兩韓統一在全球政治上的重要性不及德國的例子——除非舊的領導勢力美國和新崛起的中國之間的新衝突要在這裡決一勝負。這有可能,但不是必然會發生。
除此以外,差別還顯現在國土統一對區域影響的預期心理。幾乎所有歐洲的鄰國,包括法國、英國和波蘭都有很大的擔憂,害怕統一後的德國會再度對他們的生存造成威脅。
雖然鄰國中國和日本同樣對統一的朝鮮半島持保留態度,主要是因為多起領土的要求,但是這個區域對韓國帝國主義式的稱霸意圖並沒有可以讓人擔心的歷史根據。兩韓統一在較高的程度上來說屬於本國事務,跟德國不一樣。但這並不表示,鄰國對這個議題不感興趣,然而這個保留態度有不同的性質,所以也需要另一種解決方案。
至於兩韓彼此互動的方式,跟德國也有明顯的區別。我們可以感到慶幸,韓戰相同的情況沒有發生在我們身上。因此也形成我們口頭和其他互動上某種程度的節制。當我在東德服三年兵役時,我們的軍官不斷指示,不要把西德稱為敵人,而是對手。相反的,兩韓之間一直都還有射擊演習,而且把對方國家領袖的肖像當成槍靶,也一直會透過媒體打口水仗互相謾罵,北韓還生出一種極有問題的語言創意。兩德邊境曾發生過嚴重事件,尤其是在柏林圍牆邊喪生的人。但是德國沒有像兩韓間經常出現有人員傷亡的武裝衝突。
他們彼此也幾乎不瞭解。跟分裂的德國不一樣,南北韓之間只有零星的表面接觸。如果跟兩德民眾及貨物過境協定、頻繁的書信和電話往來,以及相互拜訪相較,兩韓之間安排的幾百個家庭拜訪就相形失色了。跟其他幾十萬的家庭一樣,我們在逢年過節時也會按時收到包裹,偶爾有親戚從西德來訪。我的祖母從六十歲生日以後,會定期拜訪「在那邊」的兩個姊妹。一九八八年二月,我媽媽雖然離退休還有很長一段時間,她也可以完全公開地前往威騰(Witten)慶祝阿姨的生日。單單在一九八七年一年,就有一百三十萬的東德公民前往西德和西柏林。能合法到南韓旅行的北韓人數卻屈指可數。
尤其是柏林,朝鮮半島沒有一個類似的城市,每天讓幾百萬人深切地感受到國土分裂的種種荒謬情形。身為萊比錫人,我一直問自己,為什麼有人特別挑選兩德邊界中看守最嚴的地方,柏林,試圖從那裡逃亡。難道沒有比較沒有危險的選擇嗎?當我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在上翠柳市(Oberschöneweide)火車站的緯度,第一次從火車窗口看到圍牆和後面近在咫尺的西柏林時,我突然了解:這個景象和聽到與讀到的分裂狀況是完全不同的。這個景象很沉重,對很多人來說,沉重到難以負擔。
相反的,兩韓之間的非軍事區位在人煙稀少的地區,一條寬四公里的綠色帶狀區域。南韓這邊有不同的觀察哨,可以用強力望遠鏡看一眼模糊的稻田和幾座低矮的農舍。最多在簽訂停戰協議的地方板門店可以仔細看到另外一邊的情形。但那是用木板屋和涼亭打造的人工世界;分裂的柏林卻是真實、熱鬧、近在眼前,並且折磨人。
沒有任何東西能取代直接的親身經歷,但是媒體也能激勵願望。西德電台在東德的影響非常大;我們家可以接收到的五家電視台中,三台是西德的。當我還是青少年的時候,我只聽北德廣播電台(NDR2),而這是合法的;只有特定團體,例如部隊的成員禁止使用西方的媒體。因此我是在一九八七年開始服兵役時,才開始聽東德的廣播。除了國家准許的娛樂節目外,我無意間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但是被公家機關以懷疑眼光關注的次文化,並很興奮地投身其中。
北韓禁止觀賞或是收聽南韓的電台,而且幾乎也無法接收得到。雖然DVD和USB隨身碟在穿越中國綠色邊界的路上衝破了這道藩籬,但是內容一般多是連續劇。這裡不可能像東德一樣還有一個默默被接收的龐克文化,更不用說宗教信仰的自由或是許多藝術家享有的遷徙自由。
從過去到現在,兩韓之間的交流從來不曾有兩德政府間交流的密集和頻繁。在南北韓,對共同點的意識和對彼此的認知是很混亂的,而東德的國民透過廣告、國際商店、鄰居或是訪客,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切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此政治學家艾卡哈德.耶瑟(Eckhard Jesse)從東德人的角度把西德很貼切地稱為「對比社會」。南韓卻遠遠不能替北韓扮演同樣的角色。
然而南韓人對北韓所知也非常有限。這也跟住在南韓的脫北者人數很少有關係。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之間,大約有三百五十萬的東德人離開自己的國家到西方去,而一九五三年到二〇一三年間,只有兩萬六千一百二十二個脫北者從北方逃到南方。鑒於北韓人口比東德多出百分之四十,如果做一個相對性的觀察,我們必須把原本就很少的數目再降低。日常生活裡,大部分來自貧窮東北方的脫北者想盡可能掩藏身分,因為他們害怕在競爭激烈的南韓社會裡會遭到歧視,而且這份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長期以來,南韓對北韓人的想像也同樣怪誕。一九七〇年代南韓的小孩們還會學到,北韓的共產黨員是惡魔般幾乎沒有人性的生物。這個情況改變了,但是直到今日,南韓對自己的同胞還是多有保留。首爾政府還是跟以前一樣,只是有條件地跟人民透露與北韓有關的事。例如北韓媒體的網頁在擁有民主高科技的國家南韓被封鎖,而且單單擁有金日成寫的書就違反了國家保安法。二〇一三年還有民選的南韓國會議員因為支持北韓的陰謀活動而被逮捕和判刑。二〇一三年九月,南韓的軍事單位用了好幾百發子彈掃射一名欲游泳橫渡界河到北韓的男子。
看一眼各自主要的結盟國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情況的差異。謹慎地說,東德在經濟和政治上是蘇聯的衛星國,它不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製造重型卡車或是購買潛水艇;莫斯科用簡單的一句「njet」(不)就否決了這兩項決定,因為他們對以前的侵略者仍抱持懷疑。相反的,北韓並沒有「大哥」,就算現在有人假設中國扮演了這個角色。這個想法在西方相當流行,但是多半出自於無知或是願望,希望如此一來可以對中國施壓。事實上,北韓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相當獨立,讓國家能較少受到外來影響,這也適用於可能的統一問題上。
他們的獨立性不會因為急需跟中國經濟合作而有所改變。這個合作只是更凸顯出另外一個差別:北韓最重要的夥伴是一個在任何一方面都正在崛起的強權。東德當時最緊密的結盟夥伴在經濟上卻一敗塗地,雖然戈巴契夫有最好的企圖心,卻正走向政治解體的路上。時代見證人如艾貢.克倫茲(Egon Krenz)和漢斯.莫德洛夫(Hans Modrow)都公開表示,東德被戈巴契夫賣給了西方;中國領導人應該不會想到這個主意,至少不會抱著得到大量經濟援助的希望。
如果我們假設,統一會讓兩個國土的發展水平向上靠攏,那觀察兩德當時和兩韓現在的差距將會很有趣。東西德在科技和教育水平的差距非常大;但是如果把兩韓放在同一個觀點下觀察,兩德的差異就淡化了。同樣情形也適用在基礎建設、消費行為,或是對世界的認知上。
德國統一的進程中,有許多鮮為人稱道的運氣,其中之一是我們一起經歷了職場和私人生活大幅電腦化的改變,因為這項改變一直到一九九〇年後才如火如荼地發展。北韓只有一小部分人口才享有電腦和平板電腦,更別提上網的可能性,因為北韓內部的網路受到封鎖。如果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統一的時候,那北韓大眾的知識缺陷可用文盲相比擬。兩韓生活現實的極大差異還表現在其他領域,以至於為了協調雙方的差異,得付出遠遠超過為德國例子所付出的努力。這牽涉到與公家機關的往來、新社會關係網絡中的行為,或是在生活和工作上設定正確的優先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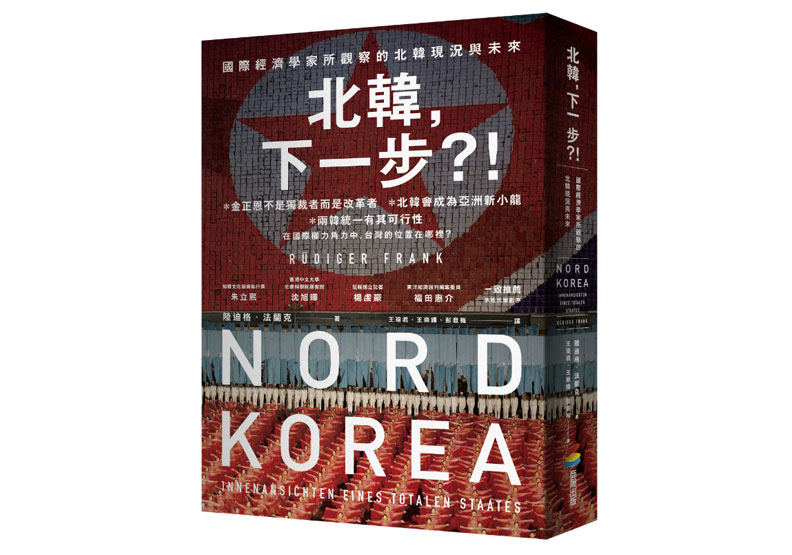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北韓,下一步?!——國際經濟學家所觀察的北韓現況與未來》一書,陸迪格.法蘭克(Rüdiger Frank)著,王瑜君、王榮輝、彭意梅譯,商周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