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者的話語中會出現驚人的隱喻,而關注對我們所愛的人有意義的隱喻,能導出療癒人心的對話。例如,以旅行而非戰鬥來談論死亡,如此一來可讓臨終的過程更像是探索及發現,而不是慘敗。
旅行隱喻是臨終者語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人們談到抵達旅途的終點,某些個案也說到將要展開一段新旅程。在臨終者的話語中,大量出現與運輸和車輛相關的語彙。安妮特是我的口腔衛生師(dental hygienist),她和我分享了她祖母的最終話語:
「黃色公車! 公車來了。」
「奶奶,誰在開公車?」
「不知道,不知道......但有好多天使!」
旅行的符號和前一章所談論的重大事件隱喻非常類似,都和當事人的一生有特定關係。安妮特的祖母都在星期天上教堂做禮拜,她的一生中,身旁總是充滿和天使有密切關係的圖片。喜愛帆船航行或乘船遊覽的人,可能會談到有各種船隻正等候著他們;我的父親愛賭,在他過世前幾個星期則是宣告:「我們將有一趟長途飛行,要到賭城拉斯維加斯。」
第一次聽見病人說出以下的話時,一位安寧照顧護士感到毫無頭緒:「我的捷達(Jetta)在哪裡? 我的捷達在哪裡?」後來才知道,他有一輛福斯汽車出廠的「捷達」。為了讓那位病人安心,她告訴他捷達「已經加滿油,幫你準備好了」。幾天後,他過世了。
「我的行李打包好沒? 火車快來了,我必須準備好才行。我在找月臺,有誰知道是哪一個月臺?」有一位女士的哥哥問她這些話。
和臨終有關的類比,我所聽過的沒有一個是說要出門長途散步或慢跑。雖然有幾個人說過「拿外套給我,我得走了」,但我的紀錄裡沒有一條是說「拿球鞋給我,我準備出去走一段長路。」交通運輸的隱喻牽涉到外來的力量,也就是在我們的肉體之外,有某個人或某樣東西可載運我們。以下這段語句是個例外,有位女士在接近過世之前曾經重複說過幾次:「跳上跳下,蹦蹦跳跳,一跳,就到了。」但是這一段語句比較不像是關於她「旅行」的方式;若說她已知自己的大限將至,這句話是在表達她的感受,反而更近乎事實。
類似以下這些才是典型的語句:「帶我到公車站,現在該回家了。」「我要搭的船到了。」或者,如前文提過的,有些人會表示需要護照。有多位安寧照顧護士告訴我,不論病人在臨終前的個人診斷、用藥或身體狀況如何,像這一類隱喻非常普遍。
旅行隱喻隨處可見
以旅行隱喻死亡1,這個隱喻手法根植於我們的人格和生活之中。這不僅是在個體層次,在人類集體層次亦然,因為普天之下的任何語言及文化,都含有這類隱喻。來看一些實例:談到死亡時,阿富汗人會說是「到山羊地」;荷蘭人說是「鑽出管子」;德國人說是「到永恆的狩獵場」;希伯來人說「下降到來世」;匈牙利人說是「動身前往永恆的狩獵場」;愛爾蘭人說「走在真理之路上」;西班牙人說是「去旅行」、「通向更好的人生」或是「搬到正面朝上的社區」;葡萄牙人說「上樓」;至於羅馬尼亞人,他們會說是「在街角轉彎」,丹麥人也有「在街角轉彎」的說法。有一名說英語的受訪者提供一樁有趣的案例,她父親的最後話語是「到街角還有多遠? 我要在街角右轉,那是我以前常住的地方」。中文世界裡,要暗示某人將不久於人世時會說「敲開死亡之門」,雖然那不是表示旅行的語言,仍暗示有一扇門向著新世界開啟。
讓我們來看這位男性的個案。他在臨終時宣告即將展開朝聖之旅,鐵軌的隱喻讓人產生前往某處的感覺,猶如他正在遠離車站:「對於沒有選擇上路的,我們這些踏上朝聖之旅的人要和你們短暫或永遠告別了......願意的人都可以加入,還請慢慢退後,這趟朝聖才能步上正軌。慢慢退、慢慢退,我們要出發了。」
凱利.巴克里和牧師派翠西亞.巴克里的研究發現,夢到旅行是很常見的事,這些夢往往能讓臨終者的恐懼轉變成探險或驚奇的感受。以下實例取自他們的著作,證明旅行夢的強大力量2:「夜裡,我再度航向未知的汪洋。熟悉的冒險感回來了,我又感到興奮不已,覺得自己乘風破浪,衝向巨大、黑暗而且空曠無比的大海,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在正確的航道上。我一點都不害怕死亡,真是奇怪。事實上,我已經準備好出發了,這感覺一天比一天強烈。」
他們對於病患的臨床觀察,在二○一四年的一項研究中獲得確認。該研究是關於臨終者的幻象和夢境,研究者要求病人描述夢的內容。經過這一次追蹤研究,兩位作者發現幾乎高達百分之四十的參與者都夢到出發或準備出發到某個地方。是否有這樣的可能:隱喻性語言的增加反映了將要有一次旅程,要從這個五感及三度空間組成的平實世界離開,準備前往另一個世界,而且這樣的經驗卻是無法以字面意義的語言直接表達的?
琴.馮.布朗克爾斯特告訴我們,臨終者的夢境顯示兩個重大的訊息,這兩大訊息和我們在最終對話中聽到的內容有密切的關係:「首先是冷靜、直接、偶爾也是發自肺腑地斷言肉體將會死亡。在這些夢中,各種事物都故障了,醫生垂頭喪氣離去,做夢的人聽見一切已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另一個訊息是關於做夢者如何「旅行到新的地點,在那裡和知交故友重逢,並且能超越肉體生命,從某處獲得協助及安慰。」
我們所聽到的各式隱喻,或許代表各自在應對死亡的新體驗時,有一段真實的旅程或是全新的經驗境界等待著我們。也有可能是在嘗試理解死亡經驗時,我們以驚奇、漫長的探險(odyssey)做類比,也就是用已知的事物,替代這個經驗中令人害怕的未知。
臨終之際,許多人會進入新的境界,語言將以嶄新的方式運作。語言做為工具,它的主要用途不再是傳達這個共有的平實世界。反之,語言如同交通工具,載送我們前往新世界。旅行的聯想伴隨著移動的感覺,取代了字面語言的地位。這些變化讓人想到瀕死經驗者說的無意義旅行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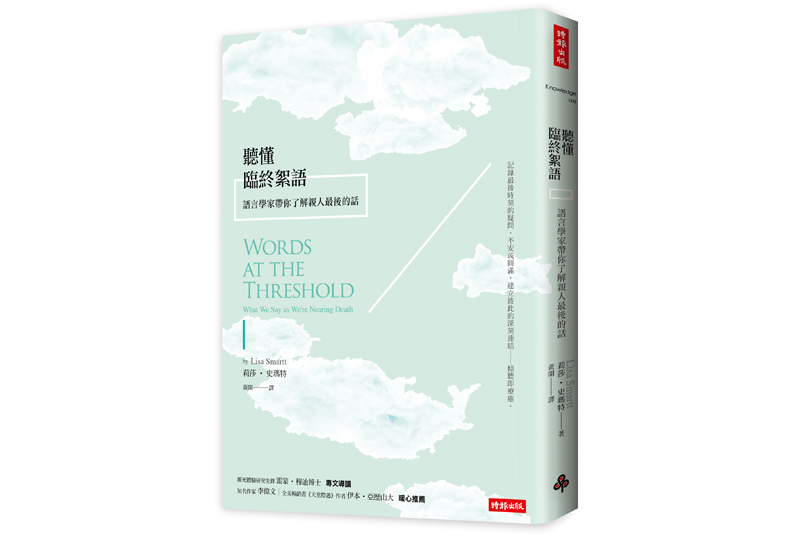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聽懂臨終絮語──語言學家帶你了解親人最後的話》一書,莉莎‧史瑪特(Lisa Smartt)著,黃開譯,時報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