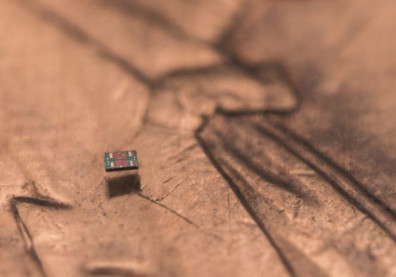在美國所有的大型新聞刊物中,和中國最有歷史淵源的就是時代周刊。這個刊物的創始人魯斯不僅在中國出生,並且在早期發展中,特別關懷、重視中國的政治變遷,與中國相關的報導,可能比其他任何美國主流雜誌都要多,其觀點也傾向於主觀,對中國歷史人物的評價,也多偏重於保守傳統的一面。
對中國的使命感
從兒童時期開始,一直到去世為止,魯斯都保持了對中國問題的高度興趣,他曾有一次公開的稱自己為「對中國情不自禁的人」(Someone With Hopeless Sentiments about China)。
魯斯和中國的深厚情誼,可以從以下幾項具體的事實得到證明:
(一)在一九三七~四五年間--即對日抗戰期間,他曾多次往訪中國,親自觀察和了解中國人艱苦奮鬥的情況,回到美國後,以演說和發表文章的方式,大力疾呼輿論界提供援助。日本正式侵略中國之前,魯斯也曾主張美國對日本實施貿易禁運;一九三九年他曾強烈要求美國以武力干涉日本違反國際法,侵占「滿洲國」;一九四一年,他偕同夫人前往戰時重慶,訪問蔣委員長後,曾直接在「生活」雜誌上報導觀感,返美之後,也曾用他個人的信箋,呼籲「時代」的每一個訂戶,為中國捐款……。
(二)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之後,魯斯一方面由於個人和蔣委員長之間的友誼,一方面也由於資本家的理想,對國共之間的內戰,便很明顯的採取了堅決反共的立場,當時駐中國的特派員自修德(Theodore H. White)因報導國民政府貪污腐化和共產黨大得人心,而遭到免職之外;還破例的向當時另外一位駐遠東的特派員格瑞
(Wi::iam Gray),以電報方式,提出有關中國事務報導的明確指示:「(1)基本政策是不偏不倚的報導事實;(2)我們應像美國政府一樣,承認蔣(介石)為合法的國家領袖,且為我們的忠實盟友;(3)對蔣所領導的政府之中,自由派與反動派的鬥爭,我們應支持自由派;(4)我們決不參與或鼓勵任何企圖推翻蔣介石的宣傳活動;(5)我們相信援助蔣介石至少和援助史達林一樣,會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好處;(6)我們相信,美國的對華政策,應該保持歷來國務卿的主張,只有一個獨立而不受任何外力所操縱的中國,才最能符合美國的立國精神和國家利益。」
(三)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前,魯斯和周以德參議員普組織聯合陣線,在美國國會和輿論界呼籲支援國府反共,可惜當時的杜魯門和艾契遜國務卿,已把注意力集中到歐洲的復原上,幾乎完全忽視亞洲問題,魯斯等人的努力,幾乎完全失敗,而後才有追究「誰失掉中國」(Who Lost China?)以及麥卡錫參議員在國會舉行轟動一時的「清共」聽證會,使美國上下發生過一次全國性的「恐共」病。
(四)一九六0年間,魯斯出資成立「魯斯基金會」,在紐約資助「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的活動,促進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另外更在台灣台中的東海大學,聘請貝聿銘工程師設計、建立一座紀念魯斯父親的教堂,並捐款給其他國內的教育和慈善事業。
肯定蔣介石
以上所舉的事例,只不過是魯斯一生對中國「使命感」的一部分表現而已,其他還有於戰時在美國組織「聯合救濟中國」財團法人,為中國募款;邀請蔣夫人到美國各地演說,並在國會現身說法,說明抗日的艱苦情況;在「時代」和「生活」等雜誌上。不斷為中國報導……等,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細讀將近二十年的「時代」封面故事,儼然就是一段充滿血淚的抗日歷史,有可能對蔣介石夫婦產生更大的肯定,因為他們代表了中國人民當時不屈不撓的堅定抗日意志,同時還.充滿了最後必勝的信心。
譬如在日本正式用武力侵占中國領土的前夕,「時代」於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第十八卷十七期)第一次在封面刊出蔣氏夫婦穿中國服裝的照片,並以五欄(約四千字)的篇幅,詳細報導了日軍在東北的暴行和全世界華人(包括加拿大和美國)拒買日貨的愛國運動,同時在軍事和政治方面,也列舉了蔣釋放政敵以團結抗日的策略,並指出由蔣介石訓練的黃埔軍校幹部,將成為抗日戰爭的軍事骨幹……等,顯然企圖宣傳和鼓勵蔣的實力。
另外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蔣將軍」封面故事,開頭和結尾都是讚揚蔣委員長的文字:前者稱他為「融合世界上人口最多、內亂最大國家的偉大軍人政治家」,後者則引用「蔣總司令」頒給「第十九路軍」肅反福建偽政府叛變的命令,顯示其統一中國的決心。
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底,「時代」選擇蔣氏夫婦為年度「風雲人物」,根據該刊中的說明,當時全世界包括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蘇聯的史達林、英國的溫莎公爵或暫時執政的女皇瑪麗(Mary the Queen Mother),或張伯倫首相……等,都不足以被稱為對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倒是在亞洲,因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壯大,使「白人對亞洲統治的時代告一段落」(此語係「時代」引用中立國瑞典的亞洲專家赫丁在瑞典皇家學院的演講辭)。
「時代」偏愛中國
一九四三年二月,由於魯斯從中穿梭,蔣夫人以蔣委員長代表的身分訪美,先後在美國參眾兩院演說,當時「時代」的報導中就指出:「她瞭解她的演說對已經決定的軍事策略不會有很大影響,但是她現身說法,卻對兩個偉大民族之間的相互瞭解,有不可估計的貢獻。」
惟一使魯斯失望的就是一九四三年的三月(即蔣夫人訪美後的一個月內),白修德發自中國的報導中,很嚴厲的批評國民政府,以很尖銳的文辭,寫出河南省的災荒和饑餓情況,「狗在路邊吃死人的骨頭,農民在黑暗的夜晚也找死人的肉吃,無數的鄉村荒廢,每個城門前充滿了乞丐,許多嬰兒也棄於路邊,哭啼待死……,河南的三千四百萬人口中,估計就有三百多萬的乞丐,另有五百多萬在秋收之前,一定會饑餓而死。」這個悲劇的主要原因,白修德說,主要是國民政府軍隊強徵糧稅,使農民無法抗拒。同時也無法生存下去。
這種負面報導和批評,當時並沒有遭受到魯斯的壓制,一方面因為饑荒遍野的情況,有照片為證,都是事實,任何人也無法隱瞞。同時,白修德還在報導中公開為中國人請命:「這個國家幾乎要在我的眼前死亡。(日本的經濟)封鎖將致中國於死命,通貨膨脹嚴重。這個國家的一切腐爛情事,都與封鎖和通貨膨脹有關。只有透過援助,中國對大戰才會有幫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終於投降,抗日戰爭結束。「時代」於該年九月三日出版以蔣介石為封面的報導,這一次是用他穿軍服的肖像,帽子上有青天白日國徽,背景是國民黨旗,文字的說明:「蔣介石--八年戰爭與和平挑戰之後」。在「封面故事」裡,蔣氏接受「時代」特派員傑考比訪問,發表對國事樂觀預測及迎接勝利的歡欣。
基督徒的軍事行動?
不幸的中國,抗日的勝利並沒有為人民帶來渴望已久的和平,國共內戰接踵而來,結果又是民不聊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時代」又以蔣氏為封面主題,報導國民政府被中共紅軍追擊,和蔣氏威望「下沉得比長江還低」的情況。
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出版的「時代」,第一次編製以毛澤東為封面的專題,除了在毛的肖像旁邊加上「民主統一」四字口號之外,圖片下的說明是:「中國的毛澤東--共產黨頭子,自童年即學會專制」。
在這一篇將近五頁的「封面故事」裏,主題完全集中在毛澤東個人,從他的出生、在湖南就學、成為馬克思的信徒、組織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宣傳、領導長征、窩居延安主謀抗日游擊戰,並與國民黨多次談判,開始正式內戰以致擊敗國民黨的軍隊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後共有二十二年的戰爭經驗,終於在人民厭戰和國民黨內部分裂腐化,及得不到美國的支持下,獲得了軍事和政治上的最後勝利,成為中國的現代獨裁者。
令人有些出乎意外的,就是在中共正式統一中國大陸,而毛澤東宣布「中國人站起來」的時候--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左右,「時代」並沒有再用「封面故事」的長篇文字記錄這個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變局。
從此以後,時代周刊上所刊載的有關中共的「封面人物」或「封面故事」,便都是負面的形象和事實,如韓戰開始(一九五0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澤東在「時代」封面上與蝗蟲為伍的肖像,圖片說明:「赤色中國的毛--新戰爭,舊軍閥」(Red China’s Mao:New War, Old Warlord),內容便是中共參戰,與美國正式衝突的新聞報導。
直到一九六七年魯斯去世之後,這種「反共」的編輯政策才逐漸開始改變,「封面故事」的主題和內容,也隨之更為客觀、平衡,不論是對毛澤東或周恩來、華國鋒等「封面人物」,也都不再以「負面」的漫畫諷刺或加上「負面」的背景,使他們的形象難堪。相反的,有關中國的新聞報導,已經完全不再受任何人主導,而是由通訊記者、研究員、資深編輯和主編共同協調,用「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以事實代替理念,以照片或藝術畫像代替漫畫家的幻想。
對中共由冷至熱
尤其在一九七一和七二年尼克森總統也一反過去「反中共」的立場,開始和中國大陸以秘密外交的方式,改變整個美國的對華政策之後,「時代」便和其他美國的主流新聞媒體一樣,進入一個由冷至熱的新階段,一連串編寫了許多以周恩來和鄧小乎為封面人物的專題報導。
單是一九七一至七五的四年間,六篇有關中國的封面故事中,五篇都是以周恩來為「封面人物」。一九七六年周恩來和毛澤東相繼去世之後,鄧小平就成為「時代」上常見的「封面人物」,而且還曾於一九七九和一九八六年兩次當選為年度「風雲人物」,在「時代」的中國報導歷史上,成為惟一的先例,足以和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以及其他多次被選為「風雲人物」的世界領導人物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