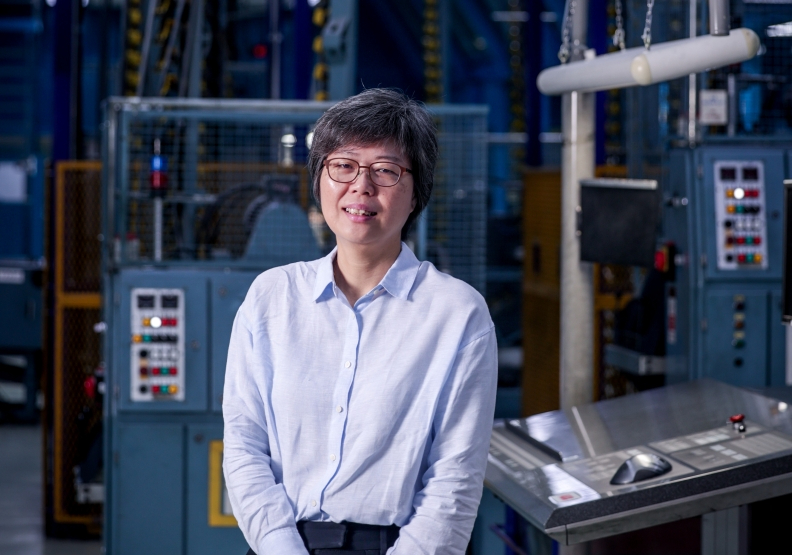跟學生講課,談到新加坡中文媒體的起落,很難不談到過去教育政策調整導致的結果。
英國殖民地時代,新加坡英校與華校拆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世界的學生唱著《God Save the Queen》(天佑女王);另一個世界的學生唱著「向敵人的砲火前進」。
實際上,我成長的1970~1980年代,父母和祖父母輩如果說英語,大部分是聽不太懂華語的。後來,也因為社會、政治的因素,以及英語的經濟價值遠遠超過中文,華校小學的生源萎縮,最終面臨關閉的命運。
在這中間,還包括1970年代末期,新加坡教育部決定統一語文源流,除了保留「華文」作為語文科之外,其他科目的教學媒介語都是英文。
那些原本用華文學習史地和理科的學生,幾個月間要適應畢業考的新要求。那些本來用華文教學的老師,他們的職業道路同樣遭遇很大衝擊。
有時我也在想,在建國不過十幾年的時間裡,社會怎樣在短時間找到共識?那些被犧牲的一代人,具備怎樣的韌性?那些傷害怎樣癒合?
我們必須從歷史中走出來,繼續向前。
今天看起來,那些犧牲,換取了國家成功培養能夠掌握好英語的年輕一代。這樣做的結果,是讓整個社會正視英文的學習。人們都向務實主義傾斜。因此,所謂的「雙語教育」,是英文高頻率和高水準使用,華文則是普及了,不過平均水平線也被拉低,而且是拉得相當低。
揮別千辛萬苦,彈指繼續向前
前總理李光耀重視華文教學,自己領導改革。他不贊成華文學習的死背硬記,甚至不認為應該太看重寫字,因為這些都增加華文學習的難度。他總是堅持科技會解決一些問題,而我們則是認為華文的學習不是他想的那樣。
我們各自擔憂了好些年,「中國崛起」給了憂心語言文化無法傳承的年長者們,帶來新希望。人們等待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希望年輕一代會自己找到動力。
這兩年,我自己再重新審視那段曾經血流成河的歷史,對於語文的學習和發展更加迷茫。什麼語種、學習新語言的動力、什麼樣的教學法,或許都不再是關鍵。把語言當工具,如李先生所預料,科技不僅解決一些問題,也在改變很多使用的習慣。
日後我們再談語言時,指的或許不再是華語相對於英語,而是人工智慧的語言怎麼學習和應用。科技教我們如何學習,也教我們如何遺忘。
個人在歷史中曾經經歷的千辛萬苦,在大潮的衝擊下終將灰飛煙滅。以後的科技,灰也不飛了,就是一彈指,我們繼續向前。
(作者為新加坡新報業媒體華文媒體集團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