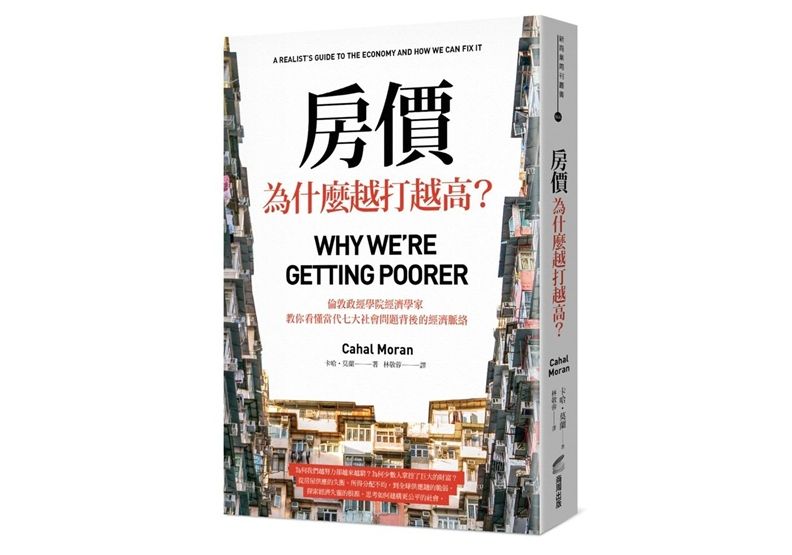德國的自有住宅比例最低,大約是50%,柏林的自有住宅比例更是只有15%。相較之下,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自有住宅比例大約是3分之2。儘管德國的私人租房比例較高,甚至富裕人士也普遍選擇租房,但這並不意味著租房者處於劣勢。(本文節錄自《房價為什麼越打越高?》一書,作者:卡哈‧莫蘭,商周出版,以下為摘文。)
以德國、荷蘭等國家為例,大部分的人都是跟私人房東租房子。看過英美市場的情況之後,你可能會認為德國、荷蘭這種模式會導致更高的住房成本,但事實恰恰相反──這些國家的房價和租金相對更穩定,許多居民即便沒有自己的房子,仍然能夠享有穩定的住房。當然,這些國家也有自己的住房問題,但整體而言,租房者的處境比英美地區穩定得多。
獲得住宅資源並不在於是否擁有
其實,獲得住宅資源並不在於是否擁有,這些國家認真看待這個事實。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富裕國家組成的機構)成員國當中,德國的自有住宅比例最低,大約是50%,柏林的自有住宅比例更是只有15%。相較之下,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自有住宅比例大約是3分之2。
儘管德國的私人租房比例較高,甚至富裕人士也普遍選擇租房,但這並不意味著租房者處於劣勢。相反,德國租房者享有多種法律保障,包含租金管制和免遭驅逐等等。柏林的房東通常不會把房租調漲到超過前任房客支付的金額。
加拿大、西班牙、荷蘭以及美國某幾州也採用相似的政策。雖然租金管制在經濟學界一直存在著爭議,但它確實挑戰了我們對「擁有住房」的傳統觀念。
盲目追求自有住宅可能會把財富(房子的價值)誤認為取得住宅的管道。經濟學家喬許.曼森(Josh Mason)指出,由於英美國家的民眾將大部分的財富投注於房產,所以統計數據可能會讓人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德國或荷蘭民眾比英美兩國的人民「窮」,僅僅因為他們的房產市值較低。
但這麼做就好比只是在看資產負債表,卻忽略了住房可得性的實際情況(譯註:這裡的「實際情況」[concrete reality]還巧妙地雙關了建築材料「混凝土」[concrete])。事實上,德國房客的住宅保障跟英國屋主不相上下,很多人也因此並沒有買房子的意願。
這些國家的經驗似乎證明了一點:一個受到良好監管的租賃市場,確實可以成為解決住房問題的一種可行方案。但是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些嚴格保護措施會讓房東陷入困境。他們主張,如果出租房子變得更難又更花錢,那麼房東投資房屋或者出租房子的意願可能會降低。
由於房租飆升,柏林在2020年推出非常嚴格的租金管制政策──事實上,大約一年之後,這項政策嚴格到被判定違憲。政策生效期間,房租確實變低了(柏林83%的家庭選擇租房子),但同時,大量房東選擇撤出租賃市場,導致空置率驟降,進一步加劇了住房供應短缺。
全球大部分的租金管制政策都比柏林更寬鬆
舉例來說,如果房東替房子進行了大整修,某些國家的政策允許房東可以提高租金。這是很合理的政策調整,確保租金調漲與住宅品質提升相配。
所謂的二代租金管制也會排除新建住宅;證據顯示,這種更靈活的租金管制並不會減少新建住宅的數量。這種管制應視為「租金穩定」的表現,因為它保護現有房客,避免房東在並未改善房屋的情況下,突然調漲房租。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政策並不會減少總住房數量,有的給租金管制公寓的房客居住,有的被房東賣給新屋主。正如住宅經濟學家卡麥隆.穆雷(Cameron Murray)強調,房東把房子賣給首次購屋族可以說是租金管制最理想的結果;若房東把房子賣給其他房東,只是所有權變更而已,房屋並未因此消失,也不會減少市場上的可用住房數量。
一項研究顯示,美國麻州劍橋市於1995年廢除租金管制後,對住房供應的影響微乎其微。雖然房東面臨的管制變少了,但是建設熱潮並未出現。然而,之前受到管制的住宅價格和租金均大幅調漲,受管制的房屋價格與租金大幅上漲,許多原本能負擔租金的人被市場淘汰,被迫搬離。
不過,房東確實選擇出租更多房屋,而非囤積或出售,使得市場上的可租房源略有增加。房東也對現有房產的維護投入略有提升,對市場品質帶來一定的改善。
平心而論,這些政策的結果相當複雜,並不能簡單地判斷其好壞,房價上漲究竟是好是壞,往往取決於你是租房者還是房主。
這種更靈活的租金管制的主要隱憂是,它創造出兩極化的房市:有的人享有保障,其他人卻因市場缺乏保障且租金調漲,導致他們不得不搬遷。
在舊金山,租金管制政策導致受管制的公寓數量減少15%,有的房東選擇賣房,有的選擇花錢整修,這樣就能用更高的價格出租公寓。
一項著名的研究發現,受租金管制保護的租戶獲得的好處,與未受保護租戶因高房租承擔的額外成本幾乎相等。換句話說,這種政策的「得益者」與「受害者」基本相互抵消,因此它的影響並不單純是好或壞,而是取決於政策取向。
最終,這是一場價值選擇──我們是要優先保護現有租戶,還是鼓勵更多新住房進入市場?
(延伸閱讀│美國福利規模高居全球第2,所得前1%富人卻比中產階級享更多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