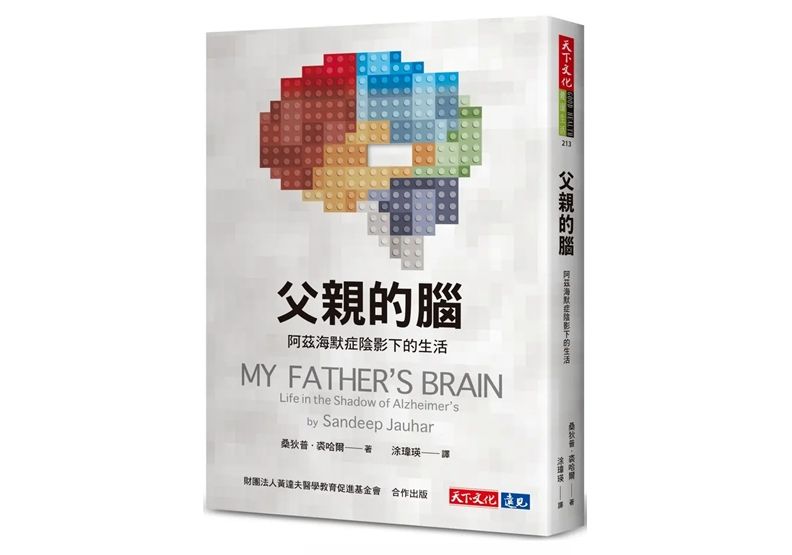喪偶和社交孤立狀態下產生的慢性壓力會對腦部功能造成劇烈損傷。研究結果顯示,父親的社交孤立可能不僅是失智症的後果,也是失智症的成因。心理狀態可能反映腦部損傷,但也可能導致腦部損傷。遺憾的是,導致父親變得孤立的惡性社會心理也來自他的家庭。(本文節錄自《父親的腦》一書,作者:桑狄普.裘哈爾,天下文化出版,以下為摘文。)
誰偷走了我的父親?失智症的殘酷真相
阿茲海默症經常分成7個階段。父親在 2014 年夏天搬到長島時,處於第3階段(輕微衰退)。這個階段的病人已經有認知障礙。
他可能無法像從前一樣勝任工作,或是可能忘記姓名或擺放個人物品的位置。儘管正式檢驗可以偵測到這種障礙,但家人的日常觀察往往無法辨別阿茲海默症和尋常的老年認知變化。
父親的病情從這個階段開始持續惡化。到了 2015 年和 2016 年之際的冬天,就在母親過世前,他的病情已經是第4階段,亦即中度失智症。
那時他已經明顯出現阿茲海默(或者更有可能是混合型)失智症的症狀:短期記憶喪失;無法管理財務或支付帳單。他開始忘記自身經歷的重要細節。
母親過世後的幾個月內,他就達到第5階段(中度至重度失智症)。失去人生伴侶後又陷入社交孤立,無疑加速他的衰退。
第5階段的病人開始需要有人幫忙進行大多數日常活動。他們很難穿著得體,而且往往無法獨自出門散步,因為他們會迷路。病人也可能出現偏執妄想和定向障礙。
父親對我們三兄妹的動機感到猜疑,特別是在財務方面。他也對自己遇到的困難和日常協助的需求完全缺乏病識感。然而,他依然能夠進行日常生活的基本活動,例如獨立洗澡及如廁。最重要的是,他仍然認得自己的家人。
他摔倒並住院之後,很快進入第6階段。在這個階段,他需要有人持續監護。有時他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哪裡。看照片時,除了最親近的朋友和親戚之外,他無法認得照片上的其他人。
只要天色暗下來,他就去睡覺,這或許是因為控制睡眠清醒週期的腦部中樞已經受損。他也開始出現尿失禁的症狀,夜間頻繁尿床,所以需要穿尿布。
到了 2020 年秋天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他開始會遊走。這是腦部退化帶來的結果,大多數失智症病人最後都會出現遊走行為,但我不禁會想,他一直想去其他地方的渴望也反映出他很懷念從前自己能夠獨立生活的時光。
雖然到長島定居,與兒子住得很近,但他從未快樂過。他為自己和母親制定的晚年計畫已經分崩離析。儘管他生性謹慎、善於預測又富有遠見,但即使是他也料想不到自己的身體和心智衰退過程,或是自己的子女會改變這麼多,無法遵守我們曾立下的承諾。
第7階段是阿茲海默症的最終階段,這個階段的病人基本上在日常生活的每個層面都需要幫助。他們失去對周遭環境做出反應的能力。
他們往往也失去吞嚥或控制口腔分泌物的能力。他們很難站起身,所以會發生褥瘡和泌尿道感染;或者他們會摔倒並骨折,然後臥床不起及染上肺炎。
我經常想起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戴伊醫師跟我說的話。「所有失智症在最終階段看起來都很像。」他當時說:「整個腦部都會受到影響。病人通常都沒辦法講話了。」
末期失能的最終順序似乎與幼童最初發展里程碑的順序顛倒。隨著腦部最基本的神經網路逐漸抹去消失,這樣的失能順序也符合我們的預期。
正如大衛.申克(David Shenk)在文筆精湛的著作《逐漸遺忘》(The Forgetting)中寫道:「阿茲海默症破壞腦部的順序幾乎恰好與腦部從出生起發展的順序顛倒。」起初,病人無法再獨立行走,然後他們不再能獨立坐起身。接著,他們失去微笑的能力,最後他們無法舉起自己的手。
(延伸閱讀│家中長輩若失智,如何保護財產?辦理「金融註記」的4個流程)
一個家庭對失智父親的殘酷真相:我們有多殘忍?
悲傷的是,失智症病人經常面臨的社交孤立,與認知功能加速衰退有關。
母親過世的幾個月後,我讀到一篇 2007 年發表於《普通精神病學檔案》的論文〈阿茲海默症的孤獨與風險〉,這篇論文從芝加哥及周邊地區的教會、社會服務機構、老人福利機構招募823 名起初未罹患失智症的人進行研究。
為評估孤獨程度,研究人員要求參與者填寫列有 5 題的問卷,回答是否同意問卷陳述,例如「我想念有人在身邊」、「我經常覺得遭到拋棄」、「我想念擁有非常要好的朋友」。
參與者也接受其他方面的評估:與社交網路互動的頻率、從事運動或參加認知刺激活動(例如閱讀)的頻率、說自己感到悲傷或憂鬱的頻率。
他們的認知功能由訓練有素的精神科醫師定期評估。過世的參與者會接受屍體剖檢以評估腦部受損程度,包括中風、類澱粉蛋白斑塊、tau 蛋白纏結。
研究人員發現,在 76 名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受試者中,即使認知活動和體能活動大致相同,但最孤獨的人罹患此病的風險依然比擁有最多社會支持的人高出1倍。這種關聯不受種族、收入、失能程度或血管風險因子是否存在所影響。
研究人員得出結論,神經病變不是臨床阿茲海默症的唯一誘因。當然,這項研究存在限制,包括參與者主要是白人,而且觀察時間平均只有 3 年。儘管如此,研究結論仍不可忽視:社交活動頻率增加與失智症風險降低有關。
屍體剖檢研究跟上述研究結果一致,同樣顯示腦部損傷(亦即斑塊和纏結量)與臨床失智症程度的相關性並未如原本預期般那麼高。腦部僅有少量損傷的病人往往有與神經障礙不成比例的「過度失能」。反之亦然:有大量斑塊和纏結的病人可能有出奇完好的認知功能。
對於這種偏差,常見的解釋為「認知儲備」,包括較高的教育水準、發病前的智力等,但鮮少有人承認「心理社會儲備」(psychosocial reserve)的重要作用,包括人際關係、環境、家庭支持。目前已有研究顯示,心理社會儲備的影響可能與神經病變同樣重要。
父親在母親過世後經歷的孤獨可說是帶來特別大的傷害。在 2020 年一篇發表於《美國醫學會期刊》的論文中,哈佛腦部老化研究(Harvard Aging Brain Study)的研究人員對 257 名沒有認知障礙的男女進行試驗。透過正子斷層造影掃描判定,這些人的腦部都有高密度的β類澱粉蛋白斑塊。
依據年齡、性別、社經地位、類澱粉蛋白濃度等因素進行調整後,研究人員發現,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喪偶的參與者在 3 年內發生心智衰退的速度是未喪偶者的 3 倍。此外,基準點類澱粉蛋白斑塊濃度最高的喪偶參與者有最顯著的衰退幅度,表示喪偶加上類澱粉蛋白可能加劇認知障礙的風險。
我們確實早已知道,喪偶和社交孤立狀態下產生的慢性壓力會對腦部功能造成劇烈損傷。舉例來說,海馬體對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特別敏感:高濃度皮質醇可能干擾短期記憶及其轉為長期記憶的程序。
目前也有大鼠和人類研究顯示,重複暴露於壓力荷爾蒙會導致海馬體和前額葉皮質(負責控制工作記憶)萎縮及形成疤痕。這種壓力也可能誘使神經發炎並伴隨斑塊和纏結。
遺憾的是,導致父親變得孤立的惡性社會心理也來自他的家庭。我希望我能夠說,我們比外人更有耐心,但我們沒有。他腦中的蝕刻素描板將他困於永恆的當下,而他的子女則困於永恆的沮喪。
我希望我能夠忘記,我們在他發問時責備他的樣子,也希望能夠忘記,我們曾說過「告訴他也沒用,因為他記不住答案」這樣的話。
(延伸閱讀│「腦袋一團亂,我好怕」失智母親過世前書寫的20年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