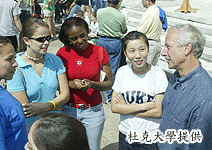中國宋氏王朝的傳奇,來自125年前宋耀如(Charlie Soong)的經歷。1881年,早在「全球化」這個字眼納入高等教育字典之前,宋耀如就進入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讀書,成為本校第一個外國學生。
宋耀如當時就讀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該學院稍後發展為杜克大學。當時,他的支持者希望他回大陸廣傳基督福音。但宋耀如歸國後,並未從事傳教工作,而是與家人共創宋氏王朝。
他的女兒宋慶齡嫁給孫逸仙,另一個女兒宋美齡成為蔣介石的妻子。兒子宋子文在哈佛大學畢業後曾任美國廣東銀行(Central Bank of Canton)總經理,也曾擔任中國的財政部長及行政院長。宋耀如從未忘記他的根源──他與祖國,以及他與美國的緊密關係,後者造就他,焠鍊他的才智和企圖心。
每個地點都納入全球網絡
今日與過去不同的地方在於,資訊迅速的流通,地球上的每一個地點都已被納入全球網絡。隨著經濟活動、科技進展、健康危機與安全威脅日益全球化,教育也亟需建立國際性的視野。
對帶領美國卓越研究型大學的我們來說,這件事帶來非常明顯的挑戰。我們努力找出方法,訓練年輕人迎向未來的全球化世界。同時,我們思考大學應如何因應這個趨勢,提供必需的教育、研究與發展,為了學生,也為了更廣闊的社會整體,提供適當的服務。
今日我們看到很多與宋耀如類似的人物,如杜克大學主導醫療保健的副校長與杜克大學醫療保健系統執行長曹文凱博士(Dr. Victor Dzau)。曹文凱出生於上海,早年定居香港。他在加拿大蒙特婁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到美國紐約醫院(New York Hospital)實習。現在,全球各地數以千計的學生,就像曹文凱一樣,仍選擇在美國接受進一步的教育。
今日,就像亞洲在製造業、奈米科技、生物學及其他領域躍居全球性的卓越地位,亞洲大學的國際地位也日益重要。跟許多其他部門一樣,高等教育逐漸成為一種全球性企業。
跨越地理界線的學習
不同的大學有不同的長處,基於共同利益而建立的策略性結盟,可讓大家都受惠於此一全球化環境。這是一個機會,讓全球各地的大學仔細思考──透過提供獎助學金,發展支持外國申請者的作法,以及合作推動簽證與研究安全方面的政策,能反映出大學在促進知識發展眾多領域中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其中以科學、科技和醫療保健等領域的角色最為重要。
同時,我們必須找出方法,為我們的學生與學者增加國際性接觸的機會。例如與其他大學及相關院校結盟,讓學生與學者能夠跨越地理界線,一同學習和進行研究。
我們同意教育必須變得更加全球化,而我們也必須思考自身在市場上有哪些策略性優勢。
在亞洲,大學生通常會選擇一個領域,然後專心努力地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但大多數美國的大學,尤其是杜克大學,採取不同作法。
在杜克大學,我們要求學生探索人文科目、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除此之外,也鼓勵學生與學者跨越傳統界線,從新的角度來思考,過去認為專屬某一領域的問題。
我們強調運用學術性的探索,來面對真實世界的挑戰。
這些作法究竟有什麼意義?
團隊合作達成知識整合
在追求知識突破的過程中,專門化的科系雖仍扮演關鍵性角色,但卻不足以因應今日社會極度複雜的種種問題。例如,醫療保健問題的解決方案,就必須同時考慮包含醫學、文化、經濟與政策層面。
在一個面臨多重挑戰的時代裡,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必須具備整合迥異知識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經由可以預先學會的既定公式,而是透過臨場反應,掌握時機,隨時針對一連串不斷改變的事實和資源而進行調整。
當許多問題需要分享與聚匯的領悟,團隊合作成為知識整合的最大特色。未來社會中,借重他人不同專長的知識,用以補自己之不足,這種能力將變得愈來愈重要。
杜克大學強調,大學生活是一段探索的時光,而不是沿著通往專業工作的軌道僵化地前進。人文教育不會讓學生變得更聰明,但會讓學生具備多重的能力與彈性,來因應不斷變遷的環境。
為了培養這種領悟力,我們的學生必須進修具有「跨文化」內涵的課程,他們可以在600多門具有國際意涵的課程中選課來修,或是在18種外語中選擇一種語言。
「神奇寶貝」也是課程
例如,艾莉森教授(Anne Allison)的文化人類學導論課程,談到動畫與「神奇寶貝」(Pokemon),幫助學生瞭解文化如何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傳播。劉康教授(Kang Liu)教導學生探索手機簡訊、卡拉OK與網際網路的知識,協助學生瞭解當代華人媒體。
我擔任杜克大學校長近兩年中,愈來愈把大學視為一個解決問題的地方。在這裡,我們可以用精妙的思想與強大的力量進行知性的探索,而不是讓大學變成一個擁有抽象專業技能、卻與外界隔絕的孤立空間。在這裡,聰明才智因真實世界的問題而爆出火花,才智的力量投注於嶄新的解決方案。
把學習和社會連結起來
杜克大學的各個角落──醫療保健、高齡化與環境政策等領域──學者與學生以卓越的方式,把他們的研究和課堂上的學習,與現代社會的挑戰連結在一起。本校的「尼可拉斯環境政策解決方案研究院」(Nicholas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Solutions)為學術性的科學與環境政策的決策者提供交流園地。像是醫學教授黃達夫(Andrew Huang)與杜克大學專精基因體研究(genomic research)的學者合作,進行乳癌研究。不過他大部分時間留在台北,在那裡,他擔任一家由他創立的重要癌症醫院的院長,這家醫院就是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去年春天,杜克大學醫學中心與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簽約,在新加坡合作成立一所新的醫學院。新加坡政府將在七年內提供3億1000萬美元做為建校費用,該校將仿照杜克醫學院,將臨床訓練與研究訓練融為一體。
新加坡政府希望推動當地成為醫學教育的領導中心,這項結盟也讓杜克大學擴展它的成果,有機會處理全球醫療面臨的多項挑戰。
讓我感到振奮的地方是,這項合作計畫不僅提供促進研究的機會,可能研發出具有開創性的新療法,也創造出一個新的醫學教育模式──分享研究結果,跨越國家界線的模式。
南亞海嘯讓學生學以致用
在這些全球性的互動中,並非每一種交流都有經驗豐富的教授參與,也不是每一種都包含高科技研究。如2004年12月印度洋發生海嘯後,杜克大學一群學習工程設計的學生,研究蘭加(Lamnga)居民的需求。蘭加是印尼的一個小漁村,南亞海嘯爆發前,當地經濟仰賴居民捕蝦的收入。
這群學生設計出一種低成本、低科技的增氧機(aerator),提高水中的含氧量,使得蝦的體積和產量開始增加。
這群學生待在印尼的期間,不斷調整設計的內容,好讓增氧機發揮適當功效。同時,在必須有翻譯人員在場、才能跟當地人通話的情況下,他們努力取得村民的信任。
最後,他們相信自己對這個社區提供了幫助,與當地人民建立了感情,他們自己則得到了實用的經驗。
這種包含廣泛人文教育基礎、鼓勵跨領域合作、強調解決問題的體系,對杜克大學來說效果不錯,但是有些人可能會感到懷疑。畢竟在美國雇用一位工程師,要比在孟加拉來得昂貴許多。一個注重節約成本的高階主管,怎麼會想要雇用一個在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杜克大學接受訓練的工程師,而不去雇用在印度接受訓練的另一個工程師?
就我們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學生在杜克大學接受訓練後,由於這種基礎廣闊的教育,他們的心智更有彈性,心中也充滿自信。隨著彈性而來的是創造力與迅速復原的能力──必須具備這種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們才能在面對眼前與未來的挑戰時,找出創新的解決方案。我相信教育的未來挑戰在這裡。
世界的未來無法預見
過去五年中,杜克大學的全球化以許多形式呈現。本校大學部約有6%為外國學生;在研究生方面,外國學生占所有研究生的1/3。
我們大學部學生約有半數到外國讀書──這個比例超過美國大多數類似的機構。此外,許多學生在國外進行獨立研究,如熊谷(Nicholas Shungu)在南非一間診所擔任實習醫師;古德曼(Maital Guttman)到以色列拍攝紀錄片,探討以色列青少年剛開始服兵役的體驗。
同時,我們的老師們在國外做研究時,會帶著學生一起去。以生物學教授布萊佛蔓(Sherryl Broverman)為例,她的愛滋病研究把她帶到肯亞;社會學教授葛瑞佛(Gary Gereffi)的商品鏈研究把他帶到東亞、墨西哥與加勒比海地區;史學教授庫安茲(Claudia Koonz)則到德國對回教徒進行研究。
未來,我們將繼續尋找新方法,讓學生在杜克大學念書的期間,得到實在的國際經驗。
但是五年或十年後的大學會是什麼模樣?我們認為,大學的角色應是幫助學生做好準備,不僅為了得到一份值得尊敬的工作,也為了經營一個值得尊敬的生活。
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拓展學生的知識,加深他們的領悟,幫助他們做好準備,成為全球公民,而這個世界的未來為他們所無法預見。
杜克大學無法獨立完成這件事。畢竟,國際化教育的未來,需要許多高等教育的領導人、決策者與企業高階主管通力合作。(汪芸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