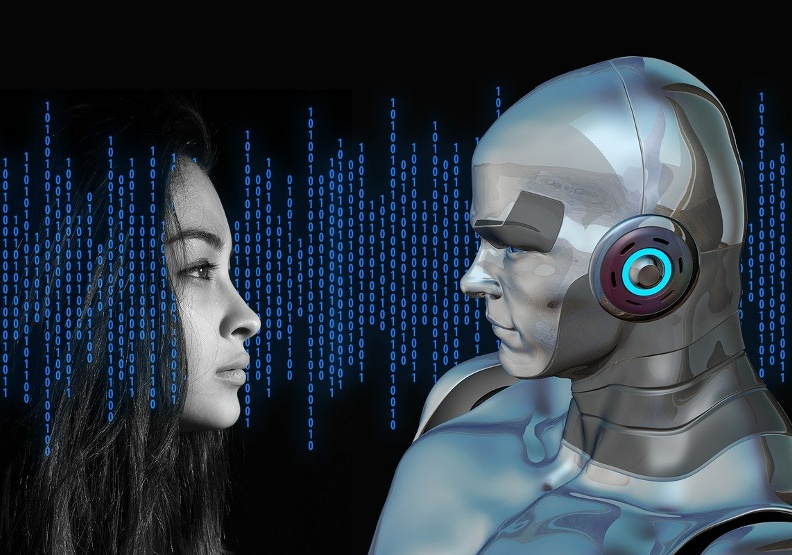這本《AI科學家李飛飛的視界之旅》非常好看,講述一位15歲的中國女孩移民到美國念高一,在短短三年之內,克服了語言上的困難,進入了普林斯頓大學,成為AI這個新領域的佼佼者,最後被邀請到美國國會去聽證的故事,非常值得推薦給不分年齡和專業的讀者們細讀,因為不但內容振奮人心,作者對機器與人的關係更是句句發人深省。AI的目的是為人類服務,但如何造福人類而不造禍人類,我們要謹慎的去思考AI的未來。
AI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誠如作者所說,企業只會用人才,不會去塑造人才,所以人才的培育要靠國家。台灣沒有天然資源,人才正是我們國家的命脈,可是到現在,除了選舉時,政府撒錢補助學費住宿,沒有看到任何有效的培養計畫。台灣有能力的孩子其實很多,假如當年李飛飛是來到台灣而不是美國,她還會有同樣的成就嗎?我們要給我們的孩子什麼樣的支持和研究環境,他們才能像李飛飛一樣一飛沖天?
我們先來看一下本書的特點,再來談一下他山之石如何可以攻錯。
一本好的科普書內容必須深入淺出,使沒有專業背景的人也能了解,所以通常由研發這個領域的科學家親自來撰寫,最能達到這個目的,因為只有真正懂的人,才能夠簡單扼要的把內容說出來,而不用專業術語去唬人。人工智能(AI)是目前的當紅炸子雞,因此,這個領域的研發過程,最能引起讀者的好奇心:它是怎麼起源的,又怎麼一步一步走到現在這個無所不在的地步的?如果我在作者的位子上,我會有這個想法嗎?我會有像作者這樣的毅力,去把理念實現出來嗎?這是本書最值得推薦的地方,「從收穫問耕耘」,從她成功的經驗來檢討台灣年輕人如何也能「有為者亦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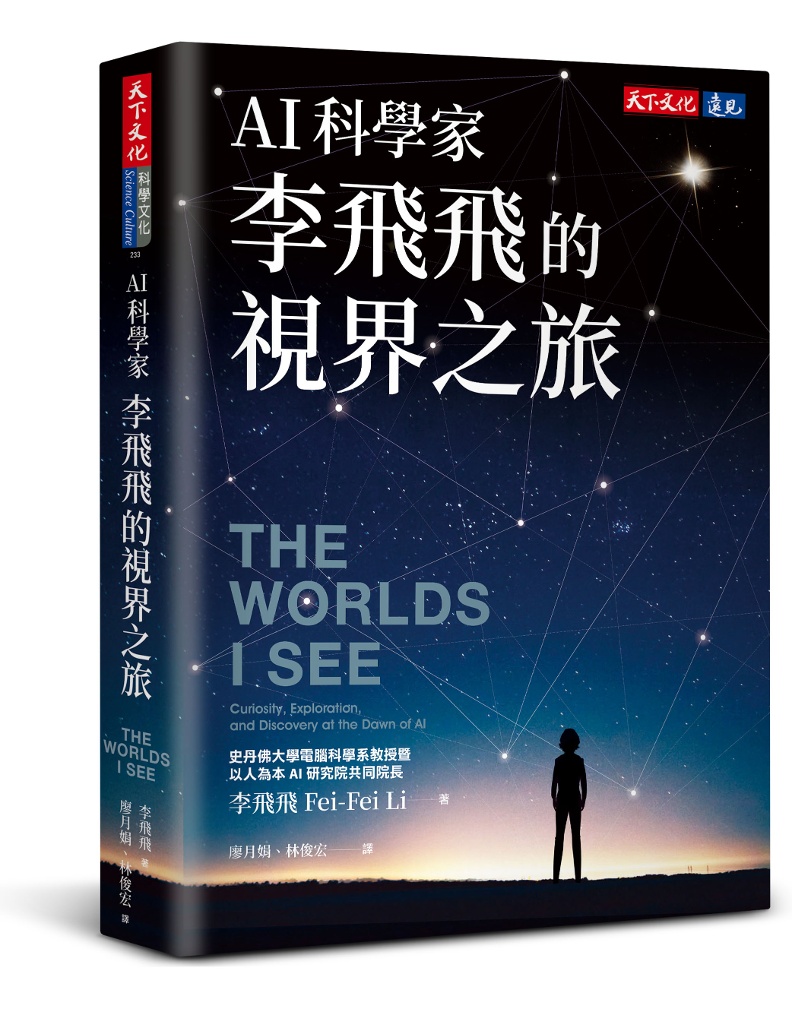
強調背景知識的重要,吸收新知最快的方式是聽演講
在書中,作者強調背景知識的重要性,她更說明聽演講是吸收新知最快的方式,因為一個小時的演講,講者至少要準備三個小時,沒有比聽一場演講更容易抓住新知的方式(這一點台灣學生不了解,每次邀請大師來演講,主辦單位最頭痛的事,便是找學生去充場面)。書中有很多例子,都說明了她在聽演講時,發現別人的研究可以幫助她更上一層樓,她便立刻去找那位講者談,加入他的研究團隊,或請他加入自己的團隊,集思才能廣益。學術需要交流,殊途同歸,不同的實驗室得到相同的結果,是證實一個理論最有力的方式。
AI起源於1956年夏天在達特茅斯學院的一個會議(不要因為它是college而小看它,它是長春藤盟校之一,這所學校人才濟濟,在學術界有崇高的地位),那是第一次,訊息處理學家(Information Processing)、心理學家、電子計算機學家,凡是跟人類行為有關的各領域頂尖學者,聚集在一起,討論人類如何學習,機器人又如何模擬人類的學習方式,為人類處理一些機械性的例行作業,減少人類的負擔。會中大膽地討論了大腦的認知功能,因為人如何辨識外界的物體,跟大腦有絕對的關係,行為主義不允許討論大腦(他們叫做「黑盒子」)是不對的,人類的學習絕對不只是刺激和反應而已。
其實,1956年那場會議也是認知心理學的起源,在那會議之前,行為主義幾乎壟斷了整個心理學界,論文如果沒有提到刺激→反應,就不被期刊接受。即使到了1970年代,我在加州大學心理所時,史金納的「工具學習」(Operant Conditioning)仍是必修課,而且學分很重。幸好,即使在行為主義獨霸美國心理學界的時候,生理學(Physiology)的必修地位也一直不曾動搖。神經生理學是研究大腦的結構和功能,從而了解人類怎麼看見東西、耳朵怎麼辨識語句,我們必修的視覺生理學,就是以Hubel和Wiesel的貓視神經實驗為主,這個實驗打下了AI Patten recognition的基礎。
教機器如何辨識外界物體,一定要先知道人怎麼辨識物體
在60年代初期,哈佛大學的Hubel和Wiesel,把貓的後腦殼打開,在視覺皮質的細胞上插了探針,給貓看直線或橫線的幻燈片,想知道視覺細胞的功能,他們持續放了千百次幻燈片,那些神經元都沒有活化,一直到幻燈片不堪使用,中間裂開成斜線時,這些神經元就瘋狂地活化起來了。Hubel和Wiesel才明瞭,原來視覺皮質上的每個神經元都各有所司,有的管直線,有的管橫線,有的管斜線,它們是分工合作,每個細胞將自己辨識出來的資訊,送往上更上一層的細胞去做整合,最後綜合所有的訊息,大腦做出這是什麼東西的判斷(這就是Pattern recognition)。這個破天荒的發現,使他們得到1981年的諾貝爾獎,也開始了AI辨識物體和人臉之路。
前面說過研發AI的目的是替人類工作,幫助人類處理例行的工作,所以要教機器如何辨識外界物體一定要先知道人怎麼辨識物體。書中提到的心理學家畢德曼(I. Biederman),他1973年那篇論文是當時加州大學研究生必讀的一篇,因為他把構成物體的元素分離出來,讓後來的電腦學家可以用這些元素去教電腦辨識物體。我對他的研究印象深刻,是因為在醫院中,我看到有病人頂葉受傷以後,他可以從圖片中辨識物體,但假如拍攝的方式是鳥瞰,即從上往下照,即使是杯子、茶壺這種每天都用到的生活用品,他就不認得了。為什麼會這樣呢?構成這個杯子的基本元素不管怎麼拍,應該都是同樣的,為什麼角度不一樣就認不得了呢?我就是因此從認知心理學,走進神經心理學的。
這本書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除了作者本身非常不一樣的人生經歷之外,書章節的編排,也非常符合神經心理學的理論,本書各章節是AI主題與作者生活經驗交織呈現,這個交錯的道理,就是我們課堂安排為什麼要國文、英文、數學穿插著上,而不是一次上滿三個小時的國文課,因為我們大腦的本質是喜新厭舊,對同樣的主題會厭倦(因此有「入鮑魚之肆,久聞而不知其臭」的現象,對熟悉的刺激不再處理),而維持注意力的正腎上腺素,專門對新奇的東西敏感的神經傳導物質,因此,國文上了50分鐘,當大腦對這個主題感到疲勞,失去注意力時,就要換英文來上,實驗上叫「release from proactive inhibition」,從前項的干擾中解脫出來。本書的編輯大學時應有好好的上過「普通心理學」(Psychology)的課,當年的所學,如今用在這裡了。
科學離不開人性,科學必須以人為本
最後來談一下我們該怎麼面對這個日新月異的新科技。AI,尤其是生成性(generative)是未來的趨勢,父母擋不住,也不必擋,我們的態度是如何運用它來幫助孩子學習得更好。這一點,全世界的教育者正在摸索如何「雙贏」。但有一個倫理方面的問題,是很多工程師避開不談,而作者茲茲在念的,那就是AI的倫理問題。作者從親身經歷,指出它對人類未來的影響——「AI4ALL」(念成「AI for ALL」,取自玻璃絲襪剛上市時的廣告one size for all)。現在拜手機之賜,所有的生活領城都離不開AI,但是它只是個技術,是個冷冰冰沒有靈魂的東西。愛因斯坦曾說「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把「宗教」這兩個字換為「倫理」,就是本書作者的重點,科學離不開人性,科學必須以人為本(Human-centered),機器如何對待人,保留人的尊嚴,是在大量開發機器人時,一個不能忘記的重點。再怎麼會伺候人的機器,是沒有「心」的,而這個「心」,正是人成為人最可貴的地方。
從AI的快速進展中,我們愈發了解「倫理道德」的重要性,在「搜孤救孤」這個歷史故事中,壯士鉗麑奉屠岸賈之命去刺殺趙盾,但是他看到趙盾天未亮,便已穿好朝服在等待上朝,便不忍殺害一個忠心為國的大臣。但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屠岸賈的命令他不能不去執行,而他自己的良心使他下不了手,在工作指令與良心道德衝突的時候,他選擇了自撞槐樹而死。我們要問:當一個機器人一切都像人類,會看、會聽、會說,可以執行命令到最後一個字母時,如果他沒有良心,不能做出像鉗麑這樣的道德判斷時,這個世界會是什麼樣?
一本好的書就像一個好的法律,它會引導社會前進,本書值得生活在21世紀中葉的每一個人,細細思量AI世界的未來,因為它跟你我的命運息息相關。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台北醫學大學、中央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