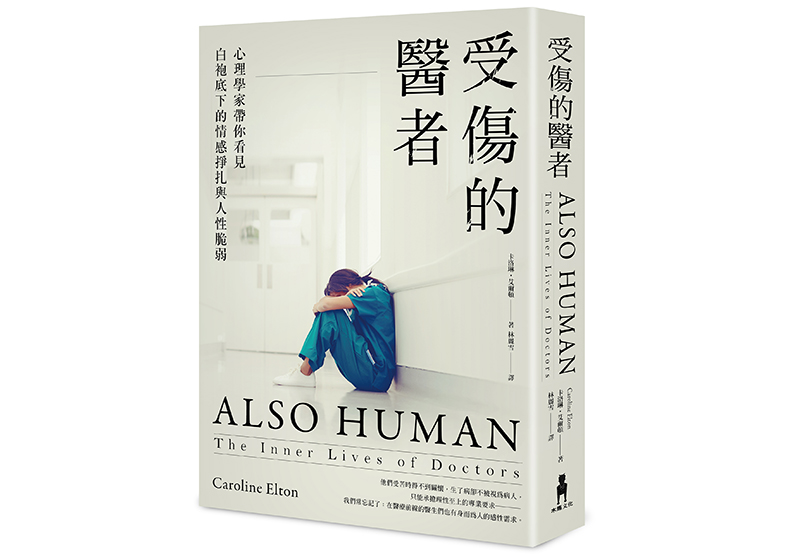編按:病患為什麼總是而且永遠都可能激發醫生痛苦的感覺,最大的理由是,他們必然會讓醫生想起,他們和那些他們所愛的人都會死。(本文摘自《受傷的醫者》一書,作者為卡洛琳‧艾爾頓,以下為摘文。)
我們對醫療工作心理要求的了解不足
如果不是醫療科學的進步,我母親在我出生時就會過世。她是英國第一批再生不良性貧血被治療成功的人,那是一種懷孕後期才出現的血液疾病。因此,在我的生命開始的頭幾個星期,她能否存活下來,是很不確定的。1/4個世紀以後,我父親罹患骨髓癌, 這是一種骨髓方面的癌症。雖然最後他死於這個疾病,但是化療讓他的性命延長了7年多。
醫療科學在20世紀的進步是非凡的,並且持續到21世紀。大部分被我們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例如白喉、破傷風和百日咳,這些疾病以前曾經是孩童殺手,到了1920年代才發展出疫苗,到了現在,我的孫子在八週大時就會接受這些疫苗的注射。小兒麻痺疫苗的發現則比較晚,是在1950年代。我懷孕時才出現超音波掃描胎兒的技術,但現在已經可以對子宮內的胎兒進行外科手術。
去年,我有一個60歲出頭的好友,因為原發性硬化性膽道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而接受移植手術,那是一種相當罕見的慢性肝病,捐贈者是他23歲的兒子,他捐給父親61%的肝臟。如果沒有這個手術,我的朋友就會死於肝功能衰竭。他的兒子已經完全康復了,而我朋友的情況也很好,只是他終生都必須服用免疫抑制劑,以免自己的免疫系統排斥兒子的肝臟。
我不是一個醫學的盧德分子(Luddite,按:反對技術革新的人),就是那些反對或蔑視21世紀醫學成就的人。但現實是,一方面是醫療實務的長足進步,另一方面是我們對醫療工作心理要求的了解,這兩者之間存在著驚人的隔閡。
在1950年代,小兒科醫生和心理分析師唐諾.溫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認知到,父母對小孩的感覺不是永遠都是好的。
假如他今天還活著,對於醫生有時會憎惡,或甚至仇恨病患,我很想知道,他會直覺地舉出什麼樣的理由。或許他列出來的會包括:
害怕犯下重大錯誤
時間的壓力;短時間要看太多的病患
對於診斷或是診療計畫感到不確定
當病患的疾病不能治癒時,對自己的專業感到無能
病患對現代醫學所能達成的效果,有不切實際的期待
害怕成為投訴或法律訴訟的對象
整個值班時間都在工作,沒有休息,又餓又渴
收到病患貶損的評論
厭惡人體的衰敗和殘缺
害怕接觸傳染原
蔑視病患因自身行為所造成的傷害
必須在某個和家人與朋友分離的地方工作
因為必須工作而錯過了一個特別的家庭慶祝活動
醫生也必須應付醫療工作的不可預測性和不確定性。在醫學裡,一個特定的疾病在兩個病患身上,可能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現,而且一個人對特定的療程可能會有反應,另一個人可能不會。這種不可預測性對一些醫生形成沉重的負擔,這是本書中為什麼有這麼多醫生在職涯中遇到困難的一個常見原因。

在意感染風險與在意醫生情緒健康,同等重要
150年前,外科醫生約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發表了利用消毒劑降低術後感染風險的發現。李斯特提倡,使用石碳酸消毒外科醫生的雙手、器材、傷口,甚至病患周遭的空氣。採用這些簡單的措施時,病患在截肢手術後的存活率從55%提升到85%。
但是即使有了這些卓越的成果,其他同仁並沒有立即採用李斯特的石碳酸方法;他們覺得這很複雜,也花時間,還辯稱這個結果實際上是因為其他的變化,例如醫院的通風改善了。
那時是1867年。現在,醫療實務中的每一個層面都知道感染控制的重要性,例如,全科醫生檢查病患後,會在診療室清洗雙手;對免疫抑制病患施行屏障式護理:隔離全部病房,以控制醫院感染的爆發;甚至是控制流行病爆發的全國計畫。除此之外,現代醫學的很多成就是取決於控制傳染散布,以及當其發生時,有效對付它的能力。像活體肝臟移植這樣的手術,如果捐贈者與宿主的術後感染風險不能降到最低,就不可能成功。
只要花一點點時間想像一下,如果醫療人力〈以及更廣泛的健康照護人力)的情緒健康被賦予和感染控制相同的重要性,換句話說,就是把情緒問題看得和感染問題一樣重要。
在李斯特的時代,45%的病患死於截肢後感染。現在,有一些報告指出,超過50%的醫生曾經有過過勞,基於過勞(以及憂鬱和自殺)的程度,很難宣稱我們沒有重大的公共衛生危機要處理。這樣的比較真的會很怪異嗎?
情緒韌性必須從個人、組織和整體醫學文化著手
這個比較也讓我們注意到沒有簡單和單一的解決方法。醫院裡的感染控制不只是在廁所裡張貼海報說「現在要清洗雙手」。當然不是。然而,當我走進一所倫敦教學醫院的教育中心,看見一個用磚塊圖案紙張遮蓋著的布告欄,頂端的標題是「韌性牆」〈resilience wall)時,得知院方鼓勵職員用立可貼張貼積極向上的意見〈如果感到壓力,我會深呼吸;我會在午餐時間到外面呼吸新鮮空氣)。全部都是好的想法,但是韌性牆對醫生健康產生重大影響的可能性,就和磚塊圖案紙張承受建築物重量的可能性一樣大。
嘗試培養醫生情緒韌性的問題(而且有很多)是,他們把責任歸於個人。這個方法是有缺失的,如同最近《英國醫學期刊》有篇文章的作者指出:
這就是我們在本書所看到的。在個人的層次,很清楚的是,有些被挑選出來進入醫學體系的人,永遠沒有辦法當得了醫生;有些醫生選擇某個專科,是出於一種無意識的企圖,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個人衝突,因此在醫生私人生活裡持續發生的事件,可能會影響他們對工作的感覺。然後,這些個人因素會和組織因素相互影響,例如,制度性的「從錯誤到失敗」現象;逆向照顧法則,也就是最需要支持的人結果卻得到最少的照顧;多年來資金不足的壓力;非常缺乏對職業轉換的關心;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具破壞性的力量。因此,由於不願意採用以證據為基礎的教學方式,也傾向否認醫生本身出現的任何脆弱徵兆而將責任歸於個人,整個醫學文化就像將這個體系鬆散結合在一起的膠水。
如果其中出現裂縫會是奇怪的事嗎?
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就是不會有簡單的答案。改善醫療人力的情緒健康需要從三個相互關聯的層次著手,個人、組織和整體醫學文化。
由於問題的規模很大,很容易令人灰心。但是,如同我們在本書看到的,在世界各地,都有閃爍著微光的希望。麥可.法夸爾的睡眠宣導需要從倫敦散布到英國各地,然後是世界其他地方。醫生利用臨床知識不只讓病患受益,還有其他的醫生,這是少見的例子。很多國家可以向紐西蘭學習,引進一年的受訓實習作法,以協助醫學生過度到臨床實務的轉換。說到開放醫療訓練機會給身體殘障人士,加拿大和美國比英國還要開明;另外,史瓦茲會談活動在北美和英國的成長也令人鼓舞。美國的醫學院則示範了,當整個組織上下都投入對多元化的承諾時,可以得到什麼樣的成就,在這種情形下,美國的實習醫生可以得到職業支持單位〈Professional Support Unit)的服務,就像是我在倫敦工作的地方。
或許在150年後,對醫生情緒健康的關心,會和目前對感染控制的程度一致。
或許當歷史學家回顧我們在2018年如何對待醫生時,對我們目前醫療體系的看法,和閱讀到李斯特年代的醫生,拒絕在診治不同病患之間洗手時,會有相同的恐懼。或許在150年後,社會大眾將會了解,雖然這個工作的要求非比尋常,但肩負醫生角色的人就和他們的父母一樣,其實他們也是人。
或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