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的研究指出,「情緒表達抑制」並不是一個有效的策略,甚至會對一個人的心理建設、社會適應帶來負面影響。白話來說,就是壓抑情緒對你的心理健康並不好。
然而,「文化」扮演了關鍵影響因素。在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中,情緒表達抑制發揮比較負面的作用,可能會與消極情緒、社會焦慮、憂鬱症有關,甚至對心理彈性、社會適應、記憶等產生消極影響。
然而在東方「集體主義文化」中,使用「情緒表達抑制」,有時在人際關係、情緒體驗與心理及社會上的適應有較好的表現,並非完全是個不好的調節策略。
因為,在個人主義文化中,主流文化期待是「最大化積極情緒,最小化消極情緒」;然而在集體文化中,主流文化期待的是,經由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間的「平衡」來尋求一個「中庸之道」。此外,謙讓、克制、隱藏強烈情緒、保持冷靜,被認為是成功的積極表現。如果自由地表達消極情緒,可能造成「人際中斷」——這在集體文化中,被認為是不必要的結果。
白話地說,西方個人主義文化,重點是讓自己開心。東方集體主義文化,雖然也希望能讓自己開心,但更重視「人際和諧」,而為了人際和諧,必須壓抑自己的情緒,以適應主流文化期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或身邊的許多人,是不是常常開心的時候不能太開心,難過的時候不能太難過,生氣的時候不能太生氣,普遍處於一種有點「壓抑」的狀態?
由此衍生出來,我們還有幾個特殊的現象:習慣委屈、台灣阿信、老二哲學。
1.習慣委屈
「委屈」是在華人文化中,很特別的一種情緒。在英文中,並沒有能夠精準表達「委屈」的詞彙。
「委屈」,不只是被誤會、被不公平地對待,更有一種「想說的話不能說」、「想表達的情緒沒辦法自在地表達」,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這種很悶憋的感覺,正是前面提到的「情緒表達抑制」,而委屈之感,常常是因為自己明明覺得不公平,但礙於尊師重道,礙於表達情緒會被討厭,所以硬是把情緒吞忍下來。
但更無奈的,其實不是「委屈」,而是習慣委屈的「習慣」這兩個字。
很多人遇到習慣委屈的人,總會說:「你就說出來啊,你不說,我怎麼知道你過得不好。」但很多時候,「習慣委屈」自己的人,很多時候甚至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委屈」的。
我有位個案曾經無奈地說:「我知道你說的『不要委屈自己』,可是我已經配合別人好久,把自己藏起來幾十年了。我已經分不清楚,我到底有沒有不小心犧牲、委屈了自己……」
聽到他這麼說,感覺真的很悲傷。
你可以想像一個孩子,把自己的身體瑟縮起來,只怕自己太張揚自己,會變成別人的麻煩,會被別人討厭。即使身體長大了,卻不知道自己其實可以不用這麼卑躬屈膝地活,甚至已經「習慣」了這種勉強自己的感覺。
他不知道,原來一個人也可以活得抬頭挺胸,不用勉強自己去配合別人。
2.台灣阿信——當「好人」就會被喜歡的幻想
從「委屈」這個概念衍生出來,在華人文化底下,也有著「阿信」原型。
《阿信》一開始是1983年在日本播放的晨間連續劇,該劇本以「阿信」這位女性從7歲到84歲的生命為主線,講述一個女人為了生存掙扎、奮鬥、創業的故事。
該劇於日本國內首播期間的平均收視率是百分之五十二點六,為日本史上收視最高的日劇。後來也在全球其他63個國家播放,當中包含台灣。1994年在台灣首播時,也在台灣掀起一陣風潮。
而「阿信」這個女性原型,能夠獲得大家這麼高度認同,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它拍出了許多日本與台灣女性的悲苦與心聲。
台灣阿信的特色是,不斷地付出、壓抑自己、委屈犧牲、忍耐,成就身邊所有的人,但除了自己。這背後有幾個意象,包含「刻苦耐勞」的象徵,很「偉大」且「堅韌」的女性。但她的偉大是建立在個人的悲慘與犧牲之上。當然也有一種「明明是好人,但最後卻沒辦法善終」的悲劇感。
因此,我總是開玩笑,大部分在鄉土連續劇中的好人,總是到了連續劇最後一集,才冤屈大白,才得到自己想要的理解或善終。但前面苦了大半輩子(100集連續劇中的95集),那痛苦卻也都是真實存在的。
反過頭來,壞人在過程中耀武揚威、作威作福,總使用著巨大權力,打壓好人,滿足自戀,讓人看了直怨不公平。但一方面我們看不起這壞人,卻也在心中偷偷羨慕著這些「壞人」,這麼自由、有力量,真好。
其實劇本,也折射出我們的人生。而許多戲劇的腳本這樣走,也絕不是偶然。
因為(所謂的)壞人,換個正面眼光來詮釋,他們有一個特色是:「他們從不吝於去爭取他們自己所需要的」。當然,壞人的「壞」,在於他爭取他所要的方法是「不擇手段的」,是不倫理、不道德的,但他們卻比誰都努力地去爭取他們所想要的目標。
反過來說,有很多好人則是習慣委屈、犧牲自己,放棄自己的需要,彎低著自己的姿態活著。
●
我看過一部漫畫《東京噬種》,男主角的媽媽,在男主角記憶裡是個極度溫柔的女子,但最後卻因為生病過世,讓男主角非常傷心。而男主角也承襲了母親的善良,對身邊的人,竭盡一切的溫柔以對。
但是劇中的反派角色,在某一段對話中,用一種非常尖銳的語言,不斷挑戰男主角:「你的媽媽真的是那麼無辜的嗎?你的媽媽,在別人欺負她,在她的姊姊向她要錢的時候,沒有認真地拒絕,不斷把錢給她的姊姊,導致自己過勞工作,最後重病死亡,難道她自己完全沒有責任嗎?這真的是善良?還是太過懦弱?懦弱到她其實沒有保護自己,更沒有保護當時是孩子的你。」
這些話,固然有一些不完全客觀,也是刻意用激將法的方式,故意要刺激男主角,但說的也不失幾分事實。看起來總是委屈自己的阿信,其實是在她的生命中,從沒學會過怎麼不用委屈的方式保護自己。
當然,回歸阿信本身,那也不是阿信的錯,是整個大時代的悲歌。看過《阿信》電視劇的人,可以了解到,阿信從小到大,都是以養女的身分存在於這個家庭,而那種把自己縮小的選擇,也是她的生存之道。
而《阿信》能夠成為最火紅的電視劇,那是因為那是屬於我們整個時代裡頭,(尤其是)女性的一種投射。大家都在阿信身上,看到自己的苦,但也都在心中偷偷盼望著,有一天,這種「苦」可以被理解,甚至在自己這樣「不斷付出」的過程裡,認為「終將有一天,孩子與家人,能夠理解自己究竟有多辛苦。那麼,自己這輩子的付出都值得了……」。
這種努力付出、當個「好人」——從小當個好孩子,長大當個好情人,結婚當個好先生、好太太──就能夠得到自己所要的、就能被喜歡的期待與幻想,是普遍存在大部分的台灣人心中的集體潛意識。
3.老二哲學
另外,再來談談「老二哲學」。
我印象很深刻,在我的小學階段,因為我很幸運(而不是比較有能力),我有比較多的資源,可以在下課之後,爸媽會請家教來家裡幫我複習功課,所以我在學校上課聽一次,回家又再聽家教上一次課,很容易拿到班上的第一名。
但有一次,我卻考了第二名。爸爸告訴我:「沒關係,不要總是拿第一名,拿個第二名比較好。」
當時我很困惑,哪有第一名不當,要當第二名的道理。但後來我發現,那其實是根深柢固在我們的文化裡頭的「老二哲學」。
我們的文化中,真的太害怕「出頭」,被看見。
我想大家對於「恐懼失敗」應該不陌生,很多人因為恐懼失敗,就會逃避責任,或是變得完美主義。但在心理學裡,還有一種現象,叫做「恐懼成功」。
為什麼要恐懼成功呢?
聽起來很諷刺,但在我們的文化中,常常是恐懼成功的。
成功,理當是大家所嚮往的。但是成功,代表我們可能會遭人嫉妒;代表我們可能會被期待與要求得更多;代表如果我哪一天「摔下來」,不再那麼優秀,讓人失望了,那該怎麼辦;代表,我是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存在;代表,我會太驕傲、太耀眼,讓別人不舒服……
而這種「不能過得太快樂、太幸福」的緊箍咒,是台灣這個集體文化下大家共有的,在「女性」身上尤其是如此。東方女性普遍有一種「不能夠過得太幸福、太快樂」的自我束縛存在。
●
我還記得小時候,當我告訴爸爸,學校老師誇獎我哪裡做得很好時,我很開心,我也很希望爸爸能夠看見我的好、誇獎我。
但爸爸怕我太過驕傲,所以很認真地「提醒」我:「那只是外人誇獎你,不是真的。真正跟你親近的人,不會講這些好話,讓你太驕傲。」
當時我很受傷,我明明被誇獎了,但爸爸卻說那是假的。我覺得自己的努力與好,沒有被認可。
但我現在知道,爸爸也是在這個文化底下的傳承者/受害者之一。
而上面這幾種現象,都是從我們文化中衍生出來的。我們不能太突出、太特別、太優秀、太好、太快樂、太以自己為主,否則你就是那個奇怪、不對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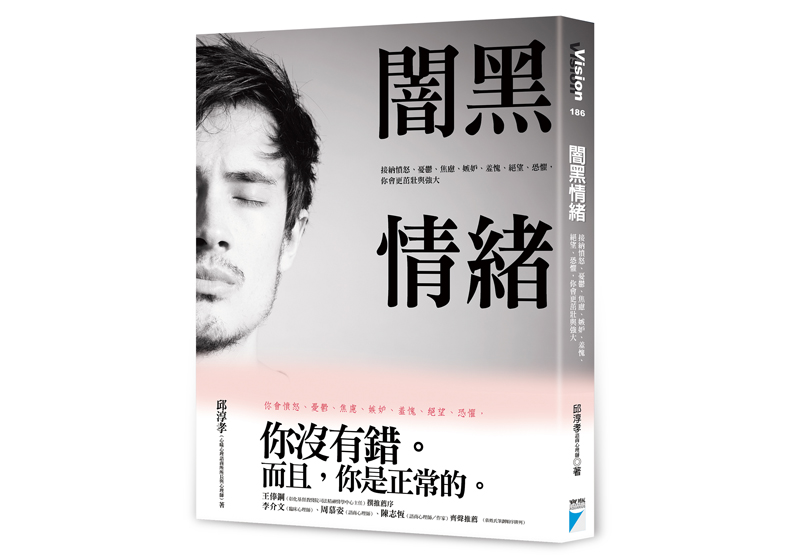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闇黑情緒》一書,邱淳孝著,寶瓶文化出版。
本文節錄自:《闇黑情緒》一書,邱淳孝著,寶瓶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