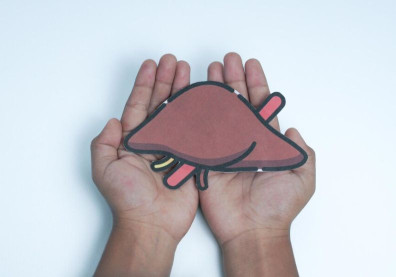下午六時,台北市交通大隊勤務指揮中心內,一陣忙亂。
隔著一大片透明玻璃窗,可以清楚看見鄰室的一面牆上,八架電視監控器,正在輪流掃描著台北市幾個重要交叉路口;十幾台電話,不時鈴聲大作;夾雜著街頭值勤的警員從四面八方傳回的無線電呼叫聲。一糟糕,車禍又「滿檔」,十三部警車都出動了。」負責指揮調度的警昌、貝施鴻洲一邊忙著接聽路況訊息,一邊為派不出人手焦急。
「這已經是今天第一百二十五件車禍了!」施鴻洲指指手上的文件,密密麻麻地記滿了八大張當天發生的車禍。他搖搖頭嘆道:「台北市的交通,教人會發瘋!」
人車大戰是共同經驗
在台北市各交通要道,「人車大戰」似乎是全台北人共有的經驗。
不僅交通大隊的警員要感嘆,對全體台北市民而言,每天被迫面臨的交通問題,就像一場永無休止的戰爭,令人充滿了無奈與挫折感。
就在距離台北市交通大隊不到三十公尺的警廣交通專業電台,這天接到民眾提供和詢問路況的電話,已不下百通。沈重的業務量,使得這個僅擁有十五坪空間、十六人編制的電台,不勝負荷。電台組長劉俊發點燃了一根菸,微微顯露出倦容:「僅僅去年十月受理的九千七百多件案件,幾乎是前年的兩倍。」
根據交通大隊統計,台北市平均每天發生車禍一百五十次。換言之,每個小時內,在台北市至少出現六.二五次交通事故。
汽車數量毫無限制地持續增加,是使台北市交通每況愈下的主因。根據台北市政府統計,截至去年十月,台北市的汽、機車數量已達七十六萬八千輛,如果以台北市現有人口計算,平均每一千人有一百五十輛汽車、一百六十輛機車。
在台北市有限的道路面積中(總面積十七.七平方公里),要容納七十六萬輛汽、機車,就像是一個吃得很撐的人,硬強迫他灌水一樣狼狽。
隨著經濟活動的頻繁,近十年來,台北市的汽、機車,正以每年四萬輛的數量急遽增加中。而台北市的道路面積,十年來卻只增加了四平方公里。「四萬輛車,在高速公路上可以從基隆一路排到彰化;也可以排滿十條建國南北路,」市議員王昆和透露,台北市的重要道路,差不多都已開完了。他急切地喊道:「車輛再這樣漫無止境地增加下去,整個台北市會死掉!」
台北市已「血脈」不通
都市是一個有機體,交通則是這個有機體的「血脈」。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所長謝潮儀憂慮地指出,台北市這個有機體,顯然因為「血脈」不通,已出了毛病。
二百六十二萬人口,擠在面積不過二百七十一平方公里的台北市(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有九千六百人);再加上鄰近六縣市(中和、永和、新店、板橋、新莊、三重)越區活動的人口(據估計約在二百五十萬人以上),使得整個大台北都會區每天的通勤人口,超過五百萬人。
人多、車也多,幾乎把整個台北市塞得滿滿的。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陳武正估算,台北市目前尖鋒時間的平均行車時速大概是十五到二十公里,低於一般正常時速三十公里的標準。
有十年採訪交通新聞經驗,交通專業電台記者孟慶霞觀察,台北市的交通尖鋒時間,已明顯地拉長。從早上七點半開始到下午六點半,扣除早上、下午就學、工作的通勤時間和中間各公司銀行業務來往頻繁的時間,大概只有在中午十一點到下午兩點短短三小時內,台北市的交通才得以稍稍疏解。
換言之,台北市的白天,有八個小時的交通是處在「緊張」狀態。
而過去塞車的範圍,只有幾條主要幹道,如忠孝西路火車站、中山北路、羅斯福路等,現在則有八成以上的道路,在尖峰時間內塞車。如果碰到下雨,情況更糟。
一名開了二十年計程車的司機,搖搖手說道:「三年前,我一個鐘頭可以跑一百五十塊,現在能跑到一百二十塊就偷笑了,」他繼續抱怨:「很難說那裡不會塞車,幾乎統統都塞啦!」
堵車也是一種公害
這個司機還舉了一個親身經歷:有一次,大約是下午五點左右,他載了一位客人從民權東路右轉到復興北路,車子開了還不到五百公尺,就堵了一個多鐘頭。他冷笑一聲:「賺了二十塊,連油錢都不夠,這行飯愈來愈難吃了……。」
心理學上有一個經常被人們舉出來的例子:把一隻白老鼠放在一個籠子裡,給牠足夠的食物和水,牠可以輕鬆自如地在裡面打轉兒;等到籠子裡增加到一百隻白老鼠,食物和水等量增加,但是這一百隻老鼠開始顯露急躁、不安的情緒,並且自相殘殺。
壅塞的交通,正如驟增的白老鼠,阻礙了人們的活動,同時產生的空氣污染與噪音,也令人情緒緊張。三軍總醫院精神科主任陸汝彬指出,堵車也算是一種「公害」,會使某些人身心失調。
一名攝影師承認,每天花四小時在通勤上,使他的脾氣變得暴躁易怒。一名胡姓公車司機也發現,做了二十年的駕駛員,使他罹患了胃潰瘍和輕微的高血壓。
只有逆來順受?
當了十年的市議員,對交通問題研究頗為深入的市議員王昆和,形容自己這一兩年來「每次堵車就免不了生氣」,因為,光是為了改善台北市的交通,他在議會裡「質詢了幾百遍也沒用」。
這種「沒有用」的感覺常形成民怨。一名計程車司機,手指著車窗外不時擦身往來的車輛,惡狠狠地說了一句:「這些做官的,簡直都是飯桶!台北市的交通怎麼會搞不好?給我當交通部長,三兩下就解決!」
擔任過三年外勤工作的交通警員施鴻洲,談到自己的經驗,不由地露出一臉苦笑:「每天在外面吸了一肚子黑煙,還要挨罵受氣……。」
交通專業電台劉俊發組長,也毫不掩飾他的無力感:「交通實在太亂了,除非把整個台北市炸掉!」輕輕敲著桌面,他略顯激動地說:「我們每天在節目中提醒駕駛人改道,但是究竟要他們改到那裡去?根本是無路可走!」
儘管生氣、抱怨,絕大多數的台北市民,面對這個連交通專家都感到棘手的問題,似乎除了以「逆來順受」的心情接受以外,別無他途。
統領運通公司總經理王高慶,兩手一攤說:「我簡直無計可施!」
如同浪費生命
為了避免塞車,王高慶放著自己的車不開,每天花一百多元改搭計程車上、下班。他抱怨:「計程車司機也是意見一大堆,動不動就拒載。」王高慶懷疑那些提出交通改善計畫的政府官員,到底有沒有實地瞭解狀況?
到過埃及,發現開羅的交通比台北還亂,王高慶才覺得稍微「舒坦」些,「畢竟台北市還不是最糟的,」他自我解嘲地說。
台北市到處塞車,很多人必須花更多的精力,去計算那些可能被耽誤的時間。
以台北市交通流量頗大的長安東、西路而言,依據台北市政府新工處交通科在去年三月二十五日做的調查,從西寧北路至基隆路之間由西向東行,全長六八九0公尺,在尖峰時間(下午五點到七點)要比非尖峰時間多花十三分鐘。
一個人每天浪費十三分鐘,一年就浪費了七十九個小時。假使這個人在同一地點工作二十年,其中有六十六天是完全被浪費了。
從高中時代開始飽嚐塞車、等車之苦,目前在雜誌社上班的蕭學仁,常常懷疑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就這樣白白耗掉了?
堵車也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與作息時間。在IBM工作的周定輝,每天在台北、基隆兩地奔波,必須耗費三個鐘頭。一氣之下,有一段時間乾脆在公司附近花了三千塊錢,租了一間只有一床、一桌的房子,「只要能容身睡覺就行了,」他解釋。
一道無解的習題
來台灣已有七年的香港僑生鄭鈞源,他感覺每天從木柵到台北上課,要比七年前多花一倍的時間。為了趕早上八點第一堂課,他往往得在六點多出門,然後再利用坐車的時間補足睡眠。他比較香港和台北的交通:「光是公車數量,台北大概是香港的三倍。」
家住天母的室內設計師邱德光,早上為了避開士林、圓山的堵車,索性繞道大直改走濱江街再上建國南北路,車程足足遠了三分之一,「雖然浪費些汽油,時間即縮短了一半,算算還是划得來。」他說。
魏碧倫算是少數比較「幸福」的,她每天只需花三分鐘從華陰街步行到市政府上班。但是途中必須經過承德路台汽客運北站一帶,野雞車強行拉客混亂的局面,每每令她心驚肉跳。一我在這裡住了那麼久,從來沒有看到誰來管過!」
「管」畢竟是被動的,開車人主動的行為更是關鍵。
由一群計程車駕駛組成的綠十字服務隊,每天在尖峰時間義務協助警察,在重要路口指揮交通。綠十字隊員盧福龍批評,大多數的市民交通行為很差,「有縫就鑽,有路就走,也不管守不守法,交通秩序怎麼不亂?」
周定輝描述他的開車經驗:「大家都在爭車道,誰的車頭先頂出去,誰就贏了。」
「這份工作做久了,愈來愈沒有成就感!」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交通警員嘆道。他悲觀地形容;台北市的交通「就像是一道無解的習題」。
這道習題如何解?交大管理學院陳武正院長寄望於未來的大眾捷運系統。
然而,縱使大眾捷運系統能擔負大台北區五百萬通勤人口四0%到五0%的交通旅次,距離完工之日,還有遙遠的十二年。換言之,台北人還得忍受十二年漫長的塞車之苦;交通專家們,則在十二年之內不必擔心砸掉飯碗。
汽車廢氣惹人生氣
大都市裡為何犯罪率較高?最新的科學研究或許可以為我們提出合理的答案:被汽車廢氣所污染的空氣能使人情緒暴躁。科學家早已懷疑空氣中的毒物會使一些人行為乖張;而隨著神經毒物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科學家相信,我們所呼吸的空氣確實會影響我們的頭腦。
科學家在幾年前就發現鉛會阻礙兒童的智力發展,因此美國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早已規定汽油中的含鉛量必須降低。也許在近期內,該署還會完全禁止使用合鉛汽油。
現在又發現另一種更糟糕的污染物質,就是臭氧。臭氧原是存在於大氣層中,阻擋太陽輻射線的有益物質;但是在溫暖、無風而且乾燥的日子,陽光與汽車廢氣中的化學物質混合,產生過多的臭氧,累積在低空中徘徊不去,就會威脅到人體的健康。
臭氧激發暴力事件
洛杉磯的警官查理斯.梅利說:「每當熱氣蒸騰,人們被污濁的空氣刺得兩眼發痛的時候,就會有許多人逗留在屋外,找別人的碴子。」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心理學家詹姆斯.洛頓指出,高犯罪率確實與污染空氣的化學毒物有關。洛頓曾以俄亥俄州的岱頓城為樣本,將兩年來該城的警方犯罪紀錄和空氣污染資料作一比較後,下結論說:「在空氣污濁的大都市中,臭氧激發了成千上百的家庭暴力事件。」
然而也有一些科學家認為,將人類的暴力行為完全歸咎於空氣污染,未免有失偏頗。美國環保署研究員勞倫斯.雷特即認為:「人類行為的形成過程十分複雜,且易因各種原因而改變,因此我們必須就化學污染物質對人類的腦、神經系統和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確定人類行為純粹是受化學物質的刺激而改變,與其他因素無關。」
洛頓為了證實自己的結論,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他用數據方式將污染以外的其他因素全部排除,所得的結果並未有何不同。因此他再度強調:「如果一個人原來已有一些生活上的困擾,惡劣的空氣就會將此人推到情緒崩潰的邊緣。」
六千人的證實
加州大學的蓋瑞.伊文斯和史蒂夫.雅各則採用另一種研究方法,來證實空氣污染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他們在全美車輛最多、空氣污染最嚴重的洛杉磯,以電話訪問了六千名各個階層的民眾。在訪問中,他們詳細詢問被訪者在工作和家庭中的壓力,以及身體和精神各方面的狀況。
結果發現許多人能夠從自己情緒的變化,感覺到空氣污染的程度,而他們大多是在生活中有嚴重困擾的人。雅各同意洛頓的見解,他說:「人多半是先在生活中遭到挫折,長期的污染則使他變得更為暴躁而好鬥。」
美國國會於一九七0年通過的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對清潔空氣訂下嚴格的標準,企圖減少空氣中六種最嚴重的污染質(其中四種的肇因皆來自汽車廢氣),但是效果不彰。這是由於汽車的數量不減反增,因此許多城市根本不可能達到標準。
環保署署長李.湯瑪斯說:「要達到標準,所有的州政府、地方政府和個人都必須痛下決心。大家必須徹底改變生活方式,減少開車的次數和行車的旅程。」換言之,除非美國人放棄「出必有車」的生活習慣,否則只有任由空氣與暴力犯罪同步惡化。
(摘譯自華盛頓郵報週日雜誌「Pa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