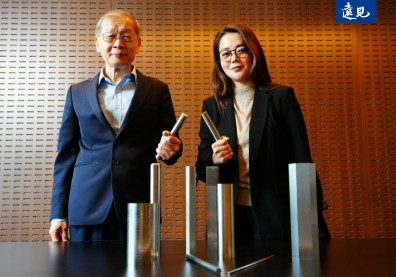他是個陽光的人,大家都這樣說。
看見他的時候,嘴角總是帶著笑,偶爾面無表情,只要喚他一聲,抬起眼相對的那一秒,他就會連眼裡也帶著笑地看向來人。
「今天我回高雄,你有沒有空來高鐵站載我呀?」早晨接近中午,我傳了訊息給他,在台北車站的人潮裡一邊走路一邊打字。
很快地,他回覆「好呀當然」的字句,我便收起手機,刷了卡出捷運站,往高鐵首站走去。
那時候的高鐵,還沒有那麼多站,南港站尚未啟用,首末站是台北和左營,如果在機器購買票卡,還是橘色的票面。
我們一直覺得,很多事情不會改變,譬如這裡永遠會是首站,在發車前還有很多時間可以慢慢來、反正列車會停得比較久的一站。
在車站外吃了點東西,算算時間差不多,便慢慢往手扶梯走去,接近十一點的列車,已在月台等待。
坐上車後,我又拿出手機,傳訊息告訴他大概抵達的時間。
他說,那就等等見。
我說好。
放下手機後,看向窗戶,在倒影上看見自己的嘴角勾著笑,眼睛彎彎的,像另一個人。
從一個不太愛笑的人,到大約花了一年的時間習慣笑起來的樣子,有時候突然看見,卻還是不曉得原來鏡子裡的人是自己,原來我笑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他不一樣,他總是笑著,笑得像是每場陰雨都有暖陽,像是一個人失去希望,還是許下一個漂亮的願望。
這時候的他,總是笑著的。
「欸,我跟妳說,」列車經過台南後,他突然傳來語音訊息:「我這場還沒打完,感覺來不及了。」我從耳機裡聽到遊戲背景聲音,還有滑鼠和鍵盤噠噠的聲響。
「哦。」我想了想,也用語音回覆他:「那沒關係,我等等搭捷運好了。」
我一邊回覆,一邊收拾著背包,列車上即將抵達終點站左營的廣播,也被錄進我的那句話裡,一起傳送過去。
「那妳搭捷運要小心哦。」
「好啦,知道了。」
「等等見。」
對話停在他的「等等見」裡,我聽了兩遍,耳邊都是即將進站的廣播聲,他的聲音在耳機裡,卻好像在有點遙遠的地方,而當列車滑進月台,我背上背包,在微微搖晃的車廂裡往門口走去。
在樓梯上,我一邊踩著階梯一邊在腦袋裡轉著,從高鐵換乘捷運,這條不太熟悉的路線要怎麼走。
先出站之後,聞著咖啡香找到咖啡廳之後往左邊走,出了高鐵站,搭下行的手扶梯,就會看到往捷運站的標誌了。
好。我下意識地雙手拉緊背包背帶,刷了票根出站後,加快腳步,面上沒有表情,正要認真地嗅起咖啡豆的香味找路時,突然對上一雙帶著笑的眼睛。
在檢票口往咖啡廳唯一路徑,他斜斜地靠著柱子,柱子上貼著標示如何往捷運站走的路標貼紙,正好在他的雙眼旁。
我看看貼紙,再看看他,愣了好幾秒,總算反應過來,衝到他面前,張了張口,呆呆地說了一句:「你怎麼在這裡?」
「我剛剛不是說,等等見嗎?」他拿出手機,晃著聊天畫面,上頭掛滿許多語音訊息,最後一個是他那句兩秒鐘的「等等見」。
「可是——」我還想說什麼,卻沒有說出口,還是看著他,看著他掛著燦笑的嘴角,和笑彎起來的雙眼,然後在裡面看到一臉呆滯的自己。
看到最後,我笑了出來,認真地開始發問:「好啦,你等很久了嗎?」
「沒有呀,」他拍了拍我的頭,說:「剛才看到某人一路從樓梯上穿越人群狂奔,一下子就等到了。」
「那你怎麼知道是這個出口?」我又說:「離捷運站最近的明明不是這邊的剪票口。」
「妳不是把車廂拍給我了嗎?」他指著我捏在手裡的票根,耐心地回答:「我覺得妳應該會從最靠近車廂的樓梯上來,然後聞著咖啡香找到咖啡廳,再往捷運站走。」
「那,」我不曉得要說什麼了,嘟囔著:「那,為什麼要故意這樣啦!」
「這樣妳就會有兩百分的快樂。」他極其認真地看著我說。
我沒有說話,他慢慢地開口:「原本因為我不會來接妳,可能心情不太好,我們算負一百分,但是後來我在這裡等妳,心情好的話,就到正一百分好了,這樣妳不是比原本的零到一百還開心更多,有兩百分的快樂嗎?」
他盯著我,眼裡沒有輕鬆隨意,而是單純的認真。
看見這樣的表情,我就明白地笑起來:「老實說,這個歪理又是你突然想到的吧?」
他露出破功的表情,也笑了出來,我們牽起手,一起離開,身旁有陣咖啡香傳進鼻腔,是路過的人捧著美式黑咖啡,那是我們都喜歡的味道。
那是我後來一直喜歡的味道。
後來的高鐵台北站,在英文廣播裡從「Terminal Station」變成「Brief Stop」了,不再是起點或者終點,只是成了過路的短暫停留。
後來的他,還是笑著的,笑得像雨季前最後一道陽光,像一個人還剩一個願望,並且再也沒有提起要讓我快樂。
後來的我,擅自獲得兩百分,在每次笑起來的時候,想起他說的,記得要快樂。
有那麼多個「後來」在日後的我們手裡,真正拿出來的,好像都是準備好被陌生的目光擁抱的。
而我們之間的眼神仍然帶笑,他帶著他的,我帶著我的,笑意成為那年雨季之後的夏天,成為煮好後被取消訂單的咖啡一杯。
都有點晚了,但我們還是笑著,還是輕輕笑著。
 本文節錄自:《還想在你的未來聽到我》一書,愛瑪著,麥田出版。
本文節錄自:《還想在你的未來聽到我》一書,愛瑪著,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