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關於愛,老子講得不算太少。譬如「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第十章)王安石是一個能幹的有天下抱負的人,他注《老子》,對此的解釋是:「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治國者,以不治治之乃長。唯其不愛而愛,不治而治,故曰無為。」(容肇祖輯《王安石老子注輯本》)這是從愛造成的結果來說的。所謂多愛多敗,因為你管得太多,統得太死,你計劃經濟,你天下一盤棋,必定擊沉了天下人的創造熱情,並使之倍感失敗和壓抑。有不能成事者,還進而養成了事事依賴公家的愉佚與惰性。是所謂愛民,適足以害民。故與其如此愛,真不如不愛。
而從施愛者的角度來說,在做到「自知不自見」的同時,老子又要求他們能「自愛不自貴」(第七十二章),即在知所能與不能並不自顯其能的同時,持身嚴謹,清心寡欲,而不是自尚高貴,感覺良好。因為這樣做的話,很可能會過分放大自我,最終必然會招人厭棄,落一個不能自愛的駡名。
可要做到「自愛不自貴」談何容易。究其原因,老子一針見血,在「有身」。他說:「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何謂「貴大患若身」?同章中他有展開性的說明:「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他的意思是人既有此身,愛之貴之自是應當,但這一切須循自然之理以應物,而不是放縱私欲以害物,須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而不是自私其身,貪戀權位。若能做到這種不自私其身,那人又能有什麼禍患呢?這裡,他所說的「無身」,很可以為上述「自愛不自貴」作一注腳。如此,能夠以貴身的態度去為天下,知道珍重一己生命並施及天下蒼生之命,老子認為就可以把天下交給他了。能夠以愛身的態度去為天下,知道不能以一己之欲覆蓋天下人之所欲,也就可以把天下託付給他了。這就是此章末所謂「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的意思。
上面的話,更像是講給聖人侯王聽的,但老子也有對一般人的愛的箴言,那就是「甚愛必大費」。過於愛一個東西,必定會讓人有很大的耗費。這個東西是什麼?老子沒有明說。歷代注家多有揣測,有說指名,有說指利,也有說是指色。其實,天底下能引人欲念的東西何止這些?占著權位能免費吃大餐嗎?喝著美酒能免單是嗎?
古玩字畫是嗎?香車寶馬、名邸豪宅是嗎?或許,對一些有特殊癖好的人來說,還有許多欲念,非人所能悉知。可天底下這麼多好東西是你一人可以愛得過來的?為了愛已經有的那些東西,你已經很累了。再以已有的東西為資本,去索愛更多的東西,你能避免不勝其累的辛苦嗎?所以,還是蘇轍《道德真經注》說得好啊,「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為,能無費乎?」
A《老子》原文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第十三章) 甚愛必大費。(第四十四章)A今譯 得寵和受辱都讓人感到驚慌,重視身體好像重視大患。 過分愛惜必定會有大的耗費。 A注釋寵辱若驚:得寵和受辱都使人驚慌。 貴大患若身:重視身體一如重視大患。王純甫說此句當為「貴身若大患」,古語倒言求奇之故也。陳鼓應說因「身」與上句「驚」,真耕協韻,故倒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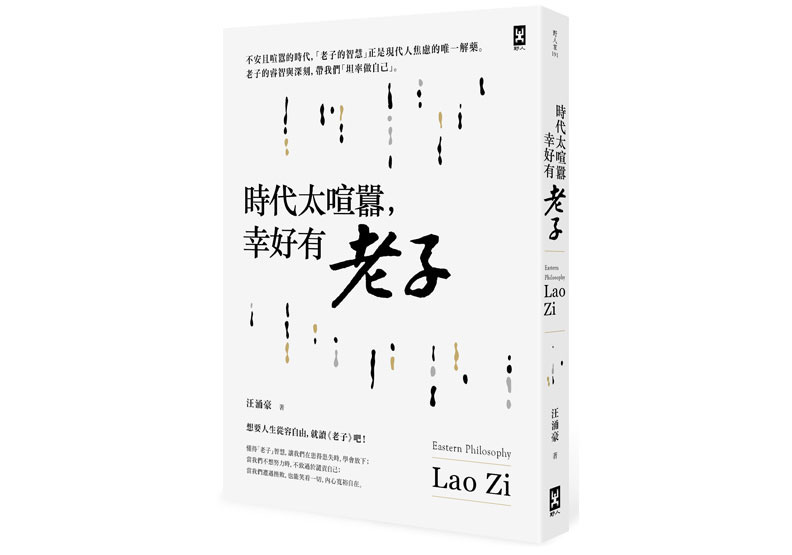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時代太喧囂,幸好有老子》, 汪涌豪著,野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