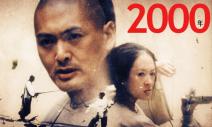最慘的年代,該如何從死亡中重生?
在取消戲院映演國片比率,不再對外國電影徵收國片輔導金,加入WTO 後又對電影製作、行銷與放映服務做出完全的市場開放,台灣電影面對「迫切的危機」,加上拍片環境不景氣的影響,逐漸在票房收入的羞澀下顯現疲態,甚至在2002年至2006年間,本土國片市占率僅不到2%。
2000 年《臥虎藏龍》的成功,讓台灣電影人開始思考,在死亡時刻,國際合作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藍海策略?大家都在看,美商全額出資拍攝,工作人員來自台、港、美、澳各地,在創下台灣電影最高製作成本的《雙瞳》,能不能讓瀕臨死亡邊緣的台灣電影,帶來滋潤的雨水,甚至重生?
邁入21世紀,台灣電影進入死亡期,關鍵就在於2002年我們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立法院刪除了對電影的保護制度,部分戲院必須播放國片的保護制度也被刪除。
當一個國家完全棄守電影,其實就等於放棄自己文化的詮釋權及話語權。台灣大概是全世界,少數除第三世界國家之外,完全放棄電影文化的國家,風雨飄搖下的小草,硬生生被碾死。
我們做了一個非常錯誤的關鍵決定,兩顆「蛋」決定了台灣電影的命運,一個是「壞蛋」,指好萊塢;另一個是「笨蛋」,是我們的文化決策者。
好萊塢施壓、遊說美國政府,要求世界各國都要對美國開放電影,而美國電影其實就是一個生活形式、價值觀、語言與世界觀的文化輸出,它只有一個核心價值,就是「以暴制暴」,跟中國或台灣的東方文化底蘊完全不一樣。
一個國家放棄自己的話語權,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事。2000年左右,台灣整個思維完全沉浸在科技產業,代工可以替我們創造巨大的外匯、文化與經濟的交換,但是,有沒有人想過,科技代工是可以被取代的,只有文化的詮釋不能被取代。
除了雨水,過境颱風還帶來什麼?
2000年後,台灣導演變得非常安靜;尤其是2003年,整年台灣國片的票房,只有新台幣1375萬元。那時一部電影的票房若有100萬元,一定要放鞭炮、發新聞稿、辦慶功宴。
在最慘的年代,台灣電影如何從死亡中重生?我的答案是:國際合作。
有鑑於美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Columbia Pictures)投資的《臥虎藏龍》,獲利超過1億美元,更橫掃2000年的奧斯卡、金球獎、香港金像獎、金馬獎各大獎項,這刺激了西方電影公司,他們開始看到亞洲市場的潛力。哥倫比亞決定在中、港、台3個地區投資,台灣就選定陳國富2001年開拍的《雙瞳》。
那年有高達9個颱風侵襲台灣,《雙瞳》的拍攝行程及情境經常因此做調整。對照來看,美商投資台灣電影,也像颱風的雨水般滋養了台灣電影工作者。
但我不禁思考:跨國合作模式的電影製作中,我們應該思考的課題是什麼?就像拍攝期間一直過境台灣的颱風一樣,除了大量的雨水之外,它還帶來了什麼?在死亡時刻,國際合作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藍海策略?
好萊塢電影對於亞洲的概念,以早期的《末代皇帝》為例,因為考量到英語系國家的觀眾,所以戲中的溥儀從頭到尾都在講英文,敘事也是屬於西方人眼中某種異國情調。但到了《雙瞳》就不一樣了,不需要去考量西方世界能否習慣東方的節奏與口音,你就做你的,接著完全就是我把你購買下來,完全去販賣屬於東方的文化背景、專業人士等,而我好萊塢是最大獲利者,我也只要投資1000萬美元就可以。
不負眾望,《雙瞳》在台票房高達新台幣8000多萬元,打破當時台灣電影沉淪的局面,在壞蛋與笨蛋聯手的狀況下殺出了一條血路。
眼界開了,看見未來可能性
15年過去了,再回過頭來看《雙瞳》,它最大的貢獻其實並不在票房數字。它雖然告訴了台灣所有投資者,我們有辦法拍出觀眾喜歡、賣座的電影,但從歷史的結論來看,在《雙瞳》之後的幾年,台灣電影的低迷態勢並沒有改變。《雙瞳》最大的意義與價值,其實是帶出一群當時只有30幾歲的年輕電影工作者。
例如魏德聖,他是《雙瞳》的企畫,兼一部分副導的工作,陳國富導演原本希望由他來當導演,可是美商不相信他,但陳國富還是把他帶在劇組裡。例如韓允中等人的「第二攝影組」,雖然他們負責的只是次要角色及街景空鏡等拍攝,但是陳國富還是會要求他們要到拍片現場協助,跟著學些東西。
雖然我沒有問過陳國富導演,他是不是刻意這樣做,但我相信他是刻意的,因為預算是夠的;但宏觀來講,他反而是培養了一群希望看到台灣電影不一樣未來的人。
與魏德聖聊到這段經歷時,他的答案非常俐落,他覺得《雙瞳》帶給他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視野。我又問了參與演出的戴立忍等人,大家用的字眼可能不一樣,但總括來說同樣是「視野」,透過這部片子,他們看到了電影的各種可能性。6年後、8年後,這個視野開始慢慢發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