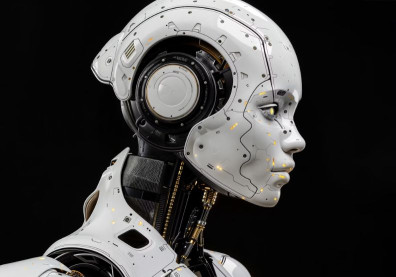一名凶猛強悍的武士在路上遇見老禪師,向他請教天堂與地獄的意義。
老禪師說:「看你這種人,跟你講也不會懂。」
武士大怒,拔劍大吼:「老漢無禮!我把你給宰了!」
禪師淡淡地說:「這就是地獄。」
武士恍然大悟,趕緊收劍,深深鞠躬,感謝禪師的指點。
禪師說:「這就是天堂。」
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是在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的《EQ》這本書中。武士和禪師的故事代表了EQ的核心理念:當人陷入了無法自拔的負面情緒,就好比陷入地獄;能夠跳脫情緒的捆綁,透過理智得到平靜,就等於到了天堂。
《EQ》自從1995 年出版就蟬聯排行榜,對於剛從心理系畢業的我也投下震撼彈。快轉20 年,EQ 已是家喻戶曉的名詞,教育家也都公認「情商」的重要性,但從最近的學運事件看來,令我驚訝的是多少「高知識分子」仍舊在基本的EQ 層面上犯規。
每個人心中都住了一個野人
舉例來說,網路上有不少挺服貿的發文,提出了數據論述,做了詳細分析,最後卻硬要補上一句:「醒醒吧!你們這些孩子們!」
反服貿人士也舉出證據和辨思,列出合理的質疑,但最後也忍不住補上一句:「你被賣了還在幫人數鈔票!你關心過台灣嗎?!」
從小學作文,老師就叮囑結尾最重要,每段的結尾都該有「回馬一槍」的力道;就像笑話的笑點都壓在最後一句的punchline,辯論也是如此:最後一句沒力,整段論述就弱掉了。
問題是,「強」的結尾往往不是在論理,而是在煽動情緒。
我做了個實驗,把一些反服貿和反反服貿的發文並列,把每段文字的最後一句拆出來,結果讀起來判若兩人。少了那最後一句,兩邊的文章像是理性的論述;但光看每段最後一句,就覺得雙方快打起來了。
很遺憾的,後來沒有更理智的討論,反而愈罵愈凶,從三字經到國罵,最後連祖譜都端出來問候,這時雙方早已陷入所謂的total breakdown in communication,徹底無法溝通了。
以我看來,這種情緒化的反應很可惜,但也很正常—如果你是野人的話。
我講的野人,就是千古萬年前那種毛毛的原始人。野人不會坐下來跟你平心論談,只想一棒子把你打死。野人不在意協商是否滿足自己的需求,反而比較在意能不能傷害對方。
萬年進化而來,我們有一部分都還是野人,不管誰都一樣。無論是黑道白道,甚至學者與出家人的心裡也都還住有野人。我們可以制伏他,但無法殺掉他。
不要讓野人挾持你的飛機
平常,野人其實是我們的保鑣,靜靜地守在身邊,反應快,行動能力強。不過野人一旦被激怒,就很容易變成「綠巨人浩克」。浩克一旦暴走就很難控制了,「理性」這時會變成合理化情緒反應的「假理性」,行動和言語不再以解決問題為目標,而以毀滅對方為先。這種狀況,在高曼的《EQ》中有一個很傳神的名詞:「情緒劫機」(emotional hijacking)。
想像大腦是一架飛機,理智的自我是機長,野人則是副機長,一個穿著制服,另一個披著皮草。兩人平日合作愉快,唯有遇到緊急狀況時,機長得跳出來做決定,不能讓野人靠近駕駛盤,因為野人自認很行,但其實只會起飛,卻不懂如何降落,更不會規畫航線,只會大聲喊:「衝啦!」
當我們遇上不理性的爭執,就好比遇上劫機。若機長不夠警覺,讓野人奪走了駕駛權,就無法控制飛機的導向。當野人大叫「老子跟你拼了!」把客機當戰鬥機,加速失控的時候,真正劫機的人反而不是敵人,而是身邊的副機長。
這次學運中,我看到雙方有太多人被自己的情緒劫機,在雲端世界暴衝,造成多年的友誼破裂,親友算舊帳,種族文化對立,憤怒、焦慮、憂鬱不堪,元氣快耗盡了還無法降落,實在很危險。
過於情緒化的溝通,很難有建設性的下場。我不做議題分析,重點也不在教你如何贏得辯論,只想簡單提醒各位:不要讓野人挾持你的飛機,做出會後悔的事,講出會後悔的話。
下次如果有人刻意激怒你,請讓機長先發言:「你剛才那句話在劫機我的情緒,我選擇不回應!」如果身邊的野人想嗆聲,補上一句無助於討論、只想罵人的話,你可能要暫停通訊,帶野人出去走走,讓他冷靜下來,再好好規畫理智的航線。因為這是緊急狀況,我們雖然都有理想的目的地,但平安降落更重要。
為了我們共同的未來,拜託,請別讓自己的野人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