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露迪因《反挫》成為媒體寵兒的那年,學界出現另一個火紅的關鍵字──「商品女性主義」(commodity feminism)。捧紅這個詞的是美國媒體學者古德曼(Robert Goldman)。古德曼的立論清楚明瞭:商品文化收編了女性主義。他在八○年代的女性雜誌中發現女性主義已大量走入時尚廣告,成為視覺符碼與個人風格。廣告商有意識地以商品再現女性主義,卻在此同時化女性主義為市場經濟,化集體政治為個人選擇。
古德曼指出,宣揚女權的雜誌與其他商業刊物一同現身於《廣告時代》(Advertising Age),共同競爭廣告業主的青睞。即便是象徵「正統女性主義」的《女士》雜誌,都身處於同一片商業網絡,以無異於時尚雜誌的語言包裝自己──「儘管《女士》總是與《柯夢波丹》形成對比,它在廣告業主面前推銷自己的方式可沒有什麼兩樣。」不同於傳統女權社群對《女士》的讚揚以及對《柯夢波丹》的貶抑,古德曼認為「女性雜誌」與「女性主義雜誌」沒有太大差別。一旦它們進入了市場經濟,登上了廣告雜誌,它們便共同參與了「商品女性主義」的運作。
在古德曼眼中,「商品女性主義」最大的矛盾便是將女性主義與陰性特質並置再現。在女性主義的傳統史觀中,陰性特質是壓迫的象徵,女性主義與陰性特質的關係應為對立;在時尚廣告的視覺再現中,女性主義卻化為符號,與陰性符碼和平共存。古德曼主張,這樣的共存只是表象。時尚廣告一方面抹平了女性主義與陰性特質之間的衝突,一方面又創造出新的意識形態矛盾──女人可以獨立自主,運籌帷幄,但是,她必須先擁有一個完美無瑕的性感身體。
不過,女性主義與商品文化必然對立嗎?對古德曼來說,女性主義是激進的政治,只是它的顛覆力量在時尚再現中遭到收編。這樣的說法忽略一件事實,那就是「女性主義」的生成仰賴多重文化再現─包括文學藝術、批判論述與社會運動──而商品文化不過是再現「女性主義」的媒介之一。我們無法預設先於再現的「女性主義本質」,正如我們不應信仰「自然身體」的神話。任何「女性主義」都是在多元的文化場域中透過種種實踐與協商形成的政治。商品文化當然未必「女性主義」,但它也不必然「反女性主義」。事實上,早在一九八九年,費思科(John Fiske)便透過自己的消費理論,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費思科主張,消費不是收編──消費是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s)。他挪用德瑟多(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實踐」(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理論,將日常消費比作游擊戰略,將購物中心視為協商戰場。從這個角度來看,消費不是單向的輸送,而是雙向的協商;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主動的生產。既然消費的過程充滿了矛盾與抵抗,那麼,我們顯然不能再用簡單的「收編論」來解釋時尚消費與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
在費思科眼中,購物中心是消費主體的游擊戰場,而女人正是最熟悉這塊場域的「游擊戰士」。她們未必全都負擔得起商品,卻絕對足以「消費」圖像,「消費」空間。在這裡,消費超越了金錢交易,牽涉了日常實踐。女人可以在購物中心瀏覽圖像,試穿新衣,女人也可以在此群聚八卦,漫步閒逛。這種種並不仰賴經濟資本的「消費」模式,都是費思科口中的文化實踐,也讓消費的定義從「金融經濟」(financial economy)轉移到「文化經濟」(cultural economy)。在文化經濟的領域之中,商品化為一個開放性文本,消費也成為一種創造性活動。因為商品的意義可以被重寫,所以我們有了「次文化風格」;因為消費的空間可以被重奪,所以我們也有了反抗的空間政治。
當然,消費作為女性的文化實踐,至少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韋克麗(Amanda Vickery)便在《紳士的女兒》(The Gentleman’s Daughter)中指出,十八世紀的女人不如大家想像得那麼深處閨中,反而在城市社交文化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受惠於「都會復興」(urban renaissance),女人在公眾劇院、遊樂花園、集會廳與流通圖書館中大量現身,積極社交,展示最新的時裝與風尚。消費不只讓女人走入城市,更成為女性一手主導的專業領域。十八世紀因此見證了「消費的陰性化」
(the feminization of consumption)與「女性消費者」的誕生。不過,十八世紀的消費活動仍掌握在仕紳階級手中,一直要到十九世紀中葉,消費文化才真正歷經了「民主化」,使得中產階級、甚至是中下階級的女性都能以消費者的身份漫遊城市,走馬看花。而帶起這波「消費民主化」的關鍵場域,正是擁有了一百五十年歷史的女性樂園──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是屬於女人的城市空間,也是屬於女人的「都會現代性」(urban modernity)。正如所有與女性連結的歷史產物,它一度不受學界重視─包括女性主義者。早先女性主義學者深受「分離領域」史觀影響,總認為城市空間只屬於男人,不屬於女人。沃芙(Janet Wolff)發表於1985年的〈看不見的女漫遊者〉(“The Invisible Flaneuse”)正是最好的代表。28 對沃芙來說,現代性文學聚焦於城市生活與公眾政治,而這些領域要不是將女人排除在外,就是對她們視而不見。沃芙並未徹底否認女人的城市經驗,但是她主張,喬治桑之所以可以化身城市漫遊者,是因為她「女扮男裝」,而百貨公司雖然讓女人走入城市,卻仍然無法被視為「現代性」經驗──那種稍縱即逝、隨波逐流的陌生相遇。沃芙因此說,「現代性的文學描述的全是男人的經驗。」
在〈現代性的否認〉(“Modernity’s Disavowal”)中,娜瓦(Mica Nava)卻一反沃芙的說法,指出十九世紀的女人早已大量走出家庭、走入城市,而百貨公司正是開創女人現代性經驗的核心場域。是百貨公司賦予女人嶄新的公眾身份,讓女人無需男性陪同便能在城市中自在漫遊,也是百貨公司讓陌生男女大量交會,促成了情慾與階級的危險逾越。對娜瓦來說,百貨公司之所以在現代性文獻中缺席,不是因為它不重要,而是因為女人的文化經驗總是容易消失在男人的歷史視野之中。重探百貨公司與女性消費,就是重新召喚女人「被消失」的現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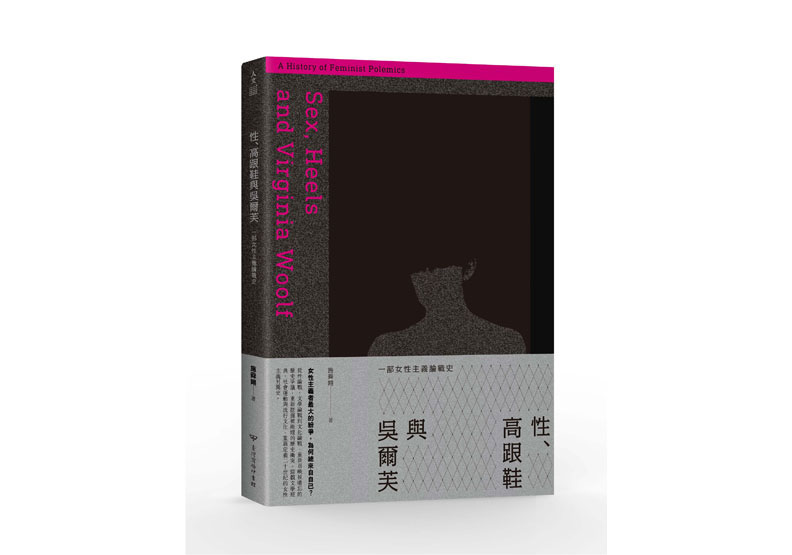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性、高跟鞋與吳爾芙》一書,施舜翔著,台灣商務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