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新加坡的一家法國餐廳裡;兩天後,又坐進另一家倫敦的印度餐廳。一個星期後;我來到巴黎的一間飯館,看了菜單,才知道他們供應泰國菜。
所以,一天下午,當我在香港中環的一處咖啡店,目睹一位婦人點了一杯熱咖啡和一盤又脆又香的中式炸豆腐,旁邊擺一小碟紅豔豔的辣椒沾醬,當作她的下午茶,我明瞭,自己一點也不應該大驚小怪。
當工業革命開始建造第一條鐵路的時候,信息開始流竄,區域開始互相模仿,人類開始移動,界限開始模糊;飛機緊跟著增快了移動的流通速度,加雜了族群的混合;而電話電報讓整個世界零時差地活在一起。
網路,給了最後的臨門一腳。
我們終於來到一個時代:膚色不再能夠指涉國籍,語言不足以涵蓋區域,服裝無以表達任何身分。
食物,成為最後一種辨識文化的方法。
你沒辦法指著一個黝黑膚色的人類,宣稱他或她是象牙海岸人,你卻可以指著檸檬魚,肯定那是一道泰國菜,不用擔憂有人會在你的電子郵箱塞滿抗議信件。
每一個號稱國際大都會的城市,都必須提供一連串不同文化的餐廳名單,泰國菜、巴西窯烤、法國料理、印度口味、中國料理、日本菜……,以證明自己的確是個大熔爐,證明自己擁有豐富「文化」。你居住的城市多「國際化」,端看你有多少食物選擇;你對異質文化的容忍程度有多寬,端賴你對陌生食物的接受態度。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炸豆腐當然可以和著熱咖啡下肚。」我朋友說。沒問題。我收起我愚蠢的表情。
在這個逐漸人工化、幻象化、電子化的超現實環境裡,幾乎所有的有機物或無機物都可以複製、移植、概念化。食物依舊牢牢連接著原始的物質環境,成為唯一真實的現實。
與物質環境緊緊相連接的臍帶,讓食物成為少數仍擁有地區限制的東西。你可以在美國紐約生產製造跟印度加爾各答一模一樣的建築物或瓷器或梳子或釘書機,可是你就是無法種植一模一樣的香料;即使你從印度進口或移植,你還是無法判斷在那種天氣下一個印度廚師究竟會灑下多少種香料,去刺激你的味蕾,讓你開懷大吃。你只能模擬,只能猜測,只能回憶。同理,你能在台北做出全世界最好吃的日本壽司,卻不見得是最道地的口味。
因為,最道地,不一定是最好吃。
透過電子圖像語言,你已經可以和你自己的Ota Benga(註一)直接作朋友,往舊金山觀賞大橋的落日,到米蘭名店購買一條褲子,不必使用你的身體也能經歷一切。但是,要吃一支北京糖葫蘆,活在電子世界的人們依然要返回物質世界,使用自己那碳水化合物做成的肉身,親身咬下一口。
我們的身體就是文化的記憶。我們就是我們吃下去的食物。今後,廚師不叫廚師了。請稱他們作「文化工作者」。
註一:Ota Benga—二十世紀初,被美國人帶回紐約展示的非洲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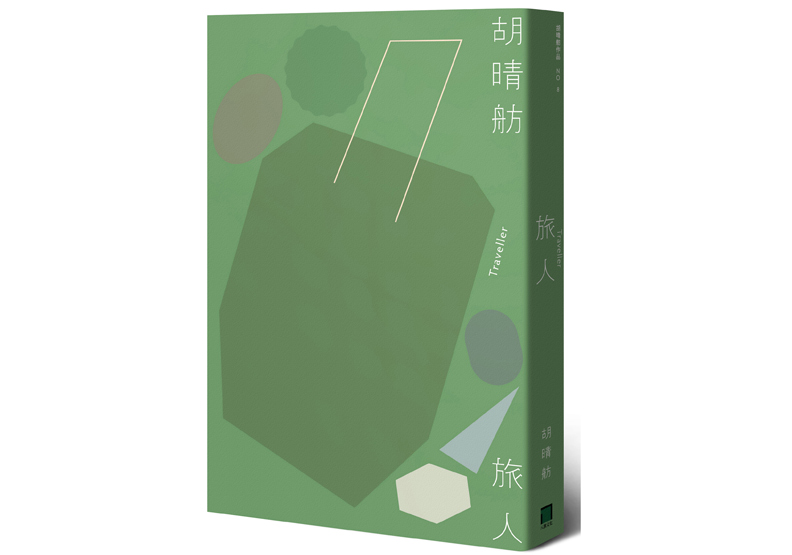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旅人》一書,胡晴舫著,八旗文化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