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吃飯是不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該不該講究食器?全世界人類對這件事恐怕都沒有定論,因為這事牽涉「階級意識」與「教養」。階級意識容易解釋,反正肉食者一直都受批評,寫出「肉食者鄙」的人,自己少不了也是個肉食者,少不了也是鐘鳴鼎食,這鼎可就是一種貴重的餐具。講到教養,如何把吃豆腐整治成吃龍髓鳳肝,恐怕除了借重餐具之外,還得有點氣氛,這點後頭再說。
古代人不太講究餐具,鴻門宴中,項羽要人給樊噲上卮酒,上生豬前腿(生彘肩)。樊噲先把酒喝了,把盾牌放地上,生豬腿放盾牌上,拿起佩劍,切了就吃。這拔劍、切肉,是何等豪壯。樊噲本是「屠狗之輩」,手起刀落,如行雲流水。可是有些人手拙,就如法國人所說「長了兩隻左手」,要他們當場切肉,有適當的工具,可能已經有困難,如果餐刀鈍如鉛刀,恐怕只能看著樊噲大啖。
餐具的材質千變萬化,從木頭、竹器到金銀、犀角都有,價格也自然有別。中國雖然是瓷器的發源地,鈞窯、汝窯等官窯,都燒出許多神品、逸品,但是聽到「官窯」,就可以想見,豈是一般閒雜人等用得起的?17世紀,歐洲各國君主都寶愛中國瓷器,有一件兩件,趕緊放架上展示,哪裡捨得使用。至於中外平民百姓的餐具,仍以陶器為主。莊子讀書識字,在當時可算是中產階級,但家裡用的也是陶盆、木筷,沒事敲敲打打,不放心上,破了不心疼。乾隆爺日常吃飯,使的也只是普通官窯青花大碗,過年過節,才換上高級瓷器。20世紀中葉以前,德國的中上人家,星期日上完教堂,吃一頓像樣的午飯,為表達虔敬肅穆之心,這才拿出與日常不同的「週日瓷器」(Sonntagsgeschirr),以示區別。
除了瓷器以外,金、銀也是優良材質,中國官宦人家喜歡用銀製餐具。武松血濺鴛鴦樓之後,還把桌上的銀酒器皿踏扁,揣在懷裡,便於典當、賣錢。法國小說《悲慘世界》中,男主角尚萬強在主教家中受到親切款待,臨走卻偷了主教家中價值不菲的銀製餐具。歐洲人羨慕一個人出身高尚,總說這人「含著金湯匙出世」,都是這個道理。這些使用貴重材質餐具的人,隱約也知道不甚合適,總要避諱著點。《儒林外史》說范進中舉後,湯知縣請他吃飯,用銀鑲杯箸。范進因為母喪,不肯使用,以免逾矩。主人換了瓷杯、象牙筷,仍是不依;得要換成竹筷子,范進才肯用餐。
近代以後,瓷器可以大量生產,刀叉等也換成不鏽鋼材質,不分貧賤,大家都使得起。但是,許多根深柢固的習慣,仍然左右著一般人的用餐習慣。有誰聽說在倫敦街頭吃炸魚加薯條(fish and chips)用刀叉?有誰聽說在臺北早餐店中買了一套燒餅油條還拿筷子?不過歐洲人還是有些講究,喝什麼飲料,該使怎樣的杯子,一點都不能亂,喝紅酒不能拿啤酒杯,喝咖啡不能拿威士忌杯,否則叫做「破壞品味」(Stilbruch),就算是Banause。這個德語源自於希臘語,意思是「火爐邊工作的人」,轉成對「不懂藝術者」的稱呼,英語直接就說這人是「農民」,充滿了階級成見。只不過是沒把餐具用對,就背上這麼大的罵名。
這種破壞品味的事在咱們這倒是司空見慣,許多人為圖方便,不管喝啥,都使用免洗餐具。臺北街頭熱炒店林立,三兩個人,叫幾道菜,便喝將起來。只見喝白蘭地用塑膠杯,喝啤酒用塑膠杯,就連喝熱茶也用塑膠杯;喝完之後,全當垃圾,連洗都不用洗,多麼省事?更有甚者,夜市中賣蚵仔煎的,先拿一個美耐皿盤子,套上塑膠袋,把剛起鍋的蚵仔煎就往上放,在客人面前一撂,客人也毫不遲疑,拿起桌上的竹製免洗筷,揭掉塑膠套,風捲殘雲,三分鐘以後,結帳走人。店家把塑膠袋、竹筷子丟入垃圾筒中,盤子套上下一個塑膠袋,繼續營生。這種食物,就算是易牙再世,親自烹調,都不會有半顆米其林的星星。
說到米其林,許多人不免犯酸,認為米其林不過是個賣輪胎的,又有什麼資格對大廚的手藝品頭論足?其實大家忽略了一件事:米其林講究的,不只是廚師的手藝,而是整體用餐環境。東西好不好吃,沒一個準:同樣的東坡肉,張三喜歡軟爛帶甜,李四寧可要彈牙少糖,有誰能說誰的對?不過用餐時能桌椅乾淨,木筷瓷盤,跑堂輕聲細語,以客為尊,用餐者也不以為花錢的就是大爺,這種餐廳就能加分;要是講究餐具,環境清幽,用餐時不受鄰桌干擾,您說好是不好?
(照片:攝影 / 陳之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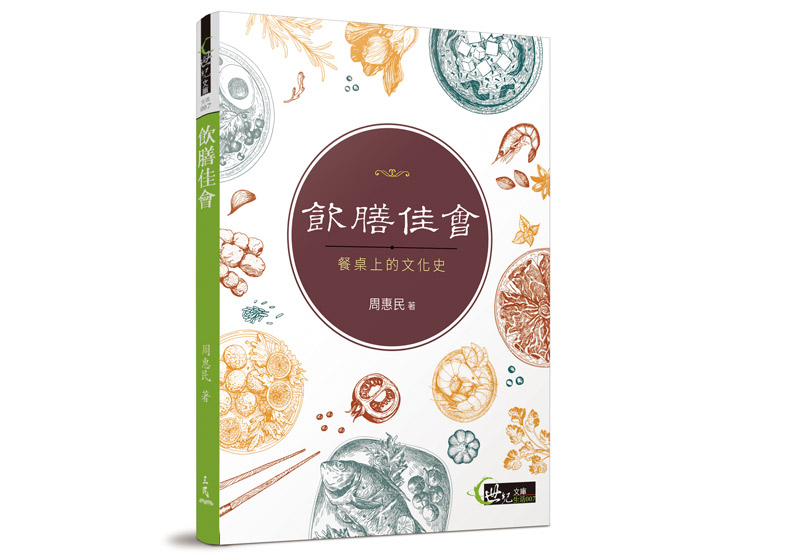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飲膳佳會:餐桌上的文化史》一書,周惠民著,三民書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