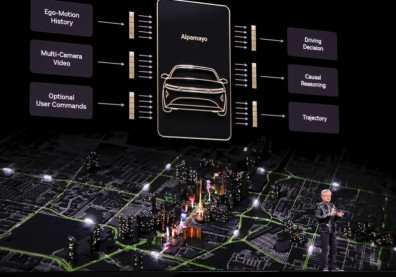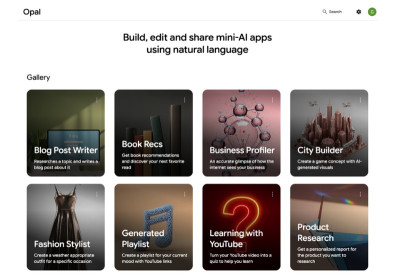攝於都蘭糖廠,E-ki在工作室外的數件雕像作品。
離開警員的車子之後我往南走了半哩路,再步上一條水泥坡道,才抵達E-ki的工作室。E-ki和他的哥哥坐在地上,倚著一塊去皮的原木,兩人都戴著向前翹的草帽,有如等火車般眼神放空,毫不急躁。「齁!」E-ki聽到我走近的聲音,一隻眼睛半開著說道。這間工作室是由一些破陋的房子組成,散落著工具、碎木塊和破家具,本來屬於E-ki的朋友所有,但那位友人計畫要夷平該處出售,這過渡期間就由E-ki負責管理。E-ki雖然已經結婚了,但他大多數時間都跟他哥在一起,處理鐵槌、鑿子、三腳椅,還有在前院到處啄食的雞隻而弄得骯髒不已。
E-ki的哥哥心思單純,臉上永遠掛著隨性的笑容。雖然是哥哥,但總聽E-ki的指令做事,即使本身的能力足以完成指派的任務,但無法主動積極地策劃。E-ki擁抱這世界,並以他所理解的那個部分突顯他的欲望、能力和眼界,但他哥哥總是落後於他,做些跟隨弟弟計畫的工作,從沒創造什麼專屬自己的作品。他一直沒結婚,眾人也無法把他跟「戀愛」聯想在一起。曾經有個晚上,我順道過去拜訪並打聲招呼,但E-ki那時在他妻子的公寓。他哥哥和我坐在塑膠凳上,啜飲我帶過去的一瓶米酒。
「唉!史考特啊!」他對我說:「你有沒有給自己找個女朋友?那該有多棒啊……」他說這些話時顯露出孤寂與渴望,好像是在說:「唉!贏得諾貝爾獎該有多棒啊……」
E-ki身為這個原住民木雕社群的長者,常常被尊稱為「E師傅」,在這慣用語中,E-ki的E會拉長成雙母音,發音就會變成類似字母A,因此聽來像是「A師傅」。他的朋友即興接上這字母順序的雙關語,戲謔似地稱呼他哥哥是「B師傅」。這綽號就一直沿用下去,稱說他是E-ki的B版本實在太過貼切,無法不認同。E-ki本人只稱呼他為「哥哥」。巧合的是,木雕師所使用的環氧樹脂又被稱為「AB膠」,兩個複合詞混在一起,形成一種立即的連結。
E-ki伸伸懶腰,示意要我過去坐著。「在山上都還好吧?你也知道的,我父親在都蘭山上殺了一隻熊,你在山上有看到熊的蹤跡嗎?」
「還沒。」
「那就對了,而且你也看不到了。牠們在海岸山脈幾乎絕跡了,成功鎮附近會有幾隻,但牠們大部分只會在中央山脈出現。」
「你們會吃熊嗎?」
「熊,這個嘛,你可以吃啦,我們也吃過,但不喜歡。我們想要跟牠們保持良好關係,而獵熊也不是我們的傳統。事實上,牠們也沒那麼美味,不像野豬或山羊,我們只會奮力抓這兩種動物。獵熊通常是賣給漢族,五十年前日本人撤台,蔣介石和兩百萬中國軍民進駐,突然就有黑熊的交易了。漢人用熊當作藥材,爪子、睪丸,誰知道還有啥。那時候阿美族人飢腸轆轆,於是變成專業的獵人。其他族也仿效,在他們還有能力跟著做的時候。」
「野豬有時候會在晚上下山,偷吃我家前面的甘蔗。」
「當然啊,你不會嗎?豬都知道什麼是好東西。下次牠們在外面時,叫我一下,我來弄點豬肉吃,我哥會幫我們剝皮,對吧哥哥?」
「喔,我剝過好幾隻了,我有一支刀專門用來去豬皮的。我會把它磨得銳利點。」
「我們可以聚個餐,整村的人都來。打給我,我會連他一起帶來,除非你想自己去叫他。你也許在上面也看過飛鼠,會飛的松鼠。」
「晚上有聽到牠們的聲音,獵人會用手電筒往樹裡面照。」
「沒錯,牠們是夜行性動物。獵人在找的是牠們眼睛發出的亮光,然後再用十字弓射下來,但用槍獵飛鼠是違法的。」
「史考特。」B師傅說:「那邊包起來的是什麼東西?你給自己買了刀嗎?」
我把剛買的刀身遞給他,他則從包好的報紙中取出,握柄舉得高高的。「啊!不錯,這把真的讚!我也想要買像這樣的刀。你買多少錢?」
但E-ki接過去看並皺起眉頭,手指沿著刀弧的平坦處游移著。「你怎麼會選這一支?」
「不曉得,就看起來還不錯,我想用來割草應該適合。」
「去!老黃怎麼會讓你買這個?如果你在山上,一隻野豬用獠牙攻擊你,你這把刀能幹嘛?在牠刺傷你之前,你必須要刺傷牠。你要怎麼用這彎彎曲曲的鬼東西?它根本就沒有威力,沒有……那叫什麼,沒有戳刺力道。在你對敵人造成傷害之前,你也許得在頭上揮舞這把刀,然後它會像一把斧頭般把你的頭砍掉,到時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看這裡,看一下我的刀身。你去問Siki、伊命,隨便問他們那些人其中一個。他們的刀身全都一模一樣。」
他抽出自己的刀,又直又長,底部很寬,但逐漸變細直至刀尖。
「好吧,現在告訴我你比較喜歡哪一把。還有媽的,你覺得我沒用過這刀來割草?我應該算是幸運吧!拜託,我帶你去走一圈,然後我再重新教教你。我猜你想給這東西做個刀柄吧?哥哥,你在幹嘛?回去工作嗎?」
B師傅大笑著:「對啊!我該做什麼?」
「幫我把木頭從貨車上搬下來,把它們堆在前牆那裡。晚點我們再來清洗並處理那些杉木。」
E-ki帶我走過連接兩間小屋的髒汙走道,穿過一個花園,裡頭新長的綠色植物隨處栽種,就那樣散落整片園圃。我們來到一個用廢木與鐵絲網搭起來的圈養區,裡頭有數十隻黑色且毛茸茸的小豬仔。「這些是迷你豬。」E-ki說。
「是什麼?」
「迷你豬,迷你山豬。」他用英文說出「mini-pigs」(迷你豬),但聽起來像是「meenipeegs」(米依你豬嗚):「你知道豬嗚吧?那是你的語言。」
「迷你」的用法從英文橫跨到中文維持不變─舉例來說,裙(qun)是中文的「裙子」之意,而迷你裙(mini qun)就是迷你短裙─而豬這個字,是E-ki在北部工作時能拿出來的英文詞彙。
「對,沒錯,我知道豬嗚。」我說:「你要怎麼處理這麼多數量?」
「用來賺錢啊!這兩窩花了我台幣一千塊,一旦牠們長大了,每隻我都能賣一千塊。想想看,兩萬四千元耶,就只是蒐集餿水再倒給豬吃,這差事還不錯吧?下個禮拜我也許會上你那兒去,我們可以割些草給牠們吃。」
「當然,上面多的是呢!」
我們回到工作室裡,有兩張木板凳並置但不完全相連,上頭有一塊黑色的尼龍篩網作為遮蔽。長桌上擺了環氧樹脂、幾支鑿子,還有上了油的鍊子、釘子和螺絲。
「我們來做你的刀柄吧!喜歡檜木嗎?」
「嗯嗯,那是我的最愛。」
「是啊,紋理和色澤都很漂亮,很多人都喜歡用來當作刀鞘,像達鳳就是。如此一來,每當你抽刀出鞘就會散發出肉桂香。此外,檜木也很好處理,那是軟木。」
E-ki從碎木堆中找出一塊檜木,放到鋸台上面。他抬起一台電鋸,測試一下鋸鍊的張力,然後拉住細索,使勁地一扯且發動馬達,濃煙便像雲霧般冒出來並繞上我們的衣物。他增強引擎轉速,讓鋸刀橫切過紋路,並用他的左腳固定木頭,鋸出了一段八吋長的木塊。這時他把電鋸關掉並放到地上,從鋸台上刷掉木屑和砂礫,審慎研究木身的節瘤,最後把木頭立起來,以短柄小斧沿著紋理削著。
「這就是你的第一步,」他說:「一塊厚實的木頭。你可以做任何處理設計,它最後會變成什麼模樣,就要看你的想法和技術,更不用說還有耐性了。」
E-ki走向他的工具台,拿回一支刀鋒呈三角形、有金屬刀柄的短小雕刻刀。他坐下來,從裝滿水的塑膠盆裡拿出一塊磨刀石,開始以幾乎水平的方向在石頭上推磨刀鋒,然後換成另一面,來來回回重複著相同的動作。
「第一次磨刀算你免費,下次你就得自己磨或付錢請我。你想要自己雕刻就多花點時間,把它完成,雕得順手合用些,之後我們就會把刀身給接上。拿去,看看我的,你覺得怎樣?」
他的刀從握柄末端陡然變細,提供了平滑且堅固的握把,然後又逐漸變寬,直至刀鋒的底部。雕過的木頭很適合我的手,彷彿合而為一。
「感覺很棒。」
「對嘛,當我上山時我在周圍會包幾片內胎皮,木頭濕了就會變滑,這些內胎皮可以讓你握得更緊。此外,你要怎麼在雨中生火?」
「我不知道。」
「內胎潮濕的時候也可以燒起來,所以我只要把它從我的刀上拆下來,就可以開始了。然後你要找一塊朝下的木頭,蒐集下方的一些乾葉子和青苔─也許還要砍些木頭下方引火用的木柴。你必須要削掉樹皮和外層,才能取得裡頭的乾木塊。你一定會想要在峭壁或巨石的遮蔽下生火,有時候則是在樹旁,這樣一來,你生火生到一半時,才不會被雨水澆熄。一旦點燃了,你要往裡頭丟一些盡可能乾燥的細枝。熱度會蒸發表面的溼氣,然後就可以用越來越粗的樹枝來重複這個動作。最好是要有個人看著火,護著它,而另一人去找更多的木頭。當然最好是不要下太大的雨─去,我在鬼扯什麼?最好是連一滴雨都不要下。看吧!沒有人會想在雨中生火,但有時候根本沒有選擇餘地。不過我父親啊,他可以僅僅帶著一包鹽和一支刀進入森林,一個月後還哼著歌大搖大擺走出來。而且,他那個年代的人很少雙手空空從森林走出來的,他們會帶著食物回來,肩膀上如果沒有扛著一隻鹿或山羊,他們還不肯露面呢!今非昔比,現在我們隨時都能開著車到店裡買塊肉,可是在以前,只要有人從森林回來,就會有一頓大餐等著。」
E-ki把木頭和刀子留給我,我一刀劃進金黃蜜色的木頭內部,在這棵樹被連根拔起之前,裡頭蘊藏了好幾年的高山日照與土壤,下沖到河流出海,又被回沖到岸上,E-ki和他哥哥就是在那兒將這塊木頭裝上貨車載回家。從山上到海中再回到岸邊,需要多少年的歲月?現在我刻著這樹木的一部分,將其黏在鐵片上,再回到山上,用來在樹叢中砍出小徑。削下的木頭呈捲曲狀,掉落到我的腳邊,周邊瀰漫濃郁的肉桂與杉木香。這把刀是汗水和金屬的連結,在我指間彎曲著,而刀鋒沿著紋理切入時,刮劃出刺耳的聲音。期盼夜晚將至的蟬隻,提高了牠們的叫聲,分貝不斷增強,而陽光從山後斜射而至。下方的公路介於E-ki工作室和大海之間,車輛加速通過彎道時發出呼嘯聲。E-ki回到他的工作檯,朝下瞧瞧我的進度。
「嗯嗯,真是有創意。」他說:「從沒看過有人做過像這樣的刀柄。問題是,你要怎麼握住它?」
他是對的,這玩意太笨重且不均勻,我一直沒辦法完成我想像中的線條和形狀。
「看看,如果你把這個弄低一點,就在刀柄的上方,你的手就能環握著。你希望手指和木柄能相互契合……好,再看看我的……如果你在山林裡,有隻野豬接近你,你會偏好哪一把?會發生什麼事?照你現在看來,你往那畜生的胃捅下去,而你的手就會跑到刀鋒的上方,而牠的獠牙就能撕裂你的鼠蹊。那麼一來,你有什麼用處?沒辦法對著漂亮女孩彈吉他,就算追到她們,也什麼都沒辦法做。現在就是你的抉擇了,但如果我是你,我會慢慢來,非常慢。不要用力鑿木頭,別試著硬來。現在又不趕,削著削著就好,用刀子去撫摸它……還沒唷!讓我躲遠一點,你動作太粗魯了,要殺豬嗚才這樣。我可不想變成你第一個受害者……」
E-ki的哥哥從院子那邊大聲吼叫著。「來吧!」E-ki說:「我哥剛煮了一條魚。」
我們穿過空地,坐在一張沾滿油汙、被鋸過的木桌前。每個人都有一碗白飯和筷子,共享著一條炸魚和一盤菜。
「知道這是什麼菜嗎?」E-ki問我。
「當然知道,地瓜葉啊!」
「沒錯,它們像雜草一樣到處長。往土裡丟幾根菜莖,一個禮拜後晚飯就能加菜了。」
「我聽說蔣介石來台並挪用軍餉時,很多台灣人是因為地瓜葉才沒有餓壞。」
「有可能,有可能……漢人只知道怎麼吃他們種的東西,我們當時根本覺得地瓜葉沒差。當時機不好,我們從野地採了什麼就吃什麼。」
「史考特,我不知道你們在美國也吃這些耶!」B師傅說。
「不,在美國不吃,但我山上的房子附近有一大片地瓜葉田。」
「你已經是我們的一份子了。」B師傅開口笑著說:「在城市裡,人們得去超市花錢買食物;在這裡,我們只要到外頭去,就可以採到我們所需要的。」
「呵呵,還是有些東西要用買的,他們還是得用些陷阱來抓住你。」E-ki說:「到目前為止,你不能跑到外頭的野地裡買米酒。菸沒辦法在野外長出來,真糟糕,對吧?順便提一下,兄弟,你怎麼沒把那瓶酒帶來,我們才能在需要時喝一下?」
桌子上方有條電線懸著燈泡,裡頭的燈絲閃閃發亮。日色漸暮,呈現晦暗的藍灰色,冷空氣也從山上傾流而下。青蛙和蟲子發出咕咕、喀達聲,並從廣場的邊緣發出鳴叫。此刻車子漸漸少了,公路之外、夜之海的沉寂,取代原先的引擎聲。
我們吃完飯後,E-ki轉開米酒瓶蓋,桌上擺一個小玻璃甕用來喝酒。我們輪流著喝酒、倒酒。
「你們美國有米酒嗎?」B師傅問。
「米酒,去!」E-ki說:「如果有威士忌,誰要喝米酒啊?這些美國人啊,喝了這小東西大概都沒感覺,才二○%,我說得沒錯吧?」
「我們沒有很多米酒,但其他的東西應有盡有。」
「下次你來,我們會完成你的刀柄,接著我會告訴你該怎麼給你的刀製作刀鞘,雖然你那彎曲的東東會有點難做。所有老人家都有外露的刀鞘,木頭外雕還綁上銅線,那是唯一能回憶他們光榮時期的方式了。現在我們有AB膠了,能作出堅固的木製刀鞘。你刻出兩個半模型,再把它們黏在一起。你可以選擇你想要哪個。」
「該死!我今天用雕刻刀,手都僵硬了!連手指也伸不直!」
「哈哈,看到沒?告訴過你了,如果要彈吉他就別雕東西。每次我拿起那吉他……手指就不聽使喚。但我又能怎樣呢?這是我註定要做的事,也許下輩子吧……」
「下次我會帶威士忌來。」
「呵呵,現在我們談到正題了。隨時來都行,但不要星期三,我那天要搭火車到花蓮看醫生。」
「生病了?」
「不是,沒什麼大不了的,只是檢查和吃藥。你知道那些醫生,總得賺點錢才行。醫生花很多錢的,呼咿,那些護士啊……你永遠不會看到醫生開著破爛的老貨車,或喝這種便宜貨。」
我倒了一小杯米酒給E-ki,同時用手指拍點玻璃杯旁的桌面,那等同於在說「請多倒點,謝謝,夠了。」
「啊!請別介意。」E-ki說道:「最後一杯,我喝完就要回鎮上我太太那邊。來吧!在你離開之前,我要介紹你給我媽媽認識。」
「介紹給誰?」
「來就對了啦!」
我跟著E-ki走到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那兒有個老婦人,坐在鋪有棉被的床上。她的頭髮往後紮成細圓髻,而她的臉看來像是以乾縮的蘋果雕成,眼睛甚至比頭目夫人更濁白。E-ki用阿美族語跟她說話,而她只回了幾個字。
「她說歡迎你。」E-ki說著。我牽著她的手並鞠躬。「她喜歡美國人,雖然你們在二次大戰時轟炸台灣,但只炸日軍。她說日軍比國民黨好,但她不怪你們。」
「她和你住在一塊?」我驚詫地問,不敢相信當我們整天來回走動時,她就自己坐在這陰暗的房間裡。她似乎在獨處中感到自在與自足,好像有某種晦暗不明的自覺和自我認同在支撐著她。
「當然啊!不然她能去哪?日本人和國民黨有分配土地給部落,但那是我們唯一的資源了。所以說,要是有人生病,家族就會賣掉土地來付醫院帳單。我們家則是堅守土地,即使當時我父親快要死了也一樣。但現在我們輸掉了官司,有另一個親戚聲稱我們的土地是他的,我們必須努力爭取,那就是我們在這裡的原因。這間工作室不是我們的,只是暫時擁有。這樣如何?漢人沒有從我們身上奪取的東西,我們家族竟然想要拿走。」我們再次往外走時,他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不論如何,我們身在此地。此刻,就是我們擁有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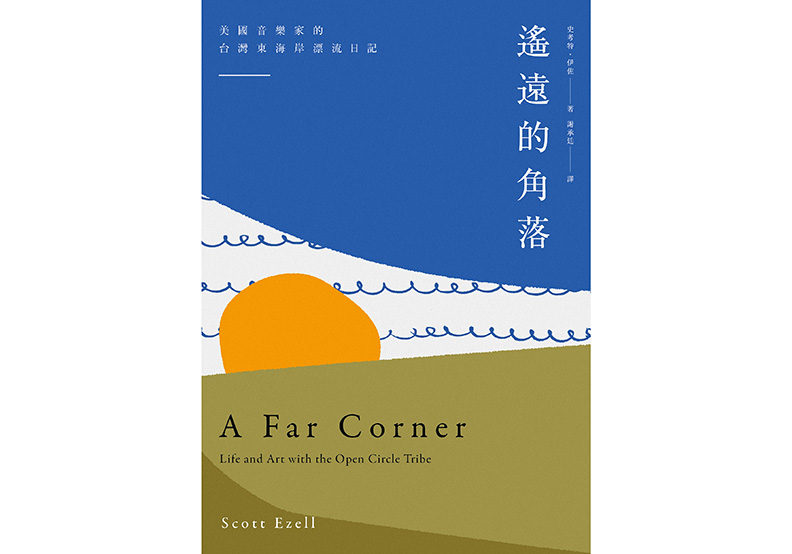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遙遠的角落:美國音樂家的台灣觀察日記》一書,史考特‧伊佐(Scott Ezell)著,謝承廷譯,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