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科學說得不錯,幸福快樂是由生化系統所掌握,那麼唯一能確保長久心滿意足的方法,就是去操縱這個系統。別再管經濟成長、社會改革或政治革命了;為了提高全球幸福快樂的程度,該操縱的是人類的生物化學。
過去幾十年間,人們確實已經開始這麼努力了。五十年前,精神藥物背負著嚴重的汙名,如今這種汙名已然打破。不論這是好是壞,現在有愈來愈高比例的人口,定期服用精神藥物,確實有些是為了治癒使人衰弱的心理疾病,但也有些只是要面對日常生活的沮喪和偶爾襲來的憂鬱。
舉例來說,已經有愈來愈多學童開始服用利他能(Ritalin)之類的興奮劑。2011年,美國因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而服用藥物的兒童人數,就有三百五十萬人。英國的這個數字,則從1997年的九萬二千人,上升到2012年的七十八萬六千人。 這些藥物的原本目的,是要治療注意力障礙,但今天就連某些完全健康的孩子,也開始服藥,希望能夠提高成績,迎合老師和家長愈來愈高的期望。
很多人相當反對這種發展,認為問題不是出在孩子,而是出在教育體系。如果學童出現注意力障礙、壓力過高、成績不佳,或許我們該怪的是學校教法過時、教室過度擁擠、生活節奏已經快到不自然。或許該改變的不是孩子,而是學校?各種相關論點的歷時演變,十分耐人尋味。幾千年來,教育方法的相關爭論未曾停息,無論是在中國古代或是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人人都各有一套理論,而且都對所有其他理論嗤之以鼻。但在先前,至少大家還有一點達成共識:想改善教育,該從學校下手。然而現在,大概是歷史上首次,至少有一些人已經認為,更有效率的做法是從學生的生化狀態下手。
軍隊也朝著同樣的方向前進:美國有12%的伊拉克駐軍、17%的阿富汗駐軍,曾經服用安眠藥或抗憂鬱症藥物,協助應對戰爭造成的壓力和痛苦。人會感覺到恐懼、憂鬱和精神創傷,原因不在於砲彈、詭雷或汽車炸彈本身,而在於荷爾蒙、神經傳遞物質和神經網路。共同遇上同一場埋伏的兩名士兵,可能一個嚇到呆滯、方寸大亂、之後幾年噩夢連連,另一個卻能勇敢向前殺敵,最後榮獲勛章。這裡的不同點,就在於兩名士兵身體裡的生物化學反應,如果能設法控制,就能一石二鳥,讓士兵更快樂,軍隊也更有效能。
用生物化學來追求快樂,也是這個世界的頭號犯罪原因。2009年,美國聯邦監獄有半數受刑人是因為毒品入獄;義大利受刑人有38%因為毒品相關罪行遭定罪;英國受刑人也有55%是因為使用或交易毒品而觸法。2001年的一份報告發現,澳洲受刑人犯下入獄罪行時,有62%都吸了毒。
人們喝酒是為了遺忘,抽大麻是為了感到平靜,用古柯鹼和安非他命是為了感到敏銳而自信;吞搖頭丸能讓人放大感官、感受狂喜,而LSD則會讓你踏進一場脫離現實的迷幻夢境。有些人靠著用功學習、工作或養家才得到的快樂,有些人只要操縱分子、調出正確劑量,就能遠遠更為輕鬆的搞定。這對於整個社會和經濟秩序都是實際存在的威脅,也正因如此,各國才會堅持對生化犯罪發動一場血腥而無望的戰爭。
國家希望管制用生物化學追求快樂幸福的手段,定出「好」與「壞」的區別。這裡的原則很清楚:如果有利於政治穩定、社會秩序和經濟成長,這樣的生化操作不但可允許,甚至還應鼓勵(例如能讓過動的學童平靜下來,或是讓士兵迫不及待投身戰役)。至於如果威脅到穩定和成長,這樣的生化操作就要禁止。然而,每年都有許多新藥從各大學、藥廠及犯罪組織的實驗室中誕生,國家與市場的需求也不斷變化。隨著用生化來追求快樂的腳步逐漸加速,對政治、社會和經濟也將有所影響,並愈來愈難以控制。
而且,使用藥物還只是個開端。實驗室裡的專家已經著手研究以更複雜的方式操縱人類的生化反應,例如將電流刺激,直接送至大腦特定部位,或是用基因工程控制人體的藍圖。不論確切方法為何,要透過生物化學操縱方式得到幸福快樂,並不容易,因為這其實改變了生命最基本的模式。不過話說回來,克服饑荒、瘟疫和戰爭,在過去又豈是易事?
長生不死之外,也想追求永恆的愉悅
究竟人類該不該花這麼大的心力來追求生化的快樂,至今離定論還很遠。有人會說,快樂這件事根本沒那麼重要,要說個人滿意度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目標,根本是走錯了路。有些人可能認為快樂確實是至善,但對於生化專家認為快樂只是身體愉悅的感覺,則很有意見。
在大約兩千三百年前,伊比鳩魯就曾警告門徒,無節制追求享樂很可能帶來的反而是痛苦,而非快樂。幾個世紀前,佛陀還有個甚至更激進的主張,認為追求快感正是痛苦的根源,這種快感只是短暫、毫無意義的振動。得到快感時,我們的反應不是滿足,反而貪得無厭,只是想得到更多。因此,不論我們感受到多少幸福、興奮的感覺,也永遠無法滿足。
如果我認定快樂就是這些稍縱即逝的快感,並且渴望要得到愈來愈多,我就別無選擇,只能不斷追求下去。好不容易得到之後,快感又很快消退,但因為光是過去快樂的回憶並不足以令我滿足,所以我又得從頭再來。像這樣的追求,就算持續幾十年,也永遠無法帶來任何長久的成果;我愈渴望這些快感,愈是變得壓力重重,愈是無法饜足。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快樂,人類該做的不是加速,而是慢下追求快感的腳步。
佛教對快樂的看法,與生物化學有許多共通之處。兩者都認為快感來得快、去得也快,如果人們只是渴求快感,卻不好好體驗快感,就仍然無法滿足。但接下來,佛教與生物化學兩者卻有了非常不同的解決方案。生化的辦法是開發出各種產品和療法,為人類提供無止無盡的快感,希望讓人能夠永遠享有快感。但佛教的建議則是減少對快感的渴望,不讓渴望控制我們的生活。佛教認為,我們可以訓練心靈,仔細觀察各種感覺是如何產生、又如何消逝。只要心靈學會看穿這些感覺的本質(也就是短暫、毫無意義的振動),我們就不再有興趣追求快感。畢竟,去追求一個倏然而來、忽焉而逝的東西,有什麼意義?
目前,人類對於生化解決方案的興趣是遠遠大得多。不論那些在喜馬拉雅山洞穴裡的僧侶、或是象牙塔裡的哲學家怎麼說,對資本主義信徒來講,愉悅的快感就是快樂,這種感覺可以周而復始。每過一年,我們忍耐不悅的能力愈來愈低,而對快感的渴望則愈來愈高。現在的科學研究和經濟活動都以此為目標,每年研發出更有效的止痛藥、新的冰淇淋口味、更舒適的床墊、更令人上癮的手機遊戲,好讓我們在等公車的時候,連一秒鐘的無聊都無須忍耐。
當然,這一切還是遠遠不足。智人的演化並未讓人能夠感受長久的快感,因此光靠冰淇淋或手機遊戲並不夠,如果真想長久感受到快感,必須改變人類的生物化學機轉,重新打造人體和心靈。而我們也正在朝這目標努力。我們可以爭論這究竟是好是壞,但似乎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大議題:確保全球的幸福快樂,就是會牽涉到重新打造智人,讓人可以享受永恆的愉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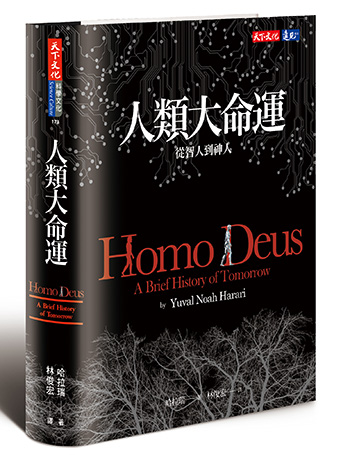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神人》一書,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著,林俊宏譯,天下文化出版。
圖片來源: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