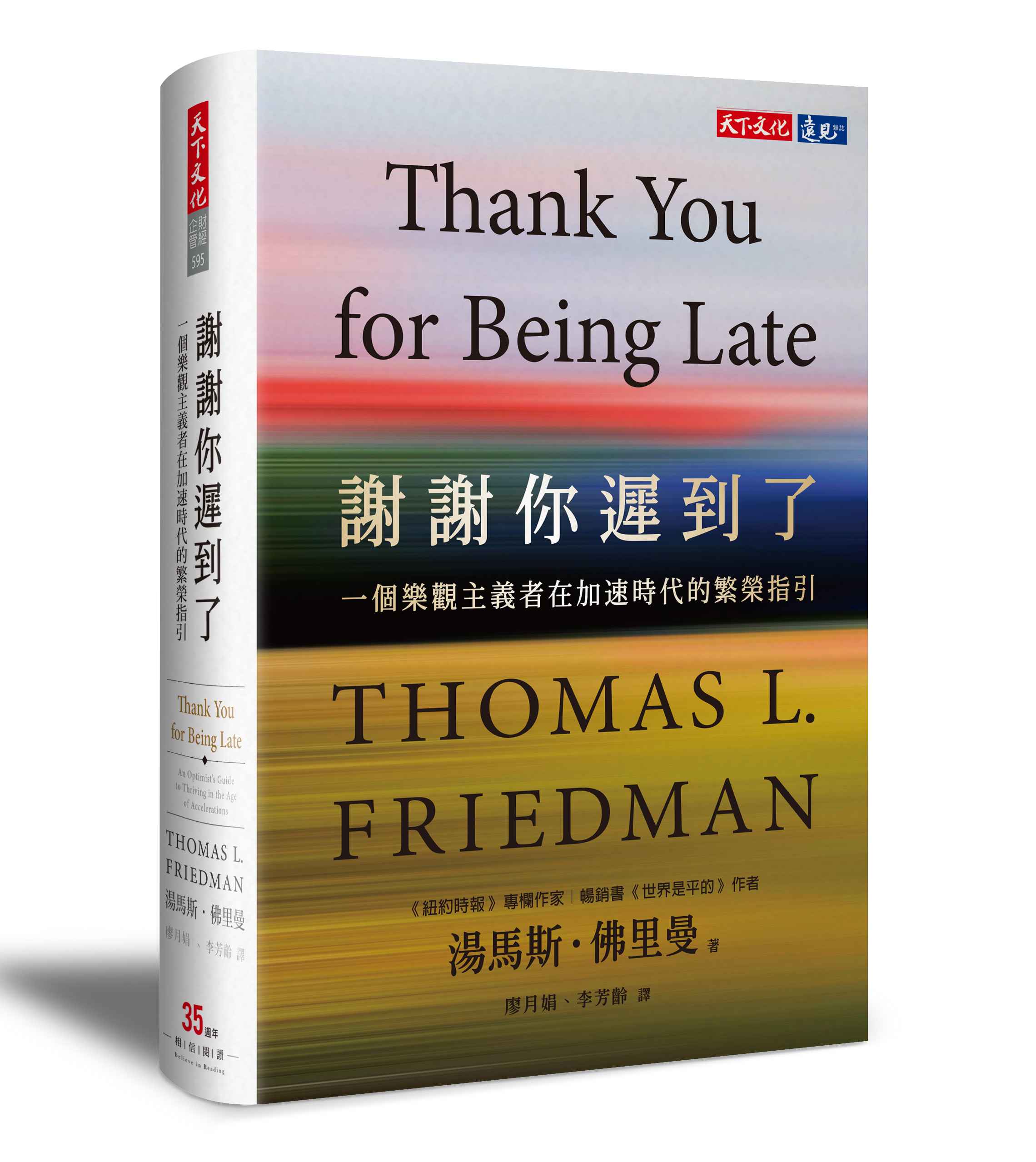我們先搞清楚一點:機器人並非注定要搶走所有的工作飯碗,除非我們讓它們這麼做;若我們不在人力、教育和創業等領域上加速創新,若我們不重新想像從初等教育、工作到終身學習這整條輸送帶,才會發生機器人搶走所有工作飯碗的情境。
但這一切,必須始於誠實地探討工作這項課題;在美國,我們已經有很長、很長一段時間,未能誠實地好好討論這項課題了。自 1990 年代初期開始,柯林頓總統及其繼任者,全都向美國人民說相同的老話:如果你努力工作、循規蹈矩,就能預期美國的體制將會提供你像樣的中產階級生活,你的孩子也會有機會過更好的生活。這些話確實曾經千真萬確過,只要上工,有平均水準的表現,好好地把工作做好,安分守己,人生就能一帆風順。
哎,向這一切揮別吧。
就如同我們似乎正在離開全新世的氣候那樣—那自然界的一切都美妙平衡的美好伊甸園時代,我們現在也正在離開工作的全新世。二次大戰後的「輝煌」數十年間,在市場、大自然和摩爾定律全都尚未進入棋局的後半盤之前,取得普通的高中或四年大學教育水準,無論選擇加入普通工會或不加入任何工會,一般工作者都可以過著像樣的生活。只要平均每週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時,你就能夠買間房子、養兩個孩子,偶爾還能去迪士尼樂園玩玩,同時為一般水準的退休及老年生活攢存積蓄。
在那些年代,許多事都對一般工作者有利。美國主宰世界經濟,許多歐洲國家和亞洲國家的工業基礎被二次大戰摧毀,因此戰後多年有龐大數量的製造業工作機會。在那些年代,外包受限,中國還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了 2001 年 12 月才加入),它的勞動力還未對多數不錯的藍領工作飯碗構成多大威脅。在那些年代,全球化的推力及拉力仍然相當輕微,創新速度也比較慢,加入不同產業的阻礙比較高;此外,工會的力量比較大,能和雇主談判出不錯且穩定的工資和福利。
在那些年代,公司負擔得起比較多的員工內部培訓,員工的流動能力比較低,因此較不可能在學會了之後離職。在那些年代,因為變化速度比較慢,你在高中或大學學到的東西,切要性和有用性維持得比較久,技能落差現象沒那麼普遍。機器、機器人及各式軟體,都還未進步到能夠非常容易、便宜地汲取這麼多複雜的事物,並且因此破壞工業及服務業工會的談判能力。
在這所有的因素下,這個勞動力全新世的許多工作者,都享有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全球政策暨倡議主任史黛芬妮•山佛(Stefanie Sanford)所謂的「中等技能的高薪工作」。哎,也向這一切揮別吧。
中等技能的高薪工作,走上了相同於柯達軟片的式微之路。在加速時代,動物園裡已經逐漸沒有這種動物了。高薪資、高技能的工作仍然存在,中等薪資、中等技能的工作也還存在,但中等技能的高薪工作已經不復存在。
僅只「普通」,不再有絢麗舞台可以發揮。我當年從大學畢業後,「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女兒卻必須「創造」自己的工作。我上大學學習終身技能,後來終身學習對我來說,變成了一種愛好;我女兒上大學學習,是為了學習獲得第一份工作的技能,至於終身學習對她們來說,是之後每份工作的必要條件。如今,美國夢已然是趟旅程,而非一個固定的終點,美國夢感覺愈來愈像是在一道下行的電扶梯上往上走。你可以試試看,我們在孩提時都曾做過這件事,你必須走得比電扶梯還快,才能夠趕得上。這意味的是,你必須更加努力,經常改造自己,取得至少某種形式的高等教育,而且勢必得投入終身學習,奉行全新法則,但也要改造其中的一些法則,這樣才可能進入中產階級。
我知道,這不是很讚的那種保險桿貼紙標語。而且,我在說這話時,也不是很開心,因為我喜歡舊時代的世界。但是,如果說了反話,那會嚴重誤導人們。想在現今的職場上成功,就得像 LinkedIn(領英)的共同創辦人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說的:投資於「自創」(the start-up of you),人生是永遠的測試版。沒有一個美國政治人物會告訴你這件事,但每個老闆都會告訴你這件事:你不能只是現身工作,你需要一套成功計畫。
和加速時代的其他任何事物一樣,為了取得並保住一份工作飯碗,你需要維持動態穩定,必須持續不停地踩著踏板或划槳前進。線上互動式程式設計學習平台 Codecademy 的共同創辦人札克•西姆斯(Zach Sims)認為:「你現在必須懂得更多,也必須更常更新自己懂的東西,用你懂的東西發揮更多創意」,而非只是做一些例行性的工作。「這種遞歸迴路(recursive loop)定義了現在的工作與學習,所以自我激勵遠比以往更為重要」,因為有太多學習是發生在你從高中或大學畢業後,或是搬離你父母家的很久以後,不是在有紀律約束的課堂上。
西姆斯說:「隨選世界(on-demand world)讓人人能夠隨選學習(on-demand learning),也讓世界各地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點,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學習,這大大改變了學習的定義。」他創立的平台讓人們可以更容易學習如何撰寫程式,「當我走進地鐵,看到人們在手機上玩《糖果傳奇》(Candy Crush Saga)時,我心想,他們真的可以用這浪費掉的五分鐘來改進自己。」
網際網路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興盛後的十多年間,很多人悲嘆「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現象—紐約市有網際網路,紐約上州沒有;美國有網際網路,墨西哥沒有;南非有網際網路,西非尼日沒有。這個問題很要緊,因為它限制了你能夠學到什麼,你能夠如何、在何處做生意,以及你能夠和誰通力合作。但在未來十年,數位落差將大致消失,帕羅奧圖未來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的執行總監瑪莉娜•高爾碧思(Marina Gorbis)說,當這天到來時,將只剩下一項關鍵落差,那就是「動機落差」(motivational divide)。未來將屬於那些能夠自我激勵、能夠善用超新星帶來的所有免費及便宜工具和全球流動的人。
二次大戰後的五十年間,如果這世界有一個針盤量表的話,指針是向左傾的,而且愈靠近蘇聯,指針就愈偏左,指向一個標誌:「你生活在一個『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s)的世界。只要你天天現身工作,有平均水準的表現,就會獲得這些給付。」自從超新星出現了以後,這個指針就大幅擺向右邊,現在指向一個標誌:「你生活在一個『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s)的世界。你的薪資與福利,如今愈來愈直接取決於你的實際貢獻,而且大數據將使我們愈來愈善於衡量你到底貢獻了多少。」現在是 401(k)的世界,借用二次大戰一幅著名徵兵海報的話:「山姆大叔要你(去當兵)」,現在是「山姆大叔要你更賣力。」
奇異公司執行長傑夫•伊梅特(Jeff Immelt)2016 年 5 月20 日對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畢業生致詞時說得直率:「科技已經提高了對公司及人員的競爭要求。」管理專家約翰•海格(John Hagel)說得更直率:「不論是個人或機構,我們全都承受了不斷升高的績效壓力。萬事萬物連結,代表進入與移動障礙明顯降低、變化加速。有愈來愈多的極端破壞性事件發生,這種種的發展給各種制度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個人方面,我舉的例子是以前豎立在矽谷高速公路旁的一個 T 霸廣告,上頭提出了一道簡單疑問:『全球至少有一百萬人能夠做你的工作,你作何感想?』我們可能會爭論這個數字究竟是一千或一百萬,但重點是,若是在二、三十年前提出這道疑問,大概會被認為是個蠢問題,因為根本不要緊,畢竟我在這裡,他們在別處嘛!但如今,這個問題愈來愈重要,或許還可以加上一句:『全球至少有一百萬個機器人能夠做你的工作,你作何感想?』在個人方面,我們全都感受到愈來愈大的績效壓力。」
三種新型社會契約
問題是,人人都能夠跟得上嗎?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經濟問題之一,或許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下列是思考這個問題的方式之一:歐巴馬總統的前任經濟顧問拜倫•奧古斯特(Byron Auguste)指出,在每一次的重大經濟轉變中,「總是有一種新的資產類別,變成生產力成長、創造財富與機會的主要基礎。」奧古斯特是Opportunity@Work 的共同創辦人,這個非營利性質的社會企業,目標是要讓至少超過一百萬個美國人,在未來十年「盡量發揮潛能工作、學習和賺取報酬。」奧古斯特說:「在農業經濟中,這種資產是土地。在工業經濟中,這種資產是實體資產。在服務業經濟中,這種資產是無形資產,例如方法、設計、軟體和專利。」
「在今天的知識人經濟中,這種資產將是人力資本,也就是天賦、技能、隱性訣竅、同理心及創造力。這些是未獲足夠重視、有待釋放的龐大人力資產,我們的教育機構和勞動市場必須對此做出調適。」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避開只有少數幸運兒才能取得資產或機會的成長模式。然而,為了支撐這種社會需要的大規模財富重新分配,在政治上卻是無法持久的。
奧古斯特說:「我們必須聚焦於以投資人力資本為基礎的成長模式,這麼做可以產生更有活力的經濟和更包容的社會,因為才能及人力資本的分配,遠比機會或財務資本的分配更為平均。」
我們又該從何著手呢?奧古斯特說,簡短的答案是:在加速時代,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三種重要的社會契約,亦即員工與雇主之間的契約、學生與教育機構之間的契約,以及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才能創造出一個人人都能充分發揮天賦潛的環境,讓人力資本變成一項舉世皆然、無法讓與的資產。讓人力資本變成一項舉世皆然、無法讓與的資產。
本文節錄:《謝謝你遲到了》 一書/湯瑪斯.佛里曼 著